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0年第6期
ID: 141459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0年第6期
ID: 141459
一代才女蔡文姬及其《悲愤诗》
◇ 俞 师
蔡文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她的作品《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影响深远,本文重在研究其作品《悲愤诗》上,她坎坷曲折,身世飘零的一生,感人至深的《悲愤诗》,还有她传奇世的经历,让她在女性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缺少的地位,本文就对她及她的作品进行了一些研究。
一.曲折的生活经历
蔡文姬,本名琰,字文姬,又字昭姬,东汉文学家蔡邕之女。关于这位才女的传记资料不是很多,散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零碎的《蔡琰别传》中,其中较全面的有《后汉书·列女传》中的一篇小传,传云——
“陈留董祀妻者,同邑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之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设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及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至嫁于祀……后感伤离乱,迫怀悲愤,作诗二章……”这段话简述了蔡文姬的生平,其实对她的研究可从其父开始。
文姬的父亲蔡邕是汉末文坛重镇,建安文学的先驱,对她的一生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1]。文姬确切生卒年不可详知,据多数学者考证大约为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年前后生,就在这一年前后,其父遭到了重大的打击,由于父亲对朝政不满,进行尖锐的抨击,得罪许多达官显贵结果被视为“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要处以极刑。在有关人士的翰旋下,才免于一死,从蔡邕的陈情中知道,当时他“年四十有六,孤身一人”这孤身表明了蔡文姬没有兄弟,似乎可以说,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初,文姬的命运就注定悲苦飘零了。
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也就是蔡邕流亡的第三个年头,朝廷大赦于永汉元年(189年),蔡邕为董卓所征迁为尚书,这时蔡文姬大约十二三岁,开始了一段比较短暂的,平静富足的生活,16岁时,蔡文姬远嫁河东卫仲道。《艺文类聚》卷三十所收了 《蔡伯喈女赋》一段话“在年华之二八,披邓林之曜鲜。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这段就是关于文姬出嫁的记载。不幸的是,此后不久,蔡邕因对董卓之死表示了同情而发出一声叹息而被王允杀害,这是初平三年(192年),更不幸的是,几乎同一年,她的丈夫逝世,史书载“夫之无子,归宁于家。光平中,天下丧乱”由此可知,文姬结婚只有一年左右时间,因为没有子女,只好回到家乡,不久就逢丧乱,她被劫持去今甘肃青海、新疆一带,正式成为羝胡家室,开始了她更艰难的人生之旅。文姬在胡前后生活了十二年,生二子,至建安十二或十三年,文姬大约三十岁了,曹操因与其父关系密切,乃遗使老以金壁赎之,重嫁于陈留董祀。在归汉的日子里,她用极大精力整理父亲的藏书,文姬大概逝世于建安二十五年,这就是蔡文姬的一生,经历了父丧夫亡,国家动荡,远家他乡,骨肉分离,这一切都充满了悲剧色彩,悲惨的经历让她的心灵伤痕累累,而她的创作则是对于苦难的悲吟,可以说她的作品,承载了社会与个人的痛苦悲哀。
二.创作的起因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蔡文姬这样才华出众的女子呢?这当然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原因吧。
首先,文学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可分两层来看即大环境与小环境,大环境是社会方面的,文姬所处的时代是魏晋时代,鲁迅曾评这个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期,出现了很多文学人士,有很浓郁的文学氛围,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对社会影响很大,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姬,在耳濡目染中当然会受到文学的熏陶。另一方面是小环境的影响,小环境即家庭方面的,前面已介绍过其父蔡邕,他是东汉著名学者,能文善书,妙操音律,虎门无犬子,师出名门当然会与众不同了,曾有大书法家,唐人张彦的《书法要求》一卷中有传授书法人名说“蔡邕受于禅人而传之崔瑗及其女文姬。”虽然这是神话但文姬承他父亲是很自然的事情,文姬对间律精通,在《后汉书·董祀妻传》注引刘昭《劝童传》中就有记载她和她父亲的对话:“邕夜弹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可见其父对其的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可见她的善书善琴,长于诗文这些都和她父亲的悉心培养分不开的。
其次,个人的勤奋好学,有父亲蔡邕的悉心指导,蔡文姬还博览群书,韩愈曾说过“中郎有女能传业”指她具备了良好的文化素养。在《后汉书·董祀妻传》中有记载曹操问文姬曰:“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之否?”文姬曰:“昔之父赐书四千多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颂忆,载回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为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由这段话可见,虽时光流逝,虽长期遭受磨难和流离之苦,仍能忆涌400余篇,这些都体现了她文学基础的扎实与深厚的文学修养。
再次,时代与个人遭受的原因。蔡文姬所处的时代,空前动荡,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运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饿,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徒,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2]曹操的《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可见人烟的荒凉;环境的凄凉。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破家亡的伤痛,深重的时代背景融入到了作品中,再加上她个人经历的坎坷曲折,年轻时丧夫后被乱军裹挟,像风卷蓬草,辗转流离于边境,一住就是十二年,她的青春年华都伴随着寒风飞雪,伴着忧郁悲伤,胡风呼啸,以及被蹂躏,受屈辱的心灵,全都凝聚于她的文章中,或许这就是发愤著书的又一例子吧,蚌病成珠,只有历经了磨难才会创作出情真意切的精品。
三.作品的价值及其影响
蔡文姬的作品流传的有两首《悲愤诗》一首是五言,一首是骚体,另外还有琴歌《胡笳十八拍》。下面着至研究《悲愤诗》来鉴定赏其艺术价值。
五言《悲愤诗》总共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文姬以自己十多年的经历和内心感受为主线,将纷繁复杂的材料,浓缩剪裁,突出被虏入关,边荒生涯,被赎返乡三个重点,给以淋漓尽致的描绘,使人身临其境,看到她屈辱的生活,体会到内心悲愤,文章峰峦起伏,气势磅礴。
第一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以及俘虏们所受的虐待,蔡文姬遭受着这样的苦难,她问苍天:到底有什么罪过,要受如此虐待,又通过士兵与百姓的对话,将百姓猪狗不如的处境逼真地表现了出来。第二段写得最为沉痛,也是最撼动人心的“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其中“边荒”,“异”,“少义理”写出了自己身在异乡的强烈不适应也写到了异乡风俗野蛮,自己飘零一生,被蹂躏受屈辱的遭遇,“霜雪”、“胡风”既写了胡地条件恶劣也写出了时间流逝,表现了对于家乡的思念无时不在,只要听到有客自远方来,总会抱有很大的期盼,总希望听到有关家乡的消息,以解思乡之苦。第三段是写回乡后生活,是悲剧性的延伸,整诗于叙事抒情为一体情感流动贯穿始终,生动地表现了各种场面和内心活动,描写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中可看出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悲愤诗”概括了时代的灾难,倾诉了自己的屈辱,呼天吁地,充满了不平,这是一个悲剧时代充满悲剧色彩的诗篇[3]。
虽然蔡文姬的作品传世的不多但是都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些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简略探讨一下:
首先,是对五言诗的延续与完善促使了五言诗走向成熟。五言诗的兴起,较早的应为班固的《咏史诗》写汉文帝时孝子缇萦为赎免父亲请求没身为婢的故事,虽形式上具备,但是却“质木无文”毫无文采可言,后来出现了张衡的《同声歌》,蔡邕的《翠鸟》等诗,促使五言诗的发展,使其逐渐成形,而蔡文姬《悲愤诗》的出现将五言诗推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古典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让其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悲愤诗》无疑是五言诗中不可缺少的典型佳作。
其次,《悲愤诗》对后来作者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悲愤诗》深受汉东府叙事诗的影响,可以和《孔雀东南飞》比美,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受到了其影响。《北征》中“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写出了战争的惨烈,让人触目心惊心,家中“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这些将战乱与贫困一一显现了出来,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诗史价值,是对蔡文姬诗中那些叙事抒情方式的继续与发扬,文姬诗中对于时代的反映与表现具有诗史价值,无不让杜甫在创作诗歌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外,文姬归汉后对其父作品的整理与保留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后世关于历史和文学资料的研究起到了帮助作用,她的出现丰富了女性文学的领域,也丰富了中国文坛,她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浸染,也在痛苦中吸取创作的源泉,她用她的才华和顽强与时代命运抗争,她是那茫茫夜色中一颗闪耀的星星。
总之,本文分别从蔡文姬的生平经历,作品的一些争议,创作原因,作品价值及影响几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对于其研究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深入的研究近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参见《蔡邕论》、《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2]袁祖亮《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3]《论蔡琰〈悲愤诗〉》《汉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俞师,文学硕士,广西医科大学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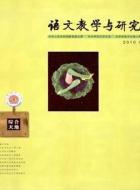
- 露天电影 / 徐则臣
- 流动和本质 / 夏元明
- 现代语文教学之路 / 于国华
- 有效教学三部曲 / 许长青
- 在古典诗歌教学中渗透美育 / 刘春艳
- 引导学生建立新型的学习方式 / 周 舫
- “最近发展区”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 / 姜金龙
- 初中语文字词教学谈 / 魏树斌
- 文言文教学与社会意识培养 / 齐莹莹 余 雯
- 新课标下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 张丽华
- 文本的几何解读:长×宽×高 / 赵永芳 尹寿波
- 让学生乐于展示自我 / 钟启娴
- 发现语文之美 培育健康心灵 / 崔永春
- 人本主义背景下的语文情境教学策略 / 陈家武
- 论语文教材的创造性使用 / 乔元勤
- 让阅读教学回归本位 / 刘美廷
- 巧用三法品语言 / 田慧兰
- 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 / 张利华
-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之我见 / 李建峰
- 语文教学中如何落实以学生为主体 / 刘杰英
- 阅读教学应凸显文本的语文核心价值 / 朱浩军
- 巧抓“空白”妙填补 / 陈 静
- 给足时间是走进文本的保证 / 葛 平
- 浅论以文为本的阅读教学 / 艾维蓉
- 有效课外阅读的几种方法 / 李彩霞
- 诗歌朗读训练与阅读能力培养 / 方建莉
- 四步教学生读懂一首古诗 / 刘 鹏
- 挖掘课文中蕴含的审美内质 / 王顺顺
- 如何解开初中作文教学的死穴 / 刘 惠
- 和谐阅读的三重境界 / 席洪周 刘传庆
- 浅议阅读教学中的读讲悟 / 陈长明
- 让学生创作的心灵自由飞翔 / 潘瑞祥
- 引导学生改出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 张迎春
- 在学习中模仿 在改写中掌握 / 柯 蕙
- 作文其实也简单 / 张国勋
- 敢于模仿,作文才会进步 / 虞伟力
- 如何指导学生写好想象作文 / 洪 杰
- 如何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 / 陈青青
- 仿写种种促创新 / 陈劲松 刘娜拉
- 以人为本是写作教学的出路 / 董亚美
- 写作是一种生命的运动 / 朱丽君
- 陆机《文赋》对中学作文教学的启示 / 李巧敏
- 让朗读成为语文课堂的主旋律 / 孙丽妍
- 语文课上,我听到了生命拔节的声音 / 贾泽云
- 如何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 / 王晓红
- 让学生在仿写中学会作文 / 冯艳艳 田 艳
- 怎样上好作文指导课 / 陈绪强
- 关于习作教学及早起步的看法 / 郭明珍
- 让动态生成演绎课堂的精彩 / 张小波
- 课堂氛围与文章美感 / 杨翠柏 杨翠莲
- 关注常态课堂 重视课堂实效 / 陈 颖
- 实践生活教育理论 激活语文课堂教学 / 顾锁英
- 语文课堂教学特性之探究 / 傅鹏伟
- 构建开放的语文课堂 / 万明哲
- 语文教学与中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 钮绪纯
- 在语文课堂里展开自由平等对话 / 丁国林
- 语文课堂教学语言运用艺术刍议 / 戴加华
- 《前方》教学构思与实录 / 王晓军
- 诗歌的审美特性与语文教学的诗意追寻 / 张厚萍
- 记叙文写作教学设计 / 张五芳
- 让农村学生也能说会道 / 杨正林
- 两篇课文的比较阅读 / 朱萍萍
- 试论文学言语的生命力 / 张汉璞
- 《望岳》与《春望》教学设计 / 王 辉
- 例谈语感的培养 / 陈益女
- 例谈经典形象的德育尴尬 / 向贤湖
- 杜甫晚年诗作中的人文思想 / 范慧芳
- 钱塘君出场艺术及形象分析 / 高培存
- 一代才女蔡文姬及其《悲愤诗》 / 俞 师
- 高考古诗词鉴赏题摭谈 / 龙莲明
- 高考作文备考复习策略 / 张 莉
- 如何有效提高语文试卷评讲课效率 / 李宝建
- 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备考 / 周珺红
- 关于学生自主学习的几点思考 / 赵 蓓
- 大雁能在秋天归来入胡天吗 / 丁文宏
- 人性化管理与言语技能高效训练 / 宁志斌
- 语文综合性学习的语文味 / 韩赟云
- 滴水藏海 丰富多彩 / 钱德宝
- 爱的教育 / 张裕峰
- 词语教学中人文性的渗透 / 张志诚
- 创新管理机制 推进课程改革 / 施洪中
- 简约的文辞与深远的意蕴 / 郭建雄
- 新课改下理想的新型师生关系 / 李成建
- 当代文化范式可能性探求 / 肖志宏
- 中学图书馆开架借阅中的乱架及对策 / 陈黔英
- 错别字整理与儿童发展 / 包玲玲
- 想你,在某个时刻 / 章美云
- 星空 / 孙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