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6期
ID: 135831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6期
ID: 135831
曹文轩散论
◇ 潘新和
与曹文轩先生素不相识,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他年龄比我略小。猛然看到一篇文章称他“老教授”,在替他抱屈之余,也不由地想到自己更应该归入“老教授”之列,因而生出颇多感慨。其实曹先生一点也不老。他是儿童文学作家,心年轻,也长得年轻,称得上清逸、俊朗。学者大多长相不怎么样,成就往往是与长相成反比的。成就既大,且能像曹先生这样相貌堂堂的实在不多。
曹文轩先生的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大水》《追随永恒》《三角地》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天瓢》等。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小说门》等。作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可见其著作之宏富。
在他的作品中,青少年成长的过程是幸福的,美好的世界逐步在他们眼前展现;这个过程也充满了烦恼甚至痛苦,因为他们要面对暂时还无法理解的人和事,因为每进一步都要付出某种代价。这些小说展示了青少年身体与头脑、情感与心灵渐次成熟的历程。读着这些小说,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生命内部的成长的声音,我们与书中人物的情感融为一体,一起经历着特定人生阶段的烟云风雨①。他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成长小说”, 深受青少年欢迎,大约就是因为重在表现青少年成长、成熟的心路历程,切中了他们的情感和心理。
他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国外,《红瓦》《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已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国家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金鸡文学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中国时报》1994年十大优秀读物奖等学术奖和文学奖30余项,2004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可见影响之广泛。
曹先生是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高校教师之一。他曾主编有广泛影响的《新语文读本》、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课教材第一册和选修课教材第一册,还曾主编配合新课标的多套丛书,其中有北京大学与江苏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语文课程标准课外读物导读丛书》(5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人文读本》(12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每周阅读计划》(12册)等。
他在语文教育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加各种重要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与作文教学会议,发表讲话。应许多地方教育部门的邀请,他向中小学语文老师以及广大学生发表演讲,阐述自己有关语文教学与作文教学的新理念。他的作品与文章有多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他的长篇小说《红瓦》第九章,被韩国选入全国高中语文教材。②
他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他对语文、文学教育,对写作和写作学习的理解和指导也特别到位,有自己独到的体验。他对文学和人的关系,文学对人性和诗性培养的重要意义,写作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意义,低龄化写作状况、存在的偏向的思考及写作学习所需修养、学养和技术练习的要求等见解,对中学文学和写作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启示。
由于他是作家,所以他对青少年写作和写作教育情有独钟,理解得特别深刻细致,特别能说在点子上。例如,他最为关注“叙事”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不但能说出自己的感受,还能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这可以看作是他的经验之谈。这种经验之谈恰恰是一般教师所缺乏的,因而是很宝贵的,师生们看了会觉得特别亲近、真切。由于他是作家化的学者,所以,他所谈的就不停留于经验,而是能够在某些更深的层面上认识语文、写作的意义与价值。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他可以不避浅俗,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学生怎么写;为了提升学生的言语素养,他可以不畏高雅,让人动心忍性、养气知言。
曹文轩先生的精神意义还在于对青少年业余写作实践的重视。曹先生可以算是高校学者中对青少年写作最为关注的学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他是“新概念作文”的发起者兼评委。他为韩寒、郭敬明的小说作序,对不少少年的写作谈了自己的看法,客观地评价他们的水平,指出了他们的优点与缺陷,既对他们寄予厚望,也使他们保持清醒。他说:“简单地说,低龄写作是件好事,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古代的那些大师不是几岁就会写诗了吗?有些写得还很好。现在低龄化写作与未来的作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现在的写作与未来的写作也没有任何关系,少年写作就是少年写作,低龄化写作就是低龄化写作。因为能否成为一个作家还牵扯到复杂的经验问题,经验这东西不是你想有就有的,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命运的安排,而命运这东西不是你想掌握就能掌握的。”③新概念作文“秋意太重,文章中的绝望、忧伤、悲剧性十分普遍,孩子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大了”。他对越办越火的新概念作文“无节制地鼓励想象力”感到困惑,认为人生也有春夏秋冬,人生各季对生命的感悟是不同的。但是,引起媒体、学校、家庭广泛注意的新概念作文,鲜有那种“阳光的、快乐的”的情绪,青少年作者很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④。他阐明了低龄写作与未来作家之间的关系,对他们的认知局限与文字缺陷也一语中的,这样透彻明白的见解是不可多得的。
有人评价曹文轩先生:学者化的作家,作家化的学者。诚哉斯言!
在高校中文专业,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教师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作家与学者的素养与话语方式是很不同的。前者是虚构、想象的,后者是实证、严谨的。上帝是吝啬的,给予你此天赋就不给你彼天赋。因此,作家不会研究,学者不会创作是很正常的。二者兼而得之,则是很稀罕、很奢侈的。作家、学者,本来是各有所长,然而长期以来,在高校中文专业,创作才能并不被重视,往往被视为雕虫小技,人们对此嗤之以鼻,多搞点创作,会被认为不务正业,创作的成果往往不被认可。在当下中国高校的中文专业中,作家型的教师是十分罕见的,“作家歧视”源远流长。当年的沈从文先生就没少招来白眼,人们看重的是研究,而不是创作。因此,教师的创作优势是得不到鼓励的。创作优势似乎反而成了教师教学的“劣势”,创作成果不能评职称,这无疑是一大偏见。曹先生如果没有学术成果,单凭创作成果——不论多么丰硕,恐怕也没法在北大呆下去。这种荒谬的状况亟待改变,创作型的教师在教学生读写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学生对作家的景仰要远远超过对学者的景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歧视学者,而是说明二者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对于中文专业来说,只有作家或只有学者,都是不完备的。
在高校,“学者崇拜”的风气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变成了“作家歧视”、“学者自傲”这就不值得推崇了。而这种观念对学者自身也是有害的,有些学者写了几篇论文便自以为是,终日板着面孔故作深沉状,以为了不起,以搞“学术”自居,从此,好的文章就再也写不出来。写出的文字干瘪瘪的,没有一点生命热度、生活情趣,简直不堪卒读。这样的学者太多了,为了写几篇论文把自己弄得没情没趣、没心没肺,划得来吗?
学者瞧不起作家这是千真万确的,不知作家是否也瞧不起学者。大概也同样吧,“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恶劣的流俗。而曹先生以其一流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改变了这一偏见,使人们明白“学者化”作家和“作家化”学者的优势,将作家与学者之间的沟壑填平了。不过,这对多数作家和学者来说,只能成为一道遥远的地平线——可望而不可及。这就尤为显出他的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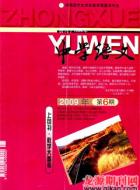
- 曹文轩散论 / 潘新和
- 语文交际教学研究 / 张 富
- 语文有效教学研究问题分析及应对策略 / 成 龙
- 孔子的教育之道(六) / 韦志成
- 学习动力驱动观:主体主动参与 / 徐 萍 曹明海
- 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困境与出路 / 胡根林
- 选修和必修教学的整体联动 / 鄂冠中
- 杀戮背后的人性扭曲 / 唐艳红
- 新课程视野下文本处置的十种意识 / 刘德海
- 文本解读三“忌” / 陈洪团
- 文学作品阅读的体认与重构 / 于卓琳
- 文本多元个性解读与微扰论建构 / 田小华
- 给学生一个支点,他们能撬动整个语文板块 / 刘 军
- 《说“木叶”》质疑 / 潘东明
- 《走进古 / 王虹霞 余映潮
- 在综合性学习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举隅 / 冯大海
- 词语误用例说 / 闫吴平
- 聚合·钩连·增替·重构 / 赵清林
- 作文技术教学内涵辨正 / 赵东阳 王春梅
- 重建课堂阅读教学尝试 / 奚雪群
- 作文教学中要理清六种关系 / 赵徐洲
- 也谈语文教学的“无声之美” / 黎万生
- 有效作文教学的三种理念 / 张世殊
- 韩信为何“怒,竟绝去” / 何 伟
- 关于树的诗文赏析(四) / 孙绍振
- 伪问 / 姚志忠
- 关于课标卷探究题的探究 / 孙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