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期
ID: 35565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期
ID: 355652
也谈古典诗歌中的比喻
◇ 韦荣瑞
姚文革同志在《古典诗歌中的比喻例谈》(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上])文中,对古典诗歌运用的实例,作了精辟而深刻的解析,使人深受启发。但对作者在该文中表明的某些见解,笔者却有不敢苟同之处,写作本文,一方面,同姚文革同志商榷,一方面也是求教于语文同行和大方之家。
一、比喻的格式
比喻分为三种基本格式:明喻、暗喻和借喻。这是修辞学上对比喻辞格的通常界说,然而,比喻在古典诗歌中的运用却更为丰富多彩。我们先看下面一些例子:
①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屈原《国殇》)
②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静夜思》)
④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杜甫《兵车行》
⑤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
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行路难(其一)》)
①②两例是明喻。它的特点是: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中间用“若”、“如”、“似”等喻词连接。③④两例是暗喻。它的特点是: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中间用“是”、“为”等喻词连接,有的则不用喻词。⑤⑥两例是借喻。它的特点是:本体和喻词都不出现,而由喻体直接替代本体出现。例⑤以春蚕吐丝、丝尽而死,蜡烛燃烧、烧尽泪止,来比喻刻骨的相思之情和对爱情的忠贞。例⑥以行程中路途的艰难,来比喻仕途之艰险。这两个例子都是只出现喻体,本体没有出现,也没有喻词。
比喻除了这三种基本格式以外,还有其他几种灵活的用法,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⑦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诗经·卫风·氓》)
⑧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
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隰”指低湿之地)(《诗经·卫风·氓》)
⑩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白居易《缭绫》)
{11}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居易《花非花》)
例⑦没有出现喻词,而把喻体和本体排列成结构相似、互相映衬的平行句式。喻体有起兴的作用,目的在于引出本体;通常我们把它称为“引喻”。
例⑧的本体与喻体有共同的特征,但为了突出本体的这一特征,特别强调喻体的程度不如或超过本体。这种比喻中常用“不及”、“不如”等做喻词,有时也用“于”做喻词来连接本体和喻体,如“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这类比喻往往借突出喻体的特性来使本体得到更强的夸张。我们称之为“较喻”。
例⑨只出现喻体,本体和喻词都没有出现,形式上同普通的借喻相似,但实质上又有不同,一般借喻都是从正面设喻的,强调本体和喻体有相似的特点;而这个比喻却是从反面设喻的,强调本体具有喻体相反的特性。这个例句就是以“淇有岸”、“隰有泮”来反喻自己愁思无尽的。我们可把这类比喻称为“反喻”。
例⑩的本体和喻体并不类同,但仍采用比喻的形式,以表明本体不具有喻体某方面的特性,这叫“否定喻”。这种比喻的喻词往往用“不是”或“不似”。这里强调“缭绫”的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
例{11}由“花”、“雾”、“春梦”、“朝云”四个并列的喻体构成,共同喻指同一事物(本体)。像这种由一个本体和多个喻体组成的比喻,叫“博喻”。
比喻除了以上几种格式之外,还有“同位喻”、“修饰喻”等。弄清比喻的基本格式及其变化形式,有助于我们在阅读鉴赏古典诗歌时,能更加正确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和诗人的感情。
二、比喻的界定
因为比喻的格式丰富多样,富于变化,有些比喻在形式上同借代、用典等修辞格极为相近,所以如不细加辨别,就很容易混淆,甚至造成张冠李戴的错误。笔者想结合具体的实例,谈谈如何界定古典诗歌中的比喻和非比喻。
姚文革同志在该文中把借喻在古典诗歌中的用法,分为三种类型:以物喻人、以物喻物、以人喻人。他在分析第三种用法时列出以下4个例子:
①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
②和烟和雾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吴融《卖花翁》)
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
④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李白《古风》)
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诗句是不是运用了比喻的辞格。
例①中的“龙城飞将”是指汉代名将李广。“龙城”是汉代右北平郡所在地,《史记·李将军列传》说:“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李广骁勇善战,胆识过人,令匈奴闻风丧胆,它在担任右北平太守时,匈奴一直不敢贸然进犯。王昌龄有感于唐代边境战事不断,“师劳力竭,而功不成”,均因“将非其人之故”(清·沈德潜《说诗晬语》)而怀古抒怀,应属“用典”,不是比喻。
例②中的“和烟和雾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两句诗指卖花翁把鲜花送入富贵人家。“和烟和雾”,形容花刚采摘下来时缀着露珠、冒着水气的样子,极为新鲜可爱。许氏与史氏分别指宣帝许皇后家和宣帝祖母史良娣家,他们都是住在宫城以内当时最有势力的皇亲国戚。这里的“许史”借指权势显赫的豪门世族,是用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物的专用名称作借体代替本体事物的名称,应为“借代”。
例③中的“旧时”是指公元4世纪司马氏的东晋王朝,“王谢”则是与司马氏共同支撑半壁江山的两大权门士族——王导、谢安,两家府第就在朱雀桥边的乌衣巷里。因此,这乌衣巷便成为显赫一时的所在,当年那朱门华厦、车马喧嚣的盛况,完全可以想见。然而,时过境迁,4个世纪以后,这里却是一派衰颓景象。“旧时王谢”的盛景早已烟消云散了。诗人赋予燕子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从中寄托了今昔沧桑、世运无常的感叹。这里的“王谢”是实指,不是比喻。
例④中的“洗耳翁”指许由。据说尧曾想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但不接受,还认为这些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就去水边洗耳。尧是圣贤,跖是盗贼。两句诗的意思是说,世上没有了像许由那样不慕荣利的人,谁还能分得清圣贤和盗贼呢!(这里的“像”表示举例,并非比喻。)诗人鄙夷地把恃宠骄恣的宦官和鸡童等小人看成是残害人民的盗贼。同时也暗刺当时最高统治者腐朽昏庸,错勘贤愚。前句用典,后句是用借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以上4例都不是比喻。比喻是在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时,用同它有相似点的别的事物或道理来打比方。构成比喻必须有两个事物,这两个事物必须是“不同类的或者是本质不同的事物”,或者说“必须在整体上极其不相同”(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只是取其某一相似点,以引人联想。姚文革同志把以上4例看成“借喻”,恐怕是只看到句子中实指的人物和虚指的人物之间有相似点,而忽略了他们是同类事物了吧。由此看来“以人喻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背离了比喻的性质。
至于借代和借喻的异同,姚文在理论上已有精辟的论述,笔者不想徒费笔墨。这里须要提醒大家的是,理论上能说清的道理,未必就意味着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具体分析实例时,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借喻和借代在难以界定的情况下,一般可采用“转换”法,看它能否转换成明喻的形式,借喻可改为明喻,而借代则不能。如前例中的“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尧”和“跖”是借代还是借喻呢?如果是借喻,采用“转换”法就该说为:“德才兼备的圣贤像尧”,“盗贼像跖”。这显然不符合原意;即使可以这么说,“像”也不表示比喻关系,因为前项“圣贤”、“盗贼”和后项的“尧”、“跖”都属于“人”这一同类事物,不符合比喻的构成条件。
用典和比喻不能混为一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给用典下的定义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借助过去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把用典分为两种,即“举人事以征义”和“引成辞以明理”,前者就是“用事”,后者就是一般说的“用辞”。“用事”就是通过引用故事对作者要表达的思想起一种类比和引发的作用,使意义表达得更形象、更深刻;“用辞”主要在于引用现成的辞语,以证明一种事理或用以创设一种意境。概括地说,用典就是借古说今。借古是艺术手段,说今才是作者的目的。“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借赵国良将廉颇因遭谗害终老未用的历史故事,来暗示自己长期遭受南宋朝廷冷落、排挤、猜忌的际遇,抒发华年虚掷、抱负成空的苦闷。许由的故事被引入诗中,也是诗人“借他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罢了。
笔者从《高考语文考试说明》得知,高考语文考查八种常见修辞格,其中比喻又是考查的重点,历年高考经常和句式仿写、修改病句等题目样式结合在一起,考查学生的语言操作能力。考查要求是能够正确运用。除了要把握比喻的特点、类型以外,要谨防比喻的误用。
(作者通联:江苏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本文为全文原貌未安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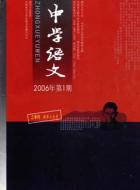
- 对《语文课程标准》的三点异议 / 朱绍禹
- 贺信贺电选登 / 佚名
-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 田 水
- 给语文教学插上人文和理性的双翼 / 鲜志英
- 诗歌教学:从技术走向艺术 / 邓 彤
- 语文教学中的对话自由与文本限制 / 张国光
- 教师设置层级话 / 李建芳
- 浅谈文言文的“教学境界” / 栾合明
- 细节有 / 陈成龙
- 巧借插 / 谢校青
- 章回小 / 王守诚 石翠青
- 九年级(下)第二单元教案 / 张桂霞
- 解读“朦胧” / 李仁甫
- 朗读·品读·赏读·背读 / 杨智慧
- 润物有声 / 屠琼轶
- “丰富”在记叙类文体中的整合 / 何启沪
- 品诗,切莫买椟而还珠 / 吴国梁
- 《〈宽容〉序言》精神新释 / 谭志鸿
- 一篇礼教的经典对话 / 李金焕
- 《荷花淀》人物的呈示方式 / 罗秉相
- 也谈古典诗歌中的比喻 / 韦荣瑞
- “阿Q也是幸福的”吗 / 曾祥奎
- 给《范进中举》中的“亲切”补注 / 欧阳炎中
- “白蘋洲”解 / 倪 岗
- 《屈原列传》“称、道、述”注释我见 / 王 珏 程洪艳
- 作文命题的新形式——感悟型作文 / 丁如泉
- 例谈“现代文阅读”中的失误及对策 / 尹 彪
- 略说漫画题的解答方法 / 邓明根
- 做标点题的几个小窍门 / 张永俊
- 王岳川例说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 林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