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期
ID: 355651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期
ID: 355651
《荷花淀》人物的呈示方式
◇ 罗秉相
小说把塑造人物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世界文学史上著名人物形象主要是由小说提供的。为此,小说可以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人物。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否成功,一要看人物性格的内涵是否丰富深刻,二要看塑造人物所运用的艺术技巧是否独特。孙犁表现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不像情节小说,通过设置叙事圈套,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展现极富动作性、冲突性的生活场面来塑造人物形象,情节中没有了刀光剑影、炮火连天和血肉横飞,淡化了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而把紧张的战斗情景和日常生活情趣糅合起来写,充满了诗情画意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篇小说也不像性格小说,把刻画人物个性放在叙述的中心地位,而是运用了中国写意画的技法,不求形肖,但求神似,在温情、优美、精致的水乡景观中,展现了冀中儿女身上那种动人的人情美、人性美。
那么,这批艺术群像是如何逐步呈示在读者面前的昵?
首先,是借助环境烘托。作品一开篇,就把读者带入一个月白、风清、湖光、荷香的如诗如画的环境中,优美的描写最终聚焦在“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作者精细的笔墨所准确勾画和展示的月下织席图,清新、明朗、美丽,简直就像神话一般,又像一首赞美诗。图中的主人——水生嫂的神态,俨然一座圣洁的塑像,再加上水生嫂织席的细节,就把一个勤劳淳朴、聪明秀逸、温顺善良的女性形象初步展现在读者面前。
环境不仅烘托了人物,随着情节的发展,还映衬了人物的性格。换句话说,就是当自然环境和人物形象已完全融为一体时,自然景色就成为人物形象的有力烘托,成为人物性格的映衬,使人物性格更鲜明地表现出来。如当她们探夫未遇回家时,作者描绘了大淀日午的明丽秀媚的水天景色:晴空、和风、微波、稻香、芦苇、菱角,一切都那么和美,那么恬适,这与妇女们那种爽朗、乐观的性格正相适应。
此外,还用景物描写来象征人物的心理情感。古人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自然景物虽然是非人的东西,但生活其间的人物则有着丰富的情感,于是人的情感往往外化、投射到自然景物中,使自然景物也染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成为人物心理的象征。当她们逃进荷花淀时,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壮美的荷花图。荷叶多得“一望无边”、“密密层层”,朴素而豪放;荷叶的姿态像“铜墙铁壁一样”,又给人以雄壮、恢宏、威严而不可侵犯的美。此外,作者还用简洁明快、质朴自然的语言,把荷花喻为“监视白洋淀的哨兵”,使人们从中感受到战争岁月里荷花淀的荷花,又具有一种独特的刚烈激荡的美,而这正是她们同仇敌忾心理的反映和内心深处对战争早有准备的真挚情感的流露。不仅如此,对荷花形象传神、充满寓意的描写,还在暗示着白洋淀妇女的成长前途——“粉色”的荷花都成为了“监视白洋淀的哨兵”,昔日粉妆的女人们,也将成为保卫白洋淀的战士。
我们说《荷花淀》是诗体小说,这取决于小说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作者深谙那一方水土。在看似轻描淡写中表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由此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的“荷花淀派”。而环境描写最终是为人物塑造服务的,小说就是这样,运用轻柔、清丽的语言,使诗化的景物有力地烘托了人物形象的性格状态和思想风貌,并使人物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又与整个水乡环境的自然美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其次,随着情节的发展,运用对话和细节描写来展示女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示人物形象。《荷花淀》的情节具有淡化的特征。但是淡化情节,不是没有情节,淡化的是战争中的残垣断壁、硝烟烈火和血污泪痕。这就是这篇小说的情节的特征。作者曾说过:“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但作者依然在自己精心设计的生活片段和场景中逐步展示了人物形象。
这就是小说《荷花淀》人物的呈示方式:借助环境的烘托,借助人物语言和细节的点染,使人物形象丰满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一人物群像中,孙犁着重渲染的是人性在抗战时期根据地这一新的社会环境里的美好呈现和升华。正是这美好的人性,支撑了艰苦的抗战,也正是这美好的人性,使艰苦的抗战充满了温馨。谁如果想要摧毁这美好的人性,人性就会给以最坚决的回击,并在这回击中,使自己得到升华。通俗地说,就是她们在对丈夫的小“牵挂”的基础上,上升到对白洋淀、对家乡、对生活、对国家民族的大“牵挂”。你看,作品开头写的是“湿润润”、“柔滑修长的苇眉子”在女人“怀里跳跃着”,结尾则写“她们学会了射击”,女人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这正是对人性、对人性升华进行赞颂的两幅生动、美好的图画。人性的美好,是人生存在的根本意义。比起人性美好的保存来,那外在的压迫、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它只能使人性显示出更滋润、更神圣的光泽来。这正是《荷花淀》用主要笔墨通过青年女性着重写人性的美好,而对战争的严酷反而不去着重强调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荷花淀派”作品清新优美又充满着一种内在的坚定力度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荷花淀》虽然写得优美抒情,但我们读了之后,依然会想到遍地战火中的厮杀,体味到战争中的民众那内心的重压和创伤。在清丽的词句中,也能读出苦涩、沉重和思考。这种味道,比读那种慷慨悲歌式的战争故事,似乎更持久强烈。这正应了中国古代文论《姜斋诗话》道出的一条艺术真谛:“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孙犁是深谙艺术创作中的辩证法的。难怪老作家方纪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社读到《荷花淀》原稿时,“差不多跳了起来”,并“把它看成一个将产生好作品的信号”。
(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四明中学)
本文为全文原貌未安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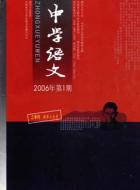
- 对《语文课程标准》的三点异议 / 朱绍禹
- 贺信贺电选登 / 佚名
-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 田 水
- 给语文教学插上人文和理性的双翼 / 鲜志英
- 诗歌教学:从技术走向艺术 / 邓 彤
- 语文教学中的对话自由与文本限制 / 张国光
- 教师设置层级话 / 李建芳
- 浅谈文言文的“教学境界” / 栾合明
- 细节有 / 陈成龙
- 巧借插 / 谢校青
- 章回小 / 王守诚 石翠青
- 九年级(下)第二单元教案 / 张桂霞
- 解读“朦胧” / 李仁甫
- 朗读·品读·赏读·背读 / 杨智慧
- 润物有声 / 屠琼轶
- “丰富”在记叙类文体中的整合 / 何启沪
- 品诗,切莫买椟而还珠 / 吴国梁
- 《〈宽容〉序言》精神新释 / 谭志鸿
- 一篇礼教的经典对话 / 李金焕
- 《荷花淀》人物的呈示方式 / 罗秉相
- 也谈古典诗歌中的比喻 / 韦荣瑞
- “阿Q也是幸福的”吗 / 曾祥奎
- 给《范进中举》中的“亲切”补注 / 欧阳炎中
- “白蘋洲”解 / 倪 岗
- 《屈原列传》“称、道、述”注释我见 / 王 珏 程洪艳
- 作文命题的新形式——感悟型作文 / 丁如泉
- 例谈“现代文阅读”中的失误及对策 / 尹 彪
- 略说漫画题的解答方法 / 邓明根
- 做标点题的几个小窍门 / 张永俊
- 王岳川例说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 林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