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期
ID: 355650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期
ID: 355650
一篇礼教的经典对话
◇ 李金焕
人教版高一册语文课本《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是选自《论语》中的一篇经典对话案例,从鲜活的对话艺术中闪射出孔子礼教思想的一束光辉,昭示千秋。
作为教学文本,学生对全篇的行文思路“问志——言志——评志”不难把握。对篇中多数字、词、句的疏通,以及基本意思的理解,学生也完全可以在课前自主阅读时看教材中的详细注释,能够无师自通。乃至对孔子与四弟子闲坐对话时所显现出来的平等、和谐、轻松、畅快的氛围,学生会在获得整体感受后,从而对“侍坐”境界产生无限神往的激情,进而引发深入探究课文的求知欲望。教学时应引领学生的这股激情和欲望,进一步探究对话中的深层次意蕴,挖掘对话中的新生成。为此,笔者认为要读懂本篇课文就应该明辨四弟子“言志”与孔子施以“礼教”在文中的语脉、语流,从而意识到这篇对话录既是“言志篇”,更是“礼教篇”。
《侍坐》从开篇“子曰”至“吾与点也”,记述了孔子与四弟子计五人在场的对话,对话的话题是在孔子循循善诱之下,四弟子畅谈理想、抱负,即“各言其志”,类似今天的理想教育座谈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弟子“各言其志”后,“座谈会”就到此结束了。然而精明、细心的曾皙却留了下来,单独问孔子:“夫三子者之言何如?”从孔子“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的回话语气来看,他没有将话题延伸下去的预设。但是,曾皙还是要问个究竟,分“三子者”为一个一个的探究对象,抱着请教的心态问孔子。按照前面对话的顺序,先是问:“夫子何哂由也?”这一问是针对前文有“夫子哂之”一笔而发的。哂:微笑。这种表情不同于其他笑容,最难让人明白笑中之意。曾皙为了弄清孔子“哂由”的奥妙,故发此问。孔子回答:“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从当今一问一答的考试规范来看,孔子的这句话不失为“夫子何哂由也”一问的标准答案。但孔子毕竟不是考生,也毕竟不只是一个教书匠,而是一位教育家,至少是那个平等对话场景中的首席。孔子的这句回话,是从更高的层面来评价弟子的“言志”,将“言志”这一话题转移、提升到“礼教”的层面。就这篇文本而言,孔子的这句话是对话过程中的一种新生成,我们对句中的“礼”与“让”两个关键词不可不明辨。
《论语·里仁篇》:“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又怎样对待礼仪呢?”)这段话的“礼”与“礼让”是两个不同含义的概念:礼,指礼仪、礼节、礼制等;礼让,指谦让的态度。在孔子看来,“礼让”与“礼”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关系,两者密不可分,礼必须以礼让为本质内容;如果不礼让,那些礼仪只是徒有形式,也是不可取的。《侍坐》所言之“礼”与《里仁篇》的这个“礼”是同一概念,《侍坐》所言之“让”与《里仁篇》的“礼让”是同一概念。孔子一贯主张“以礼治国”,所述多多。《里仁篇》中说的“以礼让为国”,与《侍坐》中说的“为国以礼”别无二致,只不过立论的角度不同,都是孔子礼教思想的体现。明乎此,则全篇对话的语脉、语流就能圆通。下面就“哂由”、“与点”以及文末的两问两答——课文中的三个难点——略陈浅见。
“哂由”:
孔子笑子路,是在肯定子路志向的前提下夹带着些许缺憾的意味。从“言志”的角度来审视,孔子对四弟子所说的“志”都是肯定的,没有厚此薄彼的倾向。子路性格直率,第一个抢先发言,自负有治理“千乘之国”的才干。孔子对这样的学生,只会暗自高兴,绝无批评的念头。他对子路的那种微笑,只是一种缺憾的表情流露,似乎是暗示子路的话语还缺少一点什么。要不是曾皙穷问,这种缺憾至今还是一个谜,尚无人知。由于曾皙一问再问,孔子才把藏于内心的谜底说了出来:“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原来孔子不仅是在启发弟子们“言志”,而且是在用一条标尺来审视弟子们的“言志”,这条标尺就是“礼教”。在孔子看来,谈治理国政,就要讲礼治,子路的发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言词中缺乏礼让、谦逊的态度,所以笑了笑。解读孔子的这句评价性言语,要揣摩特定语境中的分寸感,不要把孔子的这句话当成背后对子路的严厉批评来看待。
“与点”:
孔子为什么赞赏曾皙?至今似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法不一,问题是对曾皙述志的文字解读不同。“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是一幅社会图景,还是一幅礼祭场面?如果看成是社会图景,太平盛世的景象就忽尔而至:“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了。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青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儿回来。”(见人教版《教参》)多么诗意般的解读,却是游离开全篇断章取义而已。且不说不合时令(暮春尚寒)地到沂河里洗澡、到舞雩台上风干身子实在令人不可理解;孔子说“吾与点也”,到底赞赏曾皙什么呢?更是令人不可捉摸。其实,曾皙述志的文字,写的是礼祭场面,实为在沂水边上的舞雩台举行礼祭仪式的场面:暮春时节,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均为祭祀仪式的乐人)涉过沂河(浴,训涉;或作沐浴净身,亦通),到舞雩台上唱歌祭祀(风,训唱歌),并向祭神馈祭牲品(归,训馈)。曾皙的一番述志言词,最是符合孔子礼教的尺度,所以喟然赞叹。
文末的两问两答: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里的两问两答是曾皙问而孔子答的对话方式,一般没有引起众多解读者的注意,大概都认为这两问两答不会产生疑义吧。其实,如果也只从“言志”的角度来审视,这两问两答是可有可无的,是一条赘余的尾巴。试想,曾皙的两问是在明知故问,明明知道冉有与公西华都讲到了治理邦国之事却还要问孔子;孔子的两答几乎是用反问的语气对曾皙的所问进行复述。改变两问两答的语气,问也好,答也罢,都是说冉有与公西华讲到了治理邦国之事,这等于白问白答。再者,两问两答之前,话题已转移、提升到礼教的层面上,怎么又转回到言志这个层面上呢?这中间的语脉、语流是否受到阻绝,而产生不连贯的语病?如果从礼教的角度来审视,这两问两答则非有不可,而且与前句连贯畅通。这两问两答承接上一组对话的语意,旨在表明冉有和公西华在述说治理邦国之事的同时,还涉及到礼与礼让的问题。解读这两问两答,不能平板地译释字面,应仔细品味话外之音,言外之意。曾皙的两问,是说冉有、公西华与子路一样,不也是表述治理邦国的事吗?而你(孔子)为什么只笑子路,而不笑他二人呢?孔子的两答是说,不能因为知“礼”与“让”的冉有、公西华与子路一样表述了治理邦国之事就也要我笑一笑嘛!笑的原因,不在表述治国之志,而在是否懂得用来治国的礼与让。这就是两问两答的隐含未露的真正含意。
三处难点解读,都要用孔子的礼教思想去破解,其间的阻塞就会豁然洞开,别有天地。
(作者通联:湖北武汉汉口铁中)
本文为全文原貌未安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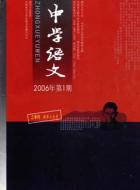
- 对《语文课程标准》的三点异议 / 朱绍禹
- 贺信贺电选登 / 佚名
-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 田 水
- 给语文教学插上人文和理性的双翼 / 鲜志英
- 诗歌教学:从技术走向艺术 / 邓 彤
- 语文教学中的对话自由与文本限制 / 张国光
- 教师设置层级话 / 李建芳
- 浅谈文言文的“教学境界” / 栾合明
- 细节有 / 陈成龙
- 巧借插 / 谢校青
- 章回小 / 王守诚 石翠青
- 九年级(下)第二单元教案 / 张桂霞
- 解读“朦胧” / 李仁甫
- 朗读·品读·赏读·背读 / 杨智慧
- 润物有声 / 屠琼轶
- “丰富”在记叙类文体中的整合 / 何启沪
- 品诗,切莫买椟而还珠 / 吴国梁
- 《〈宽容〉序言》精神新释 / 谭志鸿
- 一篇礼教的经典对话 / 李金焕
- 《荷花淀》人物的呈示方式 / 罗秉相
- 也谈古典诗歌中的比喻 / 韦荣瑞
- “阿Q也是幸福的”吗 / 曾祥奎
- 给《范进中举》中的“亲切”补注 / 欧阳炎中
- “白蘋洲”解 / 倪 岗
- 《屈原列传》“称、道、述”注释我见 / 王 珏 程洪艳
- 作文命题的新形式——感悟型作文 / 丁如泉
- 例谈“现代文阅读”中的失误及对策 / 尹 彪
- 略说漫画题的解答方法 / 邓明根
- 做标点题的几个小窍门 / 张永俊
- 王岳川例说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 林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