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9期
ID: 137579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9期
ID: 137579
百花齐放的中国革命历史小说
◇ 李翠宏
【摘 要】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上,涌现出了大批的革命历史小说。由于作家生活经验和艺术想象的差别,也由于他们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不同,因此,革命历史小说的形态也各不相同,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革命历史小说百花齐放的局面成了“十七年文学”画廊中的一道重要风景,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史 革命历史小说 百花齐放
特别的年代,迫切需要文学为之摇旗呐喊。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也需要一些文学作品,总结自己的辉煌,歌颂自己的英雄,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一种道德肯定和理想膜拜。因此,截取一片微澜、一朵浪花,加以精细挖掘和描绘,以反映时代风貌的革命历史为题材、歌颂革命先烈为主题的创作成为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一大亮点。同时,由于作家生活经验和艺术想象的差别,也由于他们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不同,因此,革命历史小说的形态也各不相同,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一、史诗性的把握与追求
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大都追求一种史诗的境界,以实现“载道”的理想。同时,批评家们也善用“史诗性”来衡量作家作品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当时就有批评家指出:对于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的。现在我们需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迹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到了50年代,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强烈,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已成为有抱负的作家的崇高责任。“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的本质”、结构上宏阔的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融合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如《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以及《三家巷》、《苦菜花》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追求。
在当代,最早被评论家从“史诗”的角度评价的长篇小说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这部小说取材1947年3月到9月的陕北延安故事——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领导军民主动放弃延安,后又收复延安。作者从“战争全局”的把握来关照具体的、局部性的战事和人物的活动,是作品的总体构思。小说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和持续的紧张节奏来着力塑造周大勇、李诚、王老虎等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并为英雄们布置了苦战、退却、流血、死亡等“检验”战斗意识的逆境,使小说自始至终保持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在虚构的艺术文本中,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1954年初版后,冯雪峰称它是“够得上称它所描写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
二、以“组织生产”的方式创作革命历史小说,以更分明、更强烈、更带象征性、更带人生哲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件和所赋予的种种含义
此类作品的首推之作应当为《红岩》,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并非是专业作家,只是书中所描写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幸存者。50年代,为配合当时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他们着手搜集材料,并在重庆、成都等地作过上百次的有关“革命传统”的报告,虽讲述的是真实的事件,但已经进入创作阶段。1956年底,他们把口述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出版了《在烈火中永生》。之后在这部“口述回忆录”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加工、提炼、修改,最终与出版社负责本书的责任编辑进行了细致讨论和修改,终于著成了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小说《红岩》。这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它的成功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是黑暗与光明交替的时刻,是新中国诞生的时刻。而《红岩》以对“革命”的更具纯洁性的追求来实现对这一历史时代的“本质”讲述。它以更分明、更强烈、更带象征性,也更带人生哲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件和所赋予的种种含义。小说的主要篇幅放在狱中斗争上,但同时也涉及中共在城市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并组织了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另一线索。作者刻画了大批英勇的革命者,如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他们被安放在两个政治集团、两种人生道路和两种精神力量的格局中。人物思想、性格、言行、心理的刻画不再存在任何幽深和曲折,彻底“透明化”。英雄人物的意志、信仰所焕发的精神力量,主要表现在敌人对其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下的坚定、从容和识见上。反面角色的狡诈、残忍、虚张声势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绝望。作品中将二者做了鲜明的对比,英雄的革命者的人生观和政治观在此中得到了强化和体现,表现出革命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而,《红岩》以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极大地影响六七十年代的小说、戏剧创作。
三、以讲述现实依据和讲述历史记忆的重点来强调创造“幸福的路”的斗争的艰苦和残酷,并在这样的背景上塑造经过血与火检验的英雄形象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革命者的血汗与泪水之上的,因此,表现革命英雄的高大形象也成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主流,而这类革命历史小说主要以短篇和中篇为主。如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党员登记表》等,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三人行》等,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等,这些作品都是描写了革命斗争的艰苦与残酷,塑造了英雄的高大形象和经历血与火检验后他们那坚定的精神信仰。
作家茹志鹃也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人物,其195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就是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作。她的有关战争生活的小说,在叙述上以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联的“封闭”方式展开,内在的“回忆”动机和叙述线索,不难辨识,它们是作为参与生活“统一性”的组织而被索取和重新构造的。《百合花》便是这样,在重重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这一表现提供了了解作者回忆“革命历史”的心理动因的线索,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写作之后时隔二十年的一种阐释。
《百合花》写的是发生于前沿包扎所的插曲,一个出身农村的军队士兵,与两个女性在激烈战斗时的情感关系。这个短篇在当时受到了肯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在50年代短篇艺术上所达到的示范性成绩。它注重构思和剪裁、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的很好结合、结构的“细致严密”且“富于节奏感”,以及“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和“前后呼应的手法”——这些把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短篇杰作看作范本的批评家的理想。文章把战士的崇高品质和军民的鱼水关系作为阐释框架,既“窄化”了阐释的空间,又遮蔽了人物之间模糊暧昧的情感,使其在当代题材的严格规范中,不被质疑而取得合法地位。这样的创作方法使得作者在“文革”中也没有被列入“批判”的行列。作者把政治效果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有短篇小说的发表。
四、既是写“革命历史”又是写知识分子的“成长”
在当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像这样既是写“革命历史”又是写知识分子“成长”的小说实在不多见,而在这一时期却涌现了杨沫的《青春之歌》和高云览的《小城春秋》等作品,在众多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显得格外新颖。两部小说都是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取得成功。小说强调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青年才能成长成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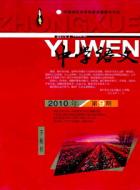
- 对话,引发意义的精彩生成 / 李 颖
- 对提升语文学科教学品质的几点思考 / 钱为民
- 对高中语文目标教学法的思考 / 何 燕
- “知行式”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 / 孙秀丽 刘亚莉
- 高中语文选修课课堂范式的理论研究 / 高金章 陈俊江
- “行”的风帆,“知”的彼岸 / 程 鸣 吴 振
- 信息技术与情感教学的整合 / 汤见光
- 《选读》教学策略谈 / 蓝爱青
- 充分利用课文资源 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 吴生鸿
- 一方论坛,一派生机 / 纪明华
- 发挥“三主”意识,构建有效课堂 / 吴寅虎
- 盘点新课程 深化新课改 / 陆三炳
- 关于《选读》主题写作的设计 / 邵淑英
- 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艺术简论 / 杨顺福
- 阅读教学中终身阅读习惯和能力培养初探 / 李冬梅
- 浅论新课标理念下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韦 佳
- 语文课堂教学调控艺术摭谈 / 黄小波
- 浅谈如何有效引导学生独立深入阅读文本 / 徐 静 童康怀
- 语文教学与素质教育的理想 / 湛承芳
- 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 郑泽谦
- 提高阅读教学对话有效性的途径 / 郑长安
- 语文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 马志红
- 高中语文课堂设疑的有效策略 / 邰雨春
- 如何通过阅读提高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 / 李丹丹
- 现代文阅读教学的终极目标 / 时广义
- 情景交融 拨动心弦 / 彭跃奎
- 如何有效开展农村初中生的课外阅读 / 万小春
- 切莫犹抱琵琶半遮面 / 卢文锋
- 决绝之美 / 吴晓明
- 自创论据 自证观点 / 姚联碧
- 谈谈小型研究性学习在小说鉴赏中的运用 / 王华清
- 析说韩愈的《师说》 / 仲乃亨
- 对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作文教学内容的实践和思考 / 丁立芬 胡锡良
- 杜十娘之死,谁之过? / 刘冰霞 叶芬芳
- 《兰亭集序》究竟表现了王羲之怎样的“生命观” / 萧兴国
- 闲话古典诗词中的“闲” / 刘有福
- 作文教学的治本之策 / 邹平洲
- 求生舍身皆是“义” / 张玉连
- 语文课堂培养学生写作个性的探索 / 孙 槐
- 猿啼声声催泪滴,人生茫茫寄真情 / 彭金华
- 黛玉进贾府: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 张万弘
- 关注生活 写出真情 / 褚丽萍
- “也”“矣”“哉”中 / 王双凤
- 诗歌神话中的海子 / 常风琴
- 关注社会 积淀文化 抒写思考 / 金 凌
- 释“还来就菊花” / 项昉初
- 古诗教学天地宽 / 鲁 明
- 借助“说”提升“写”的能力 / 朱 简
- 瞻仰历史楷模 吐露抑己心声 / 梅 岚
- 古诗教学,我们忽略了什么? / 唐 缨
- 逆向立意 别有天地 / 洪桂云
- 百花齐放的中国革命历史小说 / 李翠宏
- 《史记》人物刻画的映衬艺术 / 朱延生
- 如何打开议论文的写作思路 / 蔡晓鹏
- 从《三国演义》看儒家的治国理想 / 陈水献
- 水状的幸福 流动的风景 / 李 梅
- 勿再以现代化的名义戕害学生 / 顾 勇 董旭午
- 孔圣人原来如此可爱 / 胡赛娇
- 浅谈农村中学高考作文应对策略 / 孙卫华
- 用心托起明天的太阳 / 张俊显
- 语文需要心灵瑜伽 / 黄莹莹
- 材料作文审题立意例析 / 王维忠 翟凤举
- 能力立意 现实指向 稳中微调 过渡课改 / 王小红 赵承跃
- 不积水,焉负舟 / 任晓歌
- 高考现代文学作品阅读指津 / 邹家芝
- 语文教师就是一本教科书 / 胡志峰
- 怎样提高“文学类文本阅读”的答题效率 / 王文娟
- 教师,请慎用你的评价 / 钱永秋 李富春
- 象征性作品的类型\意义和结构 / 杨忠平
- 偏科:语文课堂中的旧话重提 / 何长俐
- 了解高考阅卷评分细则提高文言文翻译复习效率 / 张世东
- 语言高效表达的必由之路 / 吴成钦
- 拥有一对隐形翅膀 / 陈 芳
- 浅议高考满分作文与零分作文 / 余四海
- 深入题后 独辟蹊径 / 王晓娟
- 议论味与完全段:高考议论文取胜的基础 / 杨志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