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5期
ID: 136558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5期
ID: 136558
怎样理解《屈原列传》中的“曰以为”
◇ 罗献中
《屈原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馋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在这段话中,第二个“曰”字和“以为”连在一起,同时出现,令很多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怀疑这个“曰”字可能是衍文,但又缺乏依据。课本对此未作注释,很多教师也无法向学生作出解答,于是往往这个问题只好作为一个疑点搁置下来。
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对此处“曰”和“以为”的连用持问题说。如金代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中认为“曰以为”有误,清代张文虎在《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则怀疑“曰”是衍文等等。但这些学者同样只是存疑,没有确切的依据。
那么,这里的“曰”、“以为”连用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否果真存在衍文的问题?笔者多方搜寻有关研究资料,发现今人学者吴金华和富金壁在各自相关论文中论及了这个问题,觉得各有一定的道理。两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都认为“曰”、“以为”的连用是古汉语中的一种语言现象,不存在衍文或其它问题。
吴金华在《古文中的同义词连用》(江苏教育出版社《古文献研究丛稿》)中认为,汉语同义复词虽然以双音结构为常例,但古文中也有不少与同义复词相似的结构,即由同义词连用而形成的词组或短语。“曰以为”就是其中之一,由单音节词“曰”和双音节词“以为”并列而成,在句中充当谓语的成分,其用法相当于“曰”。无独有偶,吴金华还从《史记·三王世家》中举出了“曰以为”的另一个例证:“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并指出,“曰”和“以为”各自单用时,既有相同之义,又有不同之点;但是,当两者连用的时候,一般都是泛指大意而不强调其中的差别。他认为,古人连用两个、三个乃至四个同义词,无非是为了完足语义与强化语气,这种现象反映了古代语言中的某些真实情况;可以推断,这类迭床架屋式的词组和短语,在古人口头语中习用已久。
富金壁在《古代汉语中的“V+以为”结构》(北大中文论坛,2004年5月23日)中认为,古代汉语中有一种“V+以为”结构,其整体意义就相当于“V+以为”。其中“以为”用来引出见解、观点,“V”则多说明其表达方式。“V”多是表言语行为的动词,他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日知录》等文献中,列举了“V+以为”结构的大量书证。例如:“及绛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系清室。”(《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莽故大司马,辞位辟丁、傅,众庶称以为贤。”(《汉书·何武传》)“刘淑……上疏以为宜罢宦官,辞甚切直。”(《后汉书·党锢列传》)“及曜自攻洛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晋书·艺术列传》)等等。《三王世家》和《屈原列传》中的“曰以为”也属于这种结构形式。他认为,“V+以为”结构比较紧密,在古汉语中比较活跃,史书中尤为习见。
富金壁进一步指出:“V+以为”结构既然比较固定,那么,“V”与“以为”之间一般不宜点断。他针对《屈原列传》在颇多版本中,“曰以为”被点断,“曰”字被定为衍文甚至被径直删除的现象,明确指出:“实际上,这个句子乃是‘V+以为’结构较早的、最为典型的例证。‘曰’不可能是衍文。……有人认为‘曰’与‘以为’语义重沓,这是误解:‘曰’正说明了‘以为’所引出见解的表达方式。且‘曰’之有无,表达效果不同:有‘曰’则生动形象,无‘曰’便平淡呆板。这正是‘V+以为’结构在表情达意方面的妙用。”吴金华也认为“曰以为”不能点断割裂:“在‘曰’字后逗断,不仅‘以为’二字成为多余,‘也’字也无处存身了。”
总之,吴、富二位学者的研究虽然视角不同,但结论相似,都认为“曰以为”之类说法本是古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之一,其中并没有衍文,且不宜点断。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参也可以适当吸收或介绍这些研究成果,作为中学师生释疑解惑的参考。当然,相较而言,笔者更认同富金壁先生的观点,因为其视角更为新颖独到,论据更为周全充分,因而论证更有说服力,更易于为学界所接受。
[作者通联:河南固始教师进修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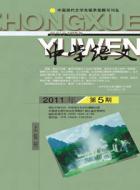
- 语文学案教学课堂基本模式探索 / 倪岗
- 考的内容要值得教 / 胡根林
- 教学即评价 / 胡根林
- 阅读教学应建基于普遍性的生活经验 / 王革虎
- 浅谈教学中对文本的适度超越 / 钟义民
- 强化文本主体意识提高文本解读能力 / 张震涛
- 由“末”逐“本”优化语文课堂提问语言 / 张卫红 魏爱平
- 抓住文章亮点,实现文本价值 / 张孟光
- 2010年度语文理论研究热点追踪(下) / 温立三
- 立足当代社会 拓展思辨空间 / 潘涌 王婷
- 自语:对语文本体的文化阐释 / 曹明海
- 种树者郭橐驼与敲钟人卡西莫多的美学共性 / 肖科
- 崇高感与悲剧感的完美结合 / 杨仕威
- 超级尴尬:高中生找不到句子的谓语和宾语 / 董旭午
- 智慧闪耀 千古至文 / 龙健
- 浅谈高三科技类文章阅读题训练的基本问题 / 朱江
- 《发现》:红色意象的文化意蕴 / 林忠港
- 语文教育史学研究的新篇章 / 李蕴哲
- 怎样理解《屈原列传》中的“曰以为” / 罗献中
- 追求功利同样渴望华彩 / 董伟永
- 课外小组研读“文化论著”方式的再思考 / 陈桂春
- 浅谈高中学生语文学习心理的调试 / 邰雨春
- 用陌生的眼光来审视世界 / 姚芳
- 虚笔不虚 美在自然 / 董辉 饶倩
- 只缘不解“赋家语” “鼎铛玉石”到如今 / 俞万所 张悦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