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5期
ID: 136605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5期
ID: 136605
只缘不解“赋家语” “鼎铛玉石”到如今
◇ 俞万所 张悦群
最近读到谭小红老师对聂剑平老师《如何理解“鼎铛玉石,金块珠砾”》一文(见《语文学习》2010年第5期)提出批评的文章《有关“鼎铛玉石,金块珠砾”的一点疑问》(见《中学语文》2010年第11期),不禁颇有感慨:杜牧《阿房宫赋》中“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如何理解?其中到底存有什么语法现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争论至今,竟然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说,实在令人遗憾。
综观几十年来的争论情况,大体可分为四种说法。
第一,认为“玉石”的“玉”是意动用法。(由于“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内部结构关系四组——“鼎铛”“玉石”“金块”“珠砾”——一致,下面分析四种说法下仅以“玉石”为代表)意动用法是主语认为宾语具有怎样的性质的一种词类活用方式,通常解释成“把……看作……”“认为……怎样”。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中的“小”,就是“认为(鲁国、天下)小了”的意思;再如“(云)友风而子雨”中的“友”和“子”,应是“把(风)当作朋友”和“把(雨)看作自己孩子”的意思。而认为“玉石”是意动用法的人,正是看到了一般课本注释中的“把……看作……”的字眼,就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但是,如果“玉石”是意动用法,那么“玉”与“石”则是意动动宾结构。而活用作意动的只能是前面的“玉”,后面“石”只是其宾语。按照意动用法的特点,参照“小天下”“友风而子雨”的解释,“玉石”只应该解释为“把石子看作宝玉”才对。可这个意思和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把宝玉看作石子”恰恰相反。
第二,认为“玉”是名词做状语,解释为“把宝玉”;“石”是名词作动词,解释为“看作石子”。把两者组合起来,“玉石”就是“把宝玉看作石子”,属于偏正结构。其意虽符合一般教材或教参的译文(如苏教版必修二第72页“把宝鼎看做铁锅,把美玉看做石头,把黄金看做土块,把珍珠看做石子”),似乎能自圆其说。然而,如此解释“玉”和“石”,其词义完全是从课本注释或教参翻译的意思中倒推出来的。而根据文言文“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力求‘信、达、雅’”的原则,正确的做法应相反:译句应建立在解词的基础上,句子意思应来源于其中词义的组合。
解读古汉语词类活用有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简洁。所有词类活用只是为了表义的需要,临时改变句中某词的类别,暂且增加句中某词的意思,可谓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尽量少用,实在必须用才用。那么,又何必要把组合的两个(其实是八个)名词都理解为活用呢?岂不是犯了“化简为繁、舍近求远”之大忌?
第三,认为“玉”是名词用作动词,解释成“把宝玉看(当)作”,“石”是名词,“石子”;“玉石”为动宾结构,意思是“把宝玉看(当)作石子”。这样的理解相比第二种说法,委实简明了许多,也吻合于一般教材、教参的翻译。可是,有些权威性教参在对“玉石”词类活用的理解上否定了“玉”是名词作动词的观点,而直接认为后面的“石”是名词用作动词。比如上海新教材(试用本)配套的《高中语文教学参考资料》第245页(“思考与练习”参考答案)在同样将“玉石”翻译为“把宝玉看作石子”后,明确指出“块、石、块、砾”“均为名词作动词”。不过,“玉”怎么讲?何以有“把宝玉看作石子”的翻译?仍然语焉不详。
第四,认为“玉石”是主谓结构。“玉”是陈述对象,“石”是陈述内容,名词作动词,解为“看作石子”。进而将“玉石”直译为“宝玉被看作石子”。可几乎没有一种教材与权威参考资料如此翻译。这只算是一种古怪的“硬译”。而且,在被动解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名词运用,也不符合“简洁”原则。
这种说法,其主要论据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君主,臣子要像臣子;父亲应该像父亲,儿子应该像儿子”)这八个名词所构成的四个主谓结构的分句。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主谓结构,类推出“玉石”等也是主谓结构。其实,“玉石”与“君君”大相径庭。一是“玉”与“石”是两个优劣对立的事物,而两个“君”是同一种人,不存在优劣比照;二是“金”与“块”是比喻关系,而两个“君”无论怎么说也不存在比喻关系。同时,如果把“玉石”看做主谓结构,那么“玉”与“石”是被动关系,“玉”是受事主语;而两个“君”则是非被动关系,前一个“君”系中性主语(既不是施事主语,也不是受事主语)。差别如此之多,差异如此之大,岂能进行类比推理?
上述四种说法是不是每一种说法都没有道理?不然。第一种说法倒值得注意。几乎所有教科书与教参资料都把“鼎铛玉石,金块珠砾”,译为“把宝鼎看做铁锅,把美玉看做石头,把黄金看做土块,把珍珠看做石子”,意动倾向非常明显。问题只在于“玉石”不是意动动宾关系,“石玉”才是意动动宾关系;因为“以石为玉”(即“石玉”)说不通,“以玉为石”(即“玉石”)才说得通。
“石玉”恰恰是“玉石”的颠倒,这种颠倒是否可行呢?如果可行,有什么奥秘可寻呢?如有充足的理由寻找到其中的奥秘,那么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韵文与一般文章不同,常常含有特殊的表达方式及其特殊的语言。近体诗讲究平仄、押韵或对仗,因而常常出现倒序、简省、跳脱等特殊的语言形式,俗称“诗家语”。诗有诗家语,词有词家语,曲有曲家语,赋亦有赋家语。韵文常常需要打破逻辑常规安排语序,以致次序颠倒。例如“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其中“英雄无觅”因平仄而颠倒了两个词语的组合次序。按照一般文章的语言组合,应是“无觅英雄”,但本词要求这四个字前两个为平声,后两个为仄声(“无”可平可仄)。所以,需要将“无觅英雄”颠倒为“英雄无觅”,这“英雄无觅”便是一种词家语。韵文中“倒序”的语句适于文体要求,便于口耳相传,宜于朗读,但不便于理解。如要理解,则需要改“倒序”为“顺序”,比如“英雄无觅”必须改为“无觅英雄”)。否则是“缘木求鱼”,无论怎样也理解不准,认识不清。
作为赋文,《阿房宫赋》是要押韵的。除了“也”“焉”等虚词煞尾的句子,本文全都押韵,或隔句押韵,或句句押韵。当然也不一韵到底,其间不断转韵(赋文是应该转韵的)。如开篇六个分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句句押韵(与现代汉语按韵母押韵不同,按韵部押韵)。接着四个分句转韵,“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隔句押韵,韵脚依次为“阳”“墙”。然后十个分句再转韵,除了“盘盘焉,囷囷焉”(不在押韵之列)隔句押韵,其韵脚依次为“阁”“啄”“角”“落”。
“鼎铛玉石,金块珠砾”所在的第三段,也是多次转韵的。一至三句每句押韵,韵脚为“藏”“营”“英”。(文赋不同于词曲,更不同于近体诗,押韵较宽,韵部相邻可押韵,也可以依据方言押韵)四至八句,隔句押韵,韵脚为“年”“山”与“间”。九至十三句文势达到高潮处,除了“秦人视之”中的虚词“之”(“之”在现代汉语中韵母巧与前后韵脚相同)句句押韵,韵脚为“石”“砾”“迤”“惜”。本应表达为“把宝鼎看做铁锅,把美玉看做石头,把黄金看做土块,把珍珠看做石子”意思的句子“铛鼎石玉,块金砾珠”,因为押韵需要,要将“石”与“砾”做韵脚,因而改为“鼎铛玉石,金块珠砾”。若不用这种“倒序”之语,这两句便不能与后面两句“弃之逦迤”“亦不甚惜”押韵。也就是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是因押韵造成的赋文语言,即一种“倒序”的赋家语。理解这“倒序”的赋文语言,需要将它改为“顺序”的一般语言形式,即把“鼎铛玉石,金块珠砾”还原为“铛鼎石玉,块金砾珠”。这“铛鼎石玉,块金砾珠”就是四组意动动宾结构,其中的“铛”“石”“块”“砾”为意动用法。两个句子也就自然译为“把宝鼎看做铁锅,把美玉看做石头,把黄金看做土块,把珍珠看做石子”,这正好与一般教材、教参的注释、翻译一致。
谭、聂二位老师可能不解赋家语,不清楚“鼎铛玉石,金块珠砾”系因赋文需要押韵而造成的“倒序”句,自然说它不符合“意动用法的典型语法结构”,因而否定其中的意动用法。聂老师另辟蹊径,认为“鼎铛玉石,金块珠砾”“极言宝物之多”,意思是“宝鼎像平常的铛一样(多),美玉像常见的石头一样(多),金子像普通的土块一样(多),珍珠像数不清的沙砾一样(多)”。但忽略了语意重心,误解了语境意义。“鼎铛玉石”早已是成语,一般工具书都解释为“视鼎如铛,视玉如石,形容生活极端奢侈”。其语意重心,是批评秦人挥金如土,穷奢极欲;而不是“极言宝物之多”。根据语境,上文说六国君主一代代从人民那里掠夺来若干财富,堆积如山;一旦他们国破家亡不能拥有,竟被秦国人运来大肆挥霍。于是杜牧用“鼎铛玉石,金块珠砾”极力铺陈其具体情形,然后顺势推出“弃之逦迤”之动作,再以“秦人视之,亦不甚惜”作结。其中隐含着强烈的谴责。如果仅仅理解为宝物之多,实为肤浅之论。就好像成语“挥金如土”一样,尽管也含有“(黄金)很多”的意思,但语意重心在浪费与奢侈。
谭老师认为“鼎、玉、金、珠”是名词动用,即“把宝鼎当作”“把宝玉当作”“把黄金当作”“把珍珠当作”,上文在第三种说法的解剖中亦已否定,在此不予赘述。
总之,不识赋文的特殊语言形式,不解“鼎铛玉石,金块珠砾”之中的“倒序”现象,不会把它改为“顺序”形式(即“铛鼎石玉,块金砾珠”),则无法解说其中的意动用法,还会造成一系列曲解与穿凿。比如有人把“鼎铛”“玉石”看成并列关系,把“金块”“珠砾”看成偏正关系(见《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0年第8期),因此,有必要撰文澄清这个问题。
[作者通联:俞万所,江苏仪征教研室;张悦群,江苏扬州邗江区教研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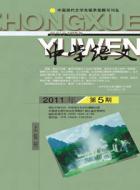
- 语文学案教学课堂基本模式探索 / 倪岗
- 考的内容要值得教 / 胡根林
- 教学即评价 / 胡根林
- 阅读教学应建基于普遍性的生活经验 / 王革虎
- 浅谈教学中对文本的适度超越 / 钟义民
- 强化文本主体意识提高文本解读能力 / 张震涛
- 由“末”逐“本”优化语文课堂提问语言 / 张卫红 魏爱平
- 抓住文章亮点,实现文本价值 / 张孟光
- 2010年度语文理论研究热点追踪(下) / 温立三
- 立足当代社会 拓展思辨空间 / 潘涌 王婷
- 自语:对语文本体的文化阐释 / 曹明海
- 种树者郭橐驼与敲钟人卡西莫多的美学共性 / 肖科
- 崇高感与悲剧感的完美结合 / 杨仕威
- 超级尴尬:高中生找不到句子的谓语和宾语 / 董旭午
- 智慧闪耀 千古至文 / 龙健
- 浅谈高三科技类文章阅读题训练的基本问题 / 朱江
- 《发现》:红色意象的文化意蕴 / 林忠港
- 语文教育史学研究的新篇章 / 李蕴哲
- 怎样理解《屈原列传》中的“曰以为” / 罗献中
- 追求功利同样渴望华彩 / 董伟永
- 课外小组研读“文化论著”方式的再思考 / 陈桂春
- 浅谈高中学生语文学习心理的调试 / 邰雨春
- 用陌生的眼光来审视世界 / 姚芳
- 虚笔不虚 美在自然 / 董辉 饶倩
- 只缘不解“赋家语” “鼎铛玉石”到如今 / 俞万所 张悦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