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5期
ID: 13660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5期
ID: 136602
虚笔不虚 美在自然
◇ 董辉 饶倩
老舍先生的语言清新纯净、优美空灵,如清水芙蓉,无铅华粉饰,却能清沁肺腑,得无穷妙境。如此佳境,得益于他善用虚笔。在《济南的冬天》一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老舍先生巧用设想与想象,化实为虚,营造美妙意境的例子。比如:
……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
偌大一个济南城,在那充满温情的双眸注视下,就这样浓缩成一个乖巧恬适的婴儿。试想,要用多少柔情才能化解那些灰瓦砖墙?如此设想,化实为虚,更透出作者心中那份浓浓的爱意。这样一个充满温情暖意的境界,怎能不让读者也沉醉其中不愿醒来呢?
再如文章的结尾:
……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济南城此时又被作者浓缩成一块蓝水晶。透过这块蓝水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天明水净的世界,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一个树影婆娑的世界。这里有纯净的气息、跳动的色彩、朦胧的美感,这是作者浓缩在心的一个令人迷醉的世界。老舍的心就犹如一块空灵的蓝水晶,滤去了一切繁芜尘杂,只留下对济南冬天的深情赞美。这样一个澄澈清明的世界,犹如书桌上珍贵无比的小摆件,让人爱不释手。
尤其妙绝的是: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
作者描绘雪后秀美的山景,由山上矮松顶上的白花写到山尖给蓝天镶上的银边,再到山坡上斑斓的雪景,由点到线到面,境界渐开,有形有色。更为奇妙的是,“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在作者欣赏且近乎痴迷的注视下这件带水纹的花衣似乎在流动。那种灵动之美,似乎被风轻拂的衣角不断挑动着读者的想象,其间含义无穷的言外之意不断冲击着读者的审美想象。在这种想象之中,山坡飘动起来了,这种恍惚的错觉,全是那“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的功劳,流动感渐次强烈,花衣轻轻拂起,柔美的弧度似乎可以拂扫面颊,给你一点希冀,一些渴望,让你在对山的肌肤的想象中实现最佳的审美酿造,并且自失其中,被自己的佳酿所迷醉。有什么能比想象更美呢?
虚笔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艺术效果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虚笔能为读者提供一个联想和想象的广阔空间,读者可以利用联想和想象去组接生活的画面,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形象、意境进行独到的补充扩展和再创造,在其自由构筑的天地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得到审美发现的满足和艺术欣赏的美感,这正是虚笔手法的魅力所在。
老舍先生说:“叙述不怕细致,而怕不生动;在细致处,要显出才华;文笔如放风筝,要飞起来,不可爬伏在地上;要有自己的想象,而且使读者的想象也活跃起来。”
冯有源有感于贾平凹的创作方法时也说:“……往日的文章单薄、干瘦、不丰腴,是因为行文时,叙述多于描绘,或者很少描绘,纯为叙述;叙述时,笔又未能放开;太拘谨,就少想象,少联想;少想象和联想,往往就是一处一个桃子,摘了就走。殊不知停下多看看,多想想,多写写,还有更多更大更红的桃子,还有更多更绿更美的桃叶,桃叶上也可能有虫子、鸟儿、蜜蜂、蝴蝶……这其中又有多少情趣和文章可做。”
因此我们在写作中也不妨试试用想象为自己的文字插上翅膀,用虚笔描绘出一个神奇的世界。那时你一定会感叹:“虚笔”真的不“虚”!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附属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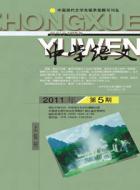
- 语文学案教学课堂基本模式探索 / 倪岗
- 考的内容要值得教 / 胡根林
- 教学即评价 / 胡根林
- 阅读教学应建基于普遍性的生活经验 / 王革虎
- 浅谈教学中对文本的适度超越 / 钟义民
- 强化文本主体意识提高文本解读能力 / 张震涛
- 由“末”逐“本”优化语文课堂提问语言 / 张卫红 魏爱平
- 抓住文章亮点,实现文本价值 / 张孟光
- 2010年度语文理论研究热点追踪(下) / 温立三
- 立足当代社会 拓展思辨空间 / 潘涌 王婷
- 自语:对语文本体的文化阐释 / 曹明海
- 种树者郭橐驼与敲钟人卡西莫多的美学共性 / 肖科
- 崇高感与悲剧感的完美结合 / 杨仕威
- 超级尴尬:高中生找不到句子的谓语和宾语 / 董旭午
- 智慧闪耀 千古至文 / 龙健
- 浅谈高三科技类文章阅读题训练的基本问题 / 朱江
- 《发现》:红色意象的文化意蕴 / 林忠港
- 语文教育史学研究的新篇章 / 李蕴哲
- 怎样理解《屈原列传》中的“曰以为” / 罗献中
- 追求功利同样渴望华彩 / 董伟永
- 课外小组研读“文化论著”方式的再思考 / 陈桂春
- 浅谈高中学生语文学习心理的调试 / 邰雨春
- 用陌生的眼光来审视世界 / 姚芳
- 虚笔不虚 美在自然 / 董辉 饶倩
- 只缘不解“赋家语” “鼎铛玉石”到如今 / 俞万所 张悦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