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5期
ID: 136549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5期
ID: 136549
种树者郭橐驼与敲钟人卡西莫多的美学共性
◇ 肖科
一、两个丑陋畸形人:郭橐驼与卡西莫多
标题中的两个人物大名鼎鼎,前者郭橐驼是一代文学宗师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刻画的个性鲜明的形象,时间是公元9世纪;卡西莫多(Quasimodo)则是著名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其《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一个著名人物,时间是公元19世纪,准确地说是1831年。
在雨果的笔下,卡西莫多是“纯粹打碎后又胡乱焊接起来的一个巨人”:
……此时从花瓣格子窗的圆洞伸出来的那个怪相,巧夺天工,举世无双。狂欢激发了民众的各种想象力,什么才算是最理想的怪诞面相,他们心目中都有个谱,但是至今从窗洞钻出来的那些五角形、六角形、不规则形状的面相,不能符合他们的心理要求,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奇妙无比的丑相,把全场观众看得眼花缭乱,一举夺魁是十拿九稳的了!科珀诺尔君亲自鼓掌喝彩,克洛潘·特鲁伊甫参加了比赛,他那张丑得无可比拟的脸,也只好甘拜下风,我们也是自愧不如。我们不想在这里向看官描述那个四面体的鼻子,那张马蹄形的嘴巴,那只被茅草似的棕色眉毛所堵塞的细小左眼,一个大瘤完全遮住了右眼,那上下两排残缺不全,宛如城堡垛子似的乱七八糟的牙齿,那沾满浆渣,上面露着一颗象牙般大门牙的嘴唇,那像开叉似的下巴,特别是面部充满应有的所有表情,如果可能,请诸位看官把这一切综合起来想一想吧!
全场一齐欢呼,大家急忙向小教堂涌去,高举着狂人教皇抬了出来。这时,大家一看,惊讶得无以复加,叹为观止:原来这副怪相竟然是他的真面目!
更恰如其分地说,他本人就是世上所有丑相的组合体。一个大脑袋,红棕色头发竖起;两个肩膀之间耸着一个偌大的驼背,与其相对应的是前面鸡胸隆凸;大腿与小腿,七扭八歪,不成个架势,两腿之间只有膝盖才能勉强并拢。从正面瞧去,就像两把只有刀把接合在一起的月牙形的大镰刀;宽大的脚板,巨大无比的手掌;并且,却有一种难以描述的体态存在这样一个身躯中:精力充沛,矫健敏捷,勇气非凡,力与美,都来自和谐,这是永恒的法则使然,但这是例外,例外得离奇!这就是“教皇”,狂人们刚刚选中的“愚人教皇”。
这纯粹是打碎后又胡乱焊接起来的一个巨人!……
这就是《巴黎圣母院》中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愚人之王”——卡西莫多的闪亮登场,似乎上帝将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他的身上!
《种树郭橐驼传》对主角的刻画是淡笔点染,则简约得多:
……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即骆驼——笔者注)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这两个形象,一中一洋,相隔近千年,却有着诸多的共同点:形貌丑陋,身体畸形残疾;被玩笑或受到人们的嘲讽;任凭他人呼牛唤马——乡人称种树高手为“橐驼(即骆驼)”,而敲钟人亦被人们呼为“响当当的驼子”、“丑八怪猩猩”、“瘸子”、“恶魔”、“卑鄙的灵魂”、“独眼巨人”……当然,当事者的反响略有不同:郭橐驼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而卡西莫多多少有些无奈、有点傻冒式的被动接受。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有趣的现象产生了:有自己审美眼光的东方人与有自己审美意识的西方人,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两个毫无二致的精彩文学形象,这就是——丑陋畸形的“中国人”郭橐驼和“法国人”卡西莫多。
而在中外美学界、文学理论界,已大致形成这样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判定:审美价值,是文学艺术的根本价值,是文学作品与其它文字作品的本质区别。在我国目前出版的美学、文学理论教材中,大多也将审美价值视为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或最高属性。这样,作为两个文学形象,似乎面临这样一个悖论:郭氏和卡氏分明是“丑”的,却如何有着审美价值?
二、丑陋如何关联着“美”?
德国美学家鲍姆嘉登(也译作鲍姆加通)1750年出版其学术专著《美学》,宣告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成立,他因此也被人们尊为“美学之父”。自从他提出Aesthetics(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感性学”,后来翻译成汉语就成了“美学”)起,美学就是一个充满争论的领域。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发出一声浩叹:“美是难的!”时至今日,关于美的探讨早已硕果累累,但当人们真正面对“美”(或“不美”,甚至“丑”)的时候,仍然逃不出先哲的设定:“美是难的!”这个“难”表现在若干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丑陋如何关联着“美”(或者说“丑”何以存在“美感”)?面对郭橐驼与卡西莫多的“不美”甚至是“丑”,读者肯定会有一个共同的疑惑:他们怎么会关涉到“美”?“美”究竟是什么?
为了廓清这一迷雾,我们来稍稍回顾一下人类的审美历程。
可以说,美感和伦理道德以及羞愧、荣誉感等一样,是自然选择长期作用的结果;美感的形成也是人类历史实践的结果。可以设想,在混沌初开的远古,原始人根本没有什么美感和美的观念,有的只是对某些表现特征的偏好,比如对人的身体本身,有的偏好身材匀称、相貌端庄的人,而厌恶身材畸形、相貌不端庄的人;有人则刚好相反。经过漫长的选择、淘汰和积累、演化,人们可能发现:相貌端庄、牙齿整洁、肤色滋润、身材匀称、体态轻盈的人,一般说来都比较健康,更适合生存或者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驼背瞎眼、龇牙咧嘴、缺臂少腿等身材畸形、相貌不端的人,往往体弱多病,生存能力差或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身材匀称、相貌端庄被人们认为是美的。这一点在中外都能找到佐证。
在西方,人类表现人自身形象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公元前3万年至1万年的时期。到公元前5世纪(这是古希腊雕塑艺术的辉煌时期),古希腊人对人体美有特殊的敏感,最基础一环的审美标准就是健壮。这一审美理想的根须深扎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频繁的战争需要强健的男子去厮杀,斯巴达人甚至对出生残疾和羸弱的婴儿毫不留情地抛入山谷喂狼。城邦制国家要求公民必须具备完善的心灵和强壮的体魄,而艺术则必须塑造庄重的理想化的公民形象——奥林匹克运动场上的竞技者便成为人体雕塑的范本。西方美术史和原始文化的研究传达出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类最早表现人自身的形象,便是肥硕而健壮的,与肢体残缺、畸形或变态相去甚远。
在中国,很久很久以前,黄帝(轩辕氏)就对中医祖师歧伯说过:“我听说上古时代有一种真人,能够提挚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自主,守护心灵,全身合一,所以能够与天地齐寿,无穷无尽,这是与道同生。中古时代,有一种至人,德行纯朴,道行圆满,能够顺和阴阳,顺从四季,摆脱世俗,保全精神,游行天地之间,洞察八方之外,这种人寿命很长,身体强健,也算是真人。其次有一种圣人,与天地和睦相处,顺从人情世故,世俗的欲望有一点,但是不贪,也不去刻意超尘拔俗;虽有一副俗人模样,心里却不落俗套,做事不钻牛角尖,内心也不存非分之想,只求心安理得,只求自得其乐,身体不得病,精神不耗散,也可以活个百把岁。”(《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上古的“真人”也好,中古的“至人、圣人”也罢,请注意他们“身体强健”、“身体不得病”等特征!
换言之,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无论中外,人类在自身形象的表现上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丑陋、残缺、畸形与美无关。此时,很容易让人想起闻名世界的一座雕像——米洛斯的断臂维纳斯。同为卢浮宫镇馆之宝的命运三女神和萨莫色雷斯的尼凯神像,不仅手臂残缺,连头颅也不复存在了,却令美学家清冈卓行等赞叹不已:“米洛斯的维纳斯虽然失去了两条由大理石雕刻成的美丽臂膊,却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抽象的艺术效果,向人们暗示着可能存在的无数双秀美的玉臂”、“为了如此秀丽迷人,必须失去双臂”……于是“残缺美”之说便常常被一知半解的人们挂在嘴边,这实在是一个误会,至少是不痛不痒的见解!当然,也有人从雨果的创作手法“对照原则”(以丑衬美)这个角度去解释,说卡西莫多的外貌丑陋,但是他的内心却是高尚的(比如他的善良、坚定、勇敢)。他外表的“丑”彰显了内在的“美”,因而也就丑变成了美(这种解释显然也适用于郭橐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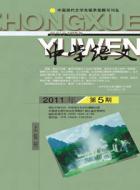
- 语文学案教学课堂基本模式探索 / 倪岗
- 考的内容要值得教 / 胡根林
- 教学即评价 / 胡根林
- 阅读教学应建基于普遍性的生活经验 / 王革虎
- 浅谈教学中对文本的适度超越 / 钟义民
- 强化文本主体意识提高文本解读能力 / 张震涛
- 由“末”逐“本”优化语文课堂提问语言 / 张卫红 魏爱平
- 抓住文章亮点,实现文本价值 / 张孟光
- 2010年度语文理论研究热点追踪(下) / 温立三
- 立足当代社会 拓展思辨空间 / 潘涌 王婷
- 自语:对语文本体的文化阐释 / 曹明海
- 种树者郭橐驼与敲钟人卡西莫多的美学共性 / 肖科
- 崇高感与悲剧感的完美结合 / 杨仕威
- 超级尴尬:高中生找不到句子的谓语和宾语 / 董旭午
- 智慧闪耀 千古至文 / 龙健
- 浅谈高三科技类文章阅读题训练的基本问题 / 朱江
- 《发现》:红色意象的文化意蕴 / 林忠港
- 语文教育史学研究的新篇章 / 李蕴哲
- 怎样理解《屈原列传》中的“曰以为” / 罗献中
- 追求功利同样渴望华彩 / 董伟永
- 课外小组研读“文化论著”方式的再思考 / 陈桂春
- 浅谈高中学生语文学习心理的调试 / 邰雨春
- 用陌生的眼光来审视世界 / 姚芳
- 虚笔不虚 美在自然 / 董辉 饶倩
- 只缘不解“赋家语” “鼎铛玉石”到如今 / 俞万所 张悦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