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7期
ID: 136286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7期
ID: 136286
从听到读:汉语阅读的发展障碍
◇ 戴方文
“听”和“读”同为语言的输入,但“听”明显先于“读”而发展,两者在发展水平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年级的学生普遍会“听”,但不一定会“读”,或者说“读”的理解不如“听”的理解透彻。同样,不同年级的学生普遍会“说”,但不一定会“写”,或者说“写”的没有“说”的生动和深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口耳相传的口头语言在向以文字符号为基础的书面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在许多方面存在障碍。正是这些障碍,造成了儿童阅读与写作的困难。我们把这种困难称作书面语言阅读和写作的发展性障碍。
这里所说的发展性阅读障碍,与心理学的概念有所不同。心理学的发展性阅读障碍一般是:具有正常的智商和受教育机会以及学习动机,没有明显的神经和器质损伤,没有情感障碍,没有注意障碍,在标准阅读测验上的成绩低于正常读者两个年级的现象(彭聃龄,《汉语儿童语言发展与促进》)。本文所说的发展性阅读障碍主要指个体书面阅读水平明显低于口语听讲水平的情况,在预设条件上与前者一致。在阅读教学中,只有帮助学生有效克服这种障碍,才能在已有的言语发展基础上,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
一、书面语言系统对阅读构成的发展障碍
阅读是读者借助文字符号与作者进行的对话。这种对话与口语会话比较,有所不同。文字符号是对话的媒介,诉诸人的视觉而不是听觉,不识字的人和没有掌握书面语言系统的人无法完成这种对话。
那么,文字和书面语言给学生的阅读发展造成了哪些障碍?
(一)汉字对阅读发展的障碍
与口头语言诉诸人的听觉,借助语音通达语义不同,书面语言的文字首先诉诸人的视觉。初始阅读必须将视觉文字转换成听觉信号,借助言语发展的基础方可通达语义,所以幼儿通常以听故事代替阅读。就汉语而言,只有当阅读发展到一定水平,文字识别达到音形义一体化以后,“以形达义”才变为可能。在阅读发展的某一阶段,借助语音和字形通达语义的可能是并存的。因此,在儿童阅读发展进程中,识字是从口头语言习得到书面语言学习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障碍。
汉字主要是一种表意文字,以形赋义是其主要特点,所以汉字字形历来就是学习的重点。形与义的互动即“以义记形”和“以形识义”,常常成为主要的识字方法。研究表明,在字义通达方面,借助字形通达语义稍晚于借助字音通达语义。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字形是作为语素这一语言单位影响汉语阅读的(McBride-Chang,2003)。因此,立足于发展学生阅读能力的汉字教学,应该把汉字放在词语语境中,辨析作为语素的汉字的意义,以此增进学生的语素意识(语素意识是影响学生阅读水平的一个独立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字不离词”有其科学依据。
汉字学习的难点主要在语音而不在字形,因为表意文字相对缺乏表音线索,而语言首先是以声音作为物质载体的。若以发展学生书面语言的接受(阅读)能力作为识字教学的重要目标,则应该注重语音意识的培养。语音意识是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它指的是个体对口语中声音结构的理解、判断与运用,包括对音节、押韵、韵脚、音位的感知和理解。多项研究证明,与其他因素的预测相比,语音意识对儿童后续阅读的发展水平具有更加稳定有力的预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的语音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的阅读发展水平(lonigan,2000)。传统识字教学以韵文(如《三字经》)和诗歌为载体,在大量的语音识记中,发展了儿童的语音意识,为后来的阅读理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方法值得借鉴。
我们知道,字义或词义的理解是一个长期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幼儿对字词含义的理解,在成年后会经历许多变化。因此,识字教学期望音形义同步发展是不现实的,旨在发展学生阅读能力的识字教学应该强化语音积累,突出培养学生的语音意识。长期的诵读和朗诵训练,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语音意识,为语感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分析有余,朗读不足,几成通病。事实上,很多不懂的地方只要再读一读就会明了。
识字教学只有有效克服字形、字音两重障碍,才能发展起儿童最初的认读能力和初步的理解能力。
(二)阅读中词义理解的障碍
人们在阅读中如何理解一个词的具体含义,这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心理学问题。特雷斯曼认为,学会了语言和阅读的人,都有一个心理词典。这个词典由许多词条组成,每个词条都包含了与这个词对应的词的语音、写法特征和词义特征,其中词义特征占据中心位置。对于单个词的认知,科勒斯(Kolers)认为,读者是直接从词的书写特征通达心理词典中词的意义的,特别是对于非拼音文字(如汉语)来说是这样的。高夫认为,心理词典中的词义被提取,有两个线索:语音线索和词形线索。多数表音文字借助语音线索通达词义,汉语也有类似的通达途径,这一过程必须以口语理解的词语作基础。汉语在后期阅读中主要借助词形线索通达词义,因此,汉语心理词典必须增加正字法的表征,读者识别正字法表征并通过言语中介(主要是语音特征),才能从词的书写形式通达它的意义。
词在句子中被加工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高夫认为,词在句子中是从左到右地、系列性地被认知的,认知模式与单个词相同。这是阅读中从下而上的认知模式。从上而下的模式认为,句子的语义和句法,协同词的语音和词形,共同激活了心理词典中的词条,赋予词在句子中的具体意义。
无论是单个词还是句子中的词,在阅读中意义的通达都离不开心理词典的建立。心理词典中词条的建立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词的语音表征,词形表征和正字法特征,词义网络的建立。只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全部具备,词义才可能在阅读中被迅速提取。三者之中,词义网络最为关键。研究表明,心理词典中的词按照种属关系、特征关联构成一个非等级的网络(科林斯、洛夫特斯,1975),如“鸟”、“动物”、“下蛋”、“吃奶”、“卵生”、“羽毛”、“金丝雀”、“家禽”、“小鸡”等词语构成了一个有种有属、特征关联的语义网。词的语义网络结构越完整,阅读理解词义通达速度越快,理解越准确。词的语义网络的建立有赖于学生的词语习得,但儿童发展后期的语言教学和书面阅读中的词语学习,对词的语义网络的构建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心理词典的建立和词的语义网络的构建,是学生书面阅读发展在词语层面必须跨越的一道障碍,词语学习和书面阅读中的词汇积累可以有效克服这一障碍。
(三)阅读中句意理解的障碍
与口语中的句子相比较,书面语言中的句子更规范、更完整、更严密、更准确、更深刻。这是口语中的句子在进入书面语言系统后被加工的结果。这种句子,由于失去面对面的具体言语情境,包括具体的交流目的、交流对象、交流场合和辅助的交流手段,理解起来相对困难。那么,高水平的读者是怎样克服这些障碍,在书面阅读中准确理解句子的含意的呢?
在阅读中理解一个句子,意味着读者从书面文字中建构这个句子的意义。下面以一个句子为例,说明句子在阅读中意义建构的过程。如:
踏上了沙漠的我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
——牛汉《绵绵土》(有改动)
读者看到这个句子,首先接触的是这个句子中词的时间序列:踏上了、沙漠、的、我、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在视觉末端,读者开始认识这个句子的表层结构:词的时间序列、句子中的词、词的组合关系(踏上了沙漠的我、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等。
在把握了句子的表层结构之后,读者明确了该句子表达的全部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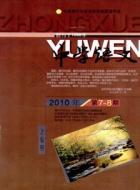
- 论生命教育的场域 / 杨定胜 杨定云
- 文化论著的探究式学习及其评价 / 潘进听
- 教学目标设计:想说爱你不容易 / 张正耀
- 板书创新与有效性探究 / 刘晓宁
- 不怕考试 超越考试 / 蓝 枫
- 视域融合:文学教育研究的基本取径 / 胡根林
- 事实胜于雄辩 / 唐建新
- 文学抑或文章——对语文高考“考什么”的思考 / 乐中保
- 语文教育概念术语辨析 / 蔡 明
- 中学语文课文中的模糊语言及教学 / 黄大族
- 语文教育活动的文化功能 / 曹明海
- 人在旅途,风景这边独好 / 郑翠娥
- 语文主体性教学视角下的文化主体性培养 / 田泽生
- 语文教学中的正话与闲话 / 汲安庆
- 在细读中体味语言的美 / 倪效思
- 网络文学影响下的高中作文批改与讲评 / 杨道州
- 背景资料:让阅读教学厚实起来 / 仇定荣
- 从听到读:汉语阅读的发展障碍 / 戴方文
- 论新课程背景下作文教学若干课型 / 贺晓刚
- 文本解读的“泛”与“实” / 程先国
- 向思维更深处漫溯 / 毕泗建
- 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嬗变之管窥 / 蒋玲慧
- 正确理解和把握高中语文新课标中的“阅读目标” / 魏政刚
- 立足语言本体,提升探究能力 / 蔡燕明
- 作文好题的标准 / 陈国仁
- 浅谈中学作文境界提升的途径 / 童县城
- 让文化底蕴提升作文品味 / 李小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