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7期
ID: 13628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7期
ID: 136282
语文教学中的正话与闲话
◇ 汲安庆
语文教学从根本上说是引领学生感悟、把握、领会经典的“秘妙”的过程,而这“秘妙”其实就是“美”。正话与闲话正是为了平衡教学中的功能性信息和非功能性信息,实现感悟美、体悟美、创造美的教学目的所做出的思考。
一、两种生存形态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这是古代说书人的口头禅,更是他所说之书(章回小说或者评书)中的高频率语句。严格地说,“传”开始指注释或解释经义的文字,后来也指叙述历史故事的作品,多用于小说的名称,正传当然就应指小说的“正文”了。闲话与之对立,指可以脱离正文,或者与正文联系不太紧密的“话”。但是,“话”依“传”而实,“传”因“话”而活,所以闲话也有“闲文”的意思,“正传”也有了“正话”的内涵。
闲话与正话并立而存,但因其闲,向来都处于“奴”或“妾”的地位。说话艺术以说为主,唱便成了“从”。故事应关注事件的系列,但是金圣叹以八股文的思维来评论《水浒传》,把议论引入叙事,注重起承转合,叙事反而沦落为“仆”。更多的受众不理这一套,他们高度关注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命运,对故事中的景物描写,对于心理抒情部分反而觉得碍事,“一会儿柳似花朵,一会儿地动山摇”的审美快感,他们觉得非常遥远。这种“正闲思维”对其他文学样式也是有深刻影响的,比如元杂剧中的楔子,虽然对剧情起交代或连接作用,是整个剧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依然是处于“配角”地位。可见,正话和闲话是依其功能价值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更的:只要沦为闲话,便难逃被轻视的命运。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如果所写的话语与主题无涉,连闲话的名分也难拥有,只配被称作“废话”。在当代语文教学中,如果所讲的话与考试的指挥棒没有直接联系,会立刻被视为教学语言不精炼,教学目的不突出;如果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情感、想象、体验等非智力因素,会立刻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花架子”,同样会遭到无情的嘲弄和封杀。所说的话语自然隶属“闲话”、“废话”之列了。
但是闲话并不因为自己“闲”或者“废”就自生自灭,卑微地退出审美的世界,相反,它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融入了创作主体的精神血脉,在文本中顽强而普遍地生存下来,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例如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乐府民歌《木兰诗》写了一位叫花木兰的女子替父从军,载誉归来的故事。照理,诗人应该对花木兰的军营生活、疆场征战这些“正话”浓墨重彩地渲染,对“战前准备”、“辞官回乡”、“亲人相见”这些闲话则应一笔带过。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正话在全诗中仅有区区6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可是,闲话却被诗人用了数倍的笔墨!
文本中是这样,那么课堂教学中的情形又如何呢?
不妨举个有案可查的例子来论证。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以一位叫小弗郎士的孩子的口吻,叙述了普法战争期间,法国阿尔萨斯地区遭受普军侵占以后,师生上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情形。细分一下,我们发现这节课容纳了下述内容:1.抽查学生背书;2.上语法课;3.习字;4.教历史;5.教初级班拼读音节。按说,讲授和这些内容相关的知识应是该课的正话,而且应该是最让作者经久难忘的,但是结果与之截然相反!作者极力渲染,且刻骨铭心的是老师韩麦尔先生对忘却时间的人性分析,对法语与敌国之间关系的论述,甚至他在学生写字时,凝视小教室每一样东西的神情,还有哽咽着和学生道别的情形。而这些却是与所传授的知识无关或者“少关”的,属于闲话的范畴。
对此,美国作家帕克. J .帕尔默深有感触地说:“好的教学有好多形式,好的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会淡忘,但对好的老师本身却会长久铭记。①”而令他终身难忘的是一位大学老师,“他似乎打破了优秀教学的每一条‘规则’,他讲课是那样富有激情,讲很多内容,以至于不给学生留一点提问和评论的时间。他博学多才,很少听学生的想法,不是他看不起学生,而是因为他那样热衷于以他所知的唯一一种方式教学生——分享他的知识和热情。”作为正话的知识在多年后会淡忘,作为闲话的“热情”(“慷慨地把他的精神生活向我敞开,充分地表达思想”)却难以磨灭。这是一个饶有趣味,却又令人深思的现象。
二、教学中的此消彼长
正话和闲话在教育史上的此消彼长,完全可以追溯到更深广的历史背景中。
从教育的角度说,教育起源于原始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及实践的过程,而生存和发展反过来也成了推动人类教育的两种基本力量。“在原始社会的教育中,凡是与日常劳动和生产相关的教育内容,如渔猎、采集、耕作、制作生产工具等都属于功能性信息,这类信息主要为人类生存提供服务;凡是与宗教、艺术等相关的教育内容,可以划归为非功能性信息,主要为发展人的精神和潜力服务。”②
可是,这种合二而一的教育本质和教育职能在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后,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一种是过分关注功能性的信息,为巩固国家的稳定和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人的发展只能从属于国家和集体的发展。如孔子倡言“启发式”,孟子主张“存养式”,荀子强调“积渐式”,都是与各自推行的教育内容“礼”、“乐”有关。后期儒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道德”,认为教育的功能就是将道德化为政治,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法家推行的教育内容主要是法令、法律,想凭借“法”施行广泛的社会教育,虽然手段不一样,但其教育的实质也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汉代、隋唐的重振儒学,宋明的功利教育思潮,清朝的实学教育可谓相同教育目的的不同呈现而已。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科学主义的盛行,学校教育流水线、机械化的特征更为显著。将知识分成若干点分布在课文中,教师围绕知识点,逐个突破,然后连线成面、成体,形成所谓的知识体系,这成了一种强劲的教育势头。感性流逝,不怕;高科技后没有高情感,也不怕。这种历史的文化惯性渗透进了教学的意识或无意识中,顺者,则名正言顺,言为“正话”;逆者,则名不正,言不顺,言为“闲话”或“废话”、“傻话”、“错话”,甚至“疯话”。
另一种是强烈关注非功能信息,努力把教育从宗教、政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突出关注人的充分发展。如老子以“道”为教育的根本,强调无为。无为不是消极地不为,而是不凭主观意志强为,是依据“道”自身的发展规律,创造条件,促使事物自化。虽然有治国之意,但十分关注顺乎人、事的天性。庄子继承老子的教育思想,并将“道”从“为治”引向“养生”,强调人的养生应该像庖丁那样顺乎自然,依乎天道,去除各种“名”与“知”的争执,达到自由的境界,也就是“天乐”之境。他还主张齐生死、崇自然、贵虚无、尚不言,以求更明智、更通达、更快乐、更幸福、更平静、更理想地享受人生,进而将人生提高到了精神审美的最高层次。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价值观中的文学地位渐趋超越经学,文学教育开始确立独特地位,这给人性从经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提供了契机。“养气”理论从道德教育中心转化到审美教育中心,所以“养气练性”成为审美教育和人文修养的中心环节。尤为可喜的是,这种社会化的审美教育还泛化到书法、绘画、音乐等诸多方面,人的思想、潜能、个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宋明心学的教育目标是:明理、立心、做人。其中立心说突出了教育的主体意识和个人的自我价值及历史职责,具有了近代教育的色彩。在当代的教学理论中,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力陈认知心理学的不足在于把人当作“冷血动物”,即没有感情的人,主张心理学要探讨完整的人,而不是把人割裂为行为、认知等从属方面。“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但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的建构的方式而获得。”③按这些理念说话,就是“闲话”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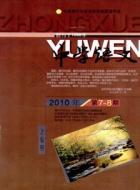
- 论生命教育的场域 / 杨定胜 杨定云
- 文化论著的探究式学习及其评价 / 潘进听
- 教学目标设计:想说爱你不容易 / 张正耀
- 板书创新与有效性探究 / 刘晓宁
- 不怕考试 超越考试 / 蓝 枫
- 视域融合:文学教育研究的基本取径 / 胡根林
- 事实胜于雄辩 / 唐建新
- 文学抑或文章——对语文高考“考什么”的思考 / 乐中保
- 语文教育概念术语辨析 / 蔡 明
- 中学语文课文中的模糊语言及教学 / 黄大族
- 语文教育活动的文化功能 / 曹明海
- 人在旅途,风景这边独好 / 郑翠娥
- 语文主体性教学视角下的文化主体性培养 / 田泽生
- 语文教学中的正话与闲话 / 汲安庆
- 在细读中体味语言的美 / 倪效思
- 网络文学影响下的高中作文批改与讲评 / 杨道州
- 背景资料:让阅读教学厚实起来 / 仇定荣
- 从听到读:汉语阅读的发展障碍 / 戴方文
- 论新课程背景下作文教学若干课型 / 贺晓刚
- 文本解读的“泛”与“实” / 程先国
- 向思维更深处漫溯 / 毕泗建
- 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嬗变之管窥 / 蒋玲慧
- 正确理解和把握高中语文新课标中的“阅读目标” / 魏政刚
- 立足语言本体,提升探究能力 / 蔡燕明
- 作文好题的标准 / 陈国仁
- 浅谈中学作文境界提升的途径 / 童县城
- 让文化底蕴提升作文品味 / 李小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