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7期
ID: 136265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7期
ID: 136265
教学目标设计:想说爱你不容易
◇ 张正耀
一
现代教学理论告诉我们,语文课堂教学目标是教学过程中师生预期达到的某一或某几种学习结果和标准。它不是指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宽泛的语文教育目标,也不是着眼于语文课程体系得以实施的长远目标,更不是某本教材某一个具体模块的学习目标,而是在一节语文课上教师到底要引导和帮助学生学习什么,达到什么效果。所以,准确地说,教学目标应是指课时目标,“它是课程目标的进一步细化,在方向上对教学活动设计起指导作用,为教学评价提供标准和依据。”①它是教学过程的基点和归宿,它对整个课堂教学中师生的教与学的活动过程具有导向作用,并引领和控制着教和学的过程有序展开。
美国教育家布鲁姆认为,教学目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认知、技能、情意,这也是我国的新课程标准中所提出的“三维目标”的主要理论依据。这就要求我们的每一个语文教师在组织和实施具体的教学活动前,必须明确在一节课中要引导学生运用怎样的方法、通过怎样的途径学习哪些知识和技能,在情意方面有哪些变化或发展。这三个方面能否明确,就看教师能否对文本进行全面、准确而有个性的解读,就看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是否有全面的了解,就看教师的教学安排是否合理、教学方式方法选择运用是否得当。很明显,教师如果没有认真而充分地备课,就不可能设计出有实施价值的教学目标。
二
目前,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设计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一是无效。
不少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缺乏教学自信,或不知或不想或不能有自己的教学思考,而是被“百度”、“谷歌”的引擎牵着鼻子,照搬照抄各种教学参考资料上对教学目标的种种说法,根本不去考虑所在学校所教班级学生的特点和差异,不去分析研究教学目标的实效;有的教师文本解读视野不宽、水平不高、能力有限,不能针对文本(所学习内容)的特点设计有效的教学目标。
如某位教师所设计的“鉴赏古代诗歌的语言”(高三复习课)的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培养学生识别关键词语和鉴赏词语的能力;培养学生养成合作学习、相互讨论的习惯和能力;
2.过程与方法:
以练习带动学习;合作中相互学习、相互讨论。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合作中相互帮助的素养;在学习中感悟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魅力。
这位教师所设计的教学目标,除了在“知识与能力”中“识别关键词语”和“鉴赏语言”的表述与所教学的内容有直接的关联外,所设计的其它几个“目标”没有充分体现课堂教学内容的要求,看不出对学生学习水平变化的期待,没有考虑教学所要实现的具体结果,更不能通过这样的设计对课堂教学情况进行评价。这样的设计除了可以应付学校相关部门的教学常规检查之外,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二是泛化。
我们评价一节课是否有效,其主要的标准应该是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的具体进步,而不是教师有没有完成自己所设定的“任务”。也就是说,教学目标在根本上应是教师所设想的学生的“学习目标”而不是教师的“教学目的”。工作调研中,我们常常发现教师在教学目标上写“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指导学生树立环保意识”等大而化之、避实捣虚的对实际课堂教学没有具体指导意义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可以用于任何年级、任何班级、任何学生、任何课型、任何内容的教学。
在上例中,教师三次从自己的教学角度用了目的性极强的“培养”一词,而试图“培养”的却是“合作学习”、“相互学习”、“相互讨论”等一些基本的学习能力,与课堂教学的具体内容和程序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有“感悟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魅力”的目标,也是在一节课中无法实施和达成的。这样的设计大而无当、笼统模糊,找不到教学的具体切入口,致使课堂教学三维目标不能得到具体细化。
三是窄化。
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我们,教学目标的确定至少应从三个层次进行表述:认知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但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偏重学生基础知识学习目标的制定,偏重对语文知识结论的训练应用的制定,忽视了对语文知识形成过程和语文学科自身的方法论的教育,忽视了人文精神、科学态度及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忽视了语文学科与自然、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二是偏重学生思想、道德、情感、品德、意志、精神等所谓的“人文性”内容的制定,过多地引导学生关注内容理解、人文感悟,忽视语言的理解与运用,忽视基本的语文知识的形成和训练,致使语文的工具性受到了不应有的弱化。
如一位教师为胡适的《我的母亲》设计了这样的教学目标:
1.概括文章中的具体事情,分析母亲优秀的性格品质,感受母亲的人物形象;
2.理解母亲对“我”的做人训练,感受母亲那无比深挚的爱子之情;
3.联系自身的生活经验,再次体会母爱的无私与伟大。
抛开这位教师在语言运用上不够准确、妥贴不谈,教师的教学思想有极大的偏差:教师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引导学生关注课文写了什么,说了什么,这诚然是可以的;但作为语文课,在任何时候对语言的学习都应该成为我们的核心任务,课堂教学的重点应是引导学生品味课文是怎么写,怎么说的,为什么这样写,不这样写还可怎样写等等。像这样的设计,忽略了对文本富有个性化的语言的学习,忽视了揣摩作者是怎样用自己的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传达思想感情的,忽视了从读中学写,体现不出语文姓“语”的这一本质属性。
四是牵强。
有的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不能从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学生的实际阅读感受出发,而是牵强附会,用社会认识、政治观点、阶级理论等进行机械联系甚至胡乱联系来设计“情感目标”,以达到所谓的“人文教育”的目的。如初中语文教学中有教师为《斑羚飞渡》所设计的情感目标是“引导学生树立保护动物、爱护大自然的思想”,为《向沙漠进军》设计的情感目标是“培养学生‘人定胜天’的精神”,为《生命的意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设计的情感目标是“培养学生从小树立伟大的人生理想,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其实,《斑羚飞渡》作为一篇寓言式的文学作品,所宣示的是生命的伟大与美丽;科普小品《向沙漠进军》所要传达的除了与沙漠有关的科学知识外,还提醒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一味违背自然规律去宣扬“人定胜天”的思想;至于《生命的意义》,则讲述了一个人在人生低谷时怎样才能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故事。语文课为什么经常上成政治课(思想品德课)、历史课、班会课、科学课?其原因就在于教师在目标设计上的“贴标签”、“画脸谱”、“拉郎配”。
这种牵强,其直接后果就是使教学活动远远偏离文本的方向,偏离语文教学的具体任务,偏离培养和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课程目标。如一位教师教学毕淑敏的《我的五样》时所设计的主要教学活动:学生在快速默读课文一遍后,教师要求学生每人拿出一张纸,在纸上写下“我的五样”,然后一样一样地划掉,最后每人只剩下“一样”。学生都划好后,教师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交流。交流的主要内容有:
1.最后,你选择了哪一样?为什么?
2.你开始选择的是哪五样?
3.你为什么划去了其他四样?请具体说出你的理由。
《我的五样》是作家毕淑敏在经历了艰难人生选择之后的心灵演绎。为了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展现得更真切些,她用文学的笔,艺术化地设计了一节“体验课”,用“选择”的方法,逐一排除生命中的其他元素,最终选出自己的“最爱”。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引领学生整体把握作家所表达的思想与感情,揣摩和分析细致的心理刻画,研习作家运用多种文学笔法来展露心理活动的艺术特色。这样的课,文本的阅读价值在哪里?学生的阅读体验又在何处?一节本来语文味十足的美文欣赏课,竟被设计成了毫无语文价值的“活动体验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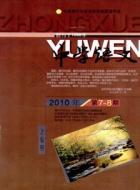
- 论生命教育的场域 / 杨定胜 杨定云
- 文化论著的探究式学习及其评价 / 潘进听
- 教学目标设计:想说爱你不容易 / 张正耀
- 板书创新与有效性探究 / 刘晓宁
- 不怕考试 超越考试 / 蓝 枫
- 视域融合:文学教育研究的基本取径 / 胡根林
- 事实胜于雄辩 / 唐建新
- 文学抑或文章——对语文高考“考什么”的思考 / 乐中保
- 语文教育概念术语辨析 / 蔡 明
- 中学语文课文中的模糊语言及教学 / 黄大族
- 语文教育活动的文化功能 / 曹明海
- 人在旅途,风景这边独好 / 郑翠娥
- 语文主体性教学视角下的文化主体性培养 / 田泽生
- 语文教学中的正话与闲话 / 汲安庆
- 在细读中体味语言的美 / 倪效思
- 网络文学影响下的高中作文批改与讲评 / 杨道州
- 背景资料:让阅读教学厚实起来 / 仇定荣
- 从听到读:汉语阅读的发展障碍 / 戴方文
- 论新课程背景下作文教学若干课型 / 贺晓刚
- 文本解读的“泛”与“实” / 程先国
- 向思维更深处漫溯 / 毕泗建
- 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嬗变之管窥 / 蒋玲慧
- 正确理解和把握高中语文新课标中的“阅读目标” / 魏政刚
- 立足语言本体,提升探究能力 / 蔡燕明
- 作文好题的标准 / 陈国仁
- 浅谈中学作文境界提升的途径 / 童县城
- 让文化底蕴提升作文品味 / 李小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