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7期
ID: 136275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7期
ID: 136275
语文教育概念术语辨析
◇ 蔡 明
编者按:
语文教育中概念术语的模糊和歧见,引起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诸多纷争,导致语文教育实践操作的摇摆不定。辨析和建立语文教育的概念术语,明确和累积语文教育的专业知识,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奠基性工作,必将有助于语文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推进。我们设置“语文教育概念术语辨析”栏目,希望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积极投入,认真进行理性思考,正确、清楚地陈述语文教育及其与内外诸事物之间的关系;对语文教育中使用的重要概念、术语达成一致理解,保障语文教育的顺利实施。
国文·国语·语文
“国文”、“国语”、“语文”是中国现代教育发展中,语文课程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名称。
“国文”是现代中国语文课程的第一个正式名称。19-20世纪之交,在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的猛烈撞击下,语文教育从综合教育中分离,裂变为词章、字课、习字、作文、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等多门课程。各门课程虽仍然是学习文言文,却专注于语文教育的某一方面,显现出分列的、专项型的语文课程雏形。1902年,蔡元培等人创办爱国学社,多门语文课程聚变为一,其名称最初统称为“国文”。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1905年,清政府学部审定国文教科书;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组织编纂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1906年前后,梁启超创办长沙女子学堂开设“国文”课;在发展过程中,“国文”名称得到了普遍认可。 1912年临时政府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小学一律开设“国文”课,“国文”名称正式确立。 “国文”做什么用? 1916年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说:“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其智德。”①
“国语”是中国语文课程中正式进入白话文后的名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白话文运动持续发展,汇入“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语运动潮流之中,推动着语文课程的前进。1917年2月,“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成立,蔡元培、张一麟为正副会长,提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的建议。②1918 年5月,教育部训令北京、武昌、沈阳、南京、广东、成都等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国语讲习科。1919年4月,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主张“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③”。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中,对于国文教科书的意见与上述相同;另有推行国语的具体办法,如师范学校增加国语科、设立国语传习所培训小学校教员等④。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20年,北洋政府通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教育部又令修正相关教育法规,将其中的“国文”改为“国语”,其要旨不变。在中国教育史上,现代白话文进入语文课程,取得了合法地位,既丰富了语文课程的基本内容,又推动了“国语”教育的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这次改革意义重大。黎锦熙在《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一文中引用胡适的话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⑤
“语文”是中国语文课程中正式进入口头语言后的名称。在语文课程发展过程中,口语和口语教学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20世纪初,庾冰《言文教授论》和潘树声《论教授国文当以语言为标准》等论文即已提倡口语教学⑥,强调国文教育中说话和听话训练的重要性。1924年,黎锦熙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新著国语教学法》,提出通过教学达到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写等五项具体目标。1925年、1926年,吴研因与舒新城、周明三与冯顺伯在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中学国语教学法》,进一步推动了口语教学的研究和施行。口语和口语教学的地位与价值逐渐被认识。1941年,教育部颁发经过修订的《小学国语科课程标准》,不仅强调了口语及其教学的功能,而且有了对口语文化功用的关注、提出了口语教学的要求。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受语文教育家叶圣陶等人的建议,决定取消“国语”和“国文”这两个名称,统称“语文”。 叶圣陶先生曾作过说明:“‘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⑦
名实相符,在“国文”→“国语”→“语文”的名称变化过程中,现代语文课程同时发生了实际变化。其显性变化主要是扩大了语文课程的对象领域:“国文”是教学文言文的语文课程,“国语”则扩大为教学文言文与教学白话文的语文课程;“国文”、“国语”是教学书面语言的语文课程,“语文”则扩大为教学书面语言与教学口头语言的语文课程。其隐性变化主要是改革了语文教育观念和思维方式——努力地改变着传统语文教育脱离学生实际、脱离社会实际的倾向,不断地纠正传统语文教育忽视科学知识教育、忽视民主精神教育的偏向。
————————
注释:
①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10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②政学会主办:《中华新报》,1917年3月9日,13日。
③④朱元善:《教育杂志》,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10卷8期、11卷11期。
⑤张鸿苓:《黎锦熙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⑥朱元善:《教育杂志》,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4卷3期、8期。
⑦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30页。
陈朱“正副(主次)目的”的划分
语文课程具有多方面的功用,它能在实施过程中训练方法、传授知识、开发能力、启迪心智、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多样的方法、广博的知识、综合的能力、复杂的心智、丰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被人们看作是语文课程的多元性目的。
可是,“语文课程目的具有多元性”这个命题却被滥用。我们常常看到,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具有不同经验和不同知识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语文课程提出不同的要求,让语文课程完成不同的任务,达成不同的目的。于是,多元性目的必然会被片面强调,语文课程的目的方向就会迷失、丢失、缺失,关于语文课程目的的辩论不可避免地发生。
20世纪前期,关于语文课程目的辩论的问题是“实用与教育”。
1909年,早期著名语文教育家、教科书编辑沈颐在《论小学校之教授国文》中提出:“宜以实用为归而不必蹈词章之习”,“授以布帛粟菽之文字而不必语以清庙明堂,则真国民教育之旨也。”①即强调语文课程的“实用”,否定“语以清庙明堂”的“教育”。
然而,语文课程与思想意识融为一体。国家要求语文课程实现教化功能;有识之士也重视语文课程强大的“教育”作用,把语文课程目的同民族精神、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1916年,蔡元培履任北大校长后致信汪兆铭说:“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他还劝汪兆铭到北大来担任国文类教学,“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1920年,当国语教育兴起时,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中强调语文课程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教育”作用:“为什么要有国语?一是对于国外的防御,一是求国内的统一。”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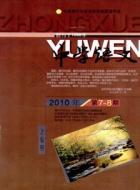
- 论生命教育的场域 / 杨定胜 杨定云
- 文化论著的探究式学习及其评价 / 潘进听
- 教学目标设计:想说爱你不容易 / 张正耀
- 板书创新与有效性探究 / 刘晓宁
- 不怕考试 超越考试 / 蓝 枫
- 视域融合:文学教育研究的基本取径 / 胡根林
- 事实胜于雄辩 / 唐建新
- 文学抑或文章——对语文高考“考什么”的思考 / 乐中保
- 语文教育概念术语辨析 / 蔡 明
- 中学语文课文中的模糊语言及教学 / 黄大族
- 语文教育活动的文化功能 / 曹明海
- 人在旅途,风景这边独好 / 郑翠娥
- 语文主体性教学视角下的文化主体性培养 / 田泽生
- 语文教学中的正话与闲话 / 汲安庆
- 在细读中体味语言的美 / 倪效思
- 网络文学影响下的高中作文批改与讲评 / 杨道州
- 背景资料:让阅读教学厚实起来 / 仇定荣
- 从听到读:汉语阅读的发展障碍 / 戴方文
- 论新课程背景下作文教学若干课型 / 贺晓刚
- 文本解读的“泛”与“实” / 程先国
- 向思维更深处漫溯 / 毕泗建
- 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嬗变之管窥 / 蒋玲慧
- 正确理解和把握高中语文新课标中的“阅读目标” / 魏政刚
- 立足语言本体,提升探究能力 / 蔡燕明
- 作文好题的标准 / 陈国仁
- 浅谈中学作文境界提升的途径 / 童县城
- 让文化底蕴提升作文品味 / 李小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