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9期
ID: 147287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9期
ID: 147287
祥林嫂的三“笑”
◇ 侯玉双
鲁迅小说《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一生备受凌辱、饱尝煎熬,最后悲惨地死去。那么这样一个人物,怎么能与“笑”联系起来呢?在小说中,有关祥林嫂的“笑”的描写有三处,作者这样安排不是偶然的,它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第一次“笑”。祥林嫂新死了丈夫,在家受婆婆虐待,婆婆为给第二个儿子娶妻,要把她卖掉。为挣脱牢笼,她只身逃出家门,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女工。其间,她“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鲁家的活计,“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一个女人、寡妇,只身出逃,寄人篱下,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本来是笑不起来的,但与原先在婆婆家里所遭受的精神折磨和生活上的痛苦相比,她自以为这就是幸福的,所以感到“满足”,自然就会“渐渐有了笑影”。一个“反满足”的“反”字,有力地说明了祥林嫂在婆婆家里遭受的族权迫害之烈,“笑”反衬出祥林嫂在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统治下的悲惨遭遇。
第二次“笑”。祥林嫂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族权的淫威,被婆家强卖改嫁后,又丧夫失子,无奈,第二次回到鲁家。这时的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了,而鲁家又把她看作“败坏风俗的”,精神遭受严重的打击,近乎一个麻木的人。然而此时,当柳妈问她是如何依从了贺老六时,祥林嫂竟“笑了”,“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这是作为女人羞涩难堪的笑?还是回忆那段生活舒心的笑?显然都不可能。失去做正常人资格的她,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些都不足以使她再笑起来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她“笑”呢?只能是作为一个女人,回忆与丈夫相亲相爱的情景,身心得到了享受和安慰,是人性真实自然的流露。这就给读者深刻的启示:不论封建社会给予中国劳动妇女多么深重的灾难,但在根本上她们要求做正常人的一切欲望是永远不可剥夺的。这一“笑”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违背人性、摧残人性的罪恶。
第三次“笑”。祥林嫂捐了门槛,“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因为一次次的打击,已把她逼到死亡的边缘,按她的理解,捐了门槛,就可“赎了这一世的罪名”,还要活下去。面对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打击,她不觉悟,只能逆来顺受,只要让她活下去,她就满足,就“高兴”。此时的“笑”,表明她对生活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多么执著,活得又多么卑微、多么悲惨。即使这样,封建礼教还是容不下她,年终祭祀时节,仍不许她沾手,终于将她置于死地,使她永远再“笑”不起来,成为一个求做“奴隶而不得”的阴魂。
纵观三次“笑”的描写,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层层推进地完成了祥林嫂这一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她是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压迫下劳动妇女的典型代表。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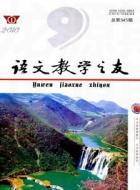
- 魏书生:“超语文”的教育价值 / 鲍艳华
- “深度语文”需要有深度的老师 / 张俊芳
- 语文课的几个坚持 / 王鸿斌 袁玉平
- 做一个真正的引领者 / 王 建
- 语文学习中的“攻心”与“放手” / 施 辉
- 写字教学如何在语文课中穿插进行 / 寇敏杰
- 浅谈创造性阅读及问题 / 杨林亚
- 古文教学中现代公民意识的渗透 / 薛胜元
- 对语文课堂几组对立关系的理性评判 / 陈红莲 成 龙
- 戴着“镣铐”也要跳出精彩的“舞蹈” / 盛维兴
- 辩证处理高中语文教学的几对关系 / 张 金
- 浅谈新课标下成功课堂的教学评价 / 陈福来
- 一次课堂讨论的反思 / 石国权
- 把课堂还给学生 / 费 洁 赵 钧
- 中学语文新诗教学内容调研 / 谭 悦
- 诗歌教学三法 / 于颖泓
- 从怦然心动到断然行动 / 杨陈军
- 苏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指瑕 / 丁大勇
- 淡妆浓抹总相宜 / 商庆国 周 军
- 英雄豪气撼乾坤 / 王继龙
- 初语课本文言文补注三则 / 周 雷
- 鲁迅小说中感叹号和破折号的用法探究 / 刘玉栋 刘忠香
- 《伤仲永》注解析疑 / 鲁永贵 朱怀芳
- “蓐”字辨义 / 谢兴圣
- 是感谢,还是嘲讽 / 黄兴亚
- 《核舟记》中的“船背”是指船顶还是船底 / 叶万金 袁传宝
- 祥林嫂的三“笑” / 侯玉双
- “寡妇起彷徨”正解 / 黄学军 黄云云
- 《孔雀东南飞》注释商兑一则 / 张小平
- 于细微处见精深 / 刘洪丽
- 苏教版高语必修五几处商榷 / 刘长宝 石 丽
- 妙手一笔夺人眼 真情流露自引人 / 段宗科
- “波及”误用一例 / 赵徐行
- 巧辨“带”与“戴” / 艾兴芳
- 流行歌曲与作文教学 / 李望成
- 责任,比技巧更重要的写作元素 / 赵 静
- 眉眼盈盈 引人入胜 / 张广胜
- 高考作文评价标准应坚持“有文采” / 刘华正
- 关于近十年高考语文全国卷大阅读的两点思考 / 李小玲
- 高分作文确立主题指要 / 唐文占
- 颇有深意的“罥烟眉”“含情目” / 马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