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10期
ID: 137640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10期
ID: 137640
前《赤壁赋》的思想情感何以如此复杂?
◇ 丁艳红
【摘 要】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说要学习前人的作品,必须知其人论其世,即必须深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才能得到更正确恰当的理解,把握作品的情感主旨。对于前《赤壁赋》这样一篇较难把握的文章,运用知人论世法以后,解读起来就相对容易而且深入得多了。
【关键词】前《赤壁赋》 知人论世 思想感情
苏轼的赤壁经典之一前《赤壁赋》历来在高中课本的讲解当中属于难点,其思想的复杂性,使很多教师不好把握,使学生更难理解。但是对于这样一篇复杂的思想情感经典,讲授时我们不忍心草草了事,也不愿意仅就文字表面做肤浅的阐释,更不想对其进行简单的处理,而分析作者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思想情感正是高考考纲当中探究题所要求的内容。那么对此文作一番认真深入的研究,更加精当深入地探究其思想情感,会有利于学生理解作品的复杂性。我在教学中尝试了用鉴赏诗歌的有效方法之一——知人论世法来进行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说要学习前人的作品,必须知其人论其世,即必须深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才能得到更正确恰当的理解,把握作品的情感主旨。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作团练副使。本文则作于元丰五年,距离苏轼被贬黄州已经两年多了。
苏轼自小受到儒学的影响,传统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深深融进了他的灵魂,使他很早就立下了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并成为一生的理想追求。他的仕途生涯是其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重要过程。他从政的原则是忠君、报国、利民,始终关心民生疾苦和国家安危,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党争中他不盲从、不徇私,不阿新党,也不附旧炎,只考虑是否有利于百姓和国家;虽然一生颠沛流离,却从未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勤政为民。
乌台诗案以前,应该说作者的仕途还算顺利,他的儒家之志也得到了实现。乌台诗案以后,被贬黄州,他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曾陷入苦闷与迷惘。那么当建功立业、经世济民的壮志难以实现时,他的思想便开始“向内转”,来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而佛老思想正满足了他这种内在精神上的要求。他吸收佛老思想中自认为有用的部分,并加以改造利用,创造性地把老庄哲学中从无限时间与空间来看待人生苦难、欢乐的观照方法以及物质都是运动的、无一事物可以长久等,与禅宗的“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进而求得了个人心灵的平静,使极度受伤疲惫的心得到了温暖的慰藉。
虽然用佛老思想暂时平复和抚慰了他痛苦的灵魂,但是儒家之志是其一生的追求,规定着他人生的基本方向,所以不可能完全忘情政治,很多时候因为外界事物的刺激和诱发,他便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了,理想壮志被激发,于是他的热情、志向、牢骚与不平以及牢骚后的自我解脱就会通过文学这一喷火口喷薄而出。所以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会错综纠结、不可分割。前《赤壁赋》正是体现这些复杂思想的一篇典型赋体文章。
宋代的黄州,即今天的湖北黄冈。黄冈西北的长江边上,有一处风景胜地,那里矗立着一座红褐色的山崖,因为形状有些像鼻子,所以人们称它为赤鼻矶。又因为山崖陡峭如一面墙壁,也称它为赤壁。它并不是三国时期赤壁大战的发生地。苏轼有名的两赋一词都写的是这里的赤壁,只是借题发挥,以之抒怀罢了。
赤壁泛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于是“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赤壁美景加上诗酒的陶醉,给苏轼郁闷、郁结的心灵带来了舒畅和洒脱,使其从现实的身心拘役中求得了解放,将有限的生命时光寓于无限的自由和想象之中,达到了庄子逍遥游的状态,仿佛自己已然是一个沉醉在大自然美好景色之中的仙人。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很明显这里的“美人”指的就是他一心想要报效的朝廷,或者是那个并不一定圣明的国君(美人代指国君,这在屈原的《离骚》里早已有之)。在封建知识分子的心里,君就是国,国就是君,所以不忘君,就是不忘国。因此这两句听起来好像是缠绵悱恻的情歌,实际上却婉转地流露出不受重用的郁结。渺渺兮予怀,直接写出了前途渺茫,内心痛苦,而后句借美人暗喻国君,可见哪怕是被捕被贬,苏轼还是没有忘记心中的美人——君主,暗喻含蓄、隐晦,教者需要点破讲解,以便学生了解苏轼时时不忘忠君报国的儒家思想。
然而当他想到自己功业未成,想到种种失意,又流露出浓厚的悲凉。以主客问答的赋体形式,通过客之口,表达了己之悲。客由赤壁的明月、江水、山川,想到了曹操的诗,想到曹操本人,那样一个一世之雄。在怀念英雄人物的同时,感叹着“故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英雄不在,往事如烟,世事无常。“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在茫茫宇宙和悠悠岁月中,感到人生短暂、生命渺小。这时道家的寻仙访道思想又涌上了作者心头——“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实在是伤感消极。
主人苏子的回答是自己劝慰自己、消解自己的悲观情绪。他同样以明月、江水作比,借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和物质是运动的观点,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写水的变),而未尝往也(写水的不变);盈虚者如彼(写月的变),而卒莫消长也(写月的不变)。”所以从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不曾已一瞬”(万物均变);从不变的角度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万物与人类都是永恒存在的,在广阔的宇宙中,人代代相传,也能永恒)。“而又何羡乎?”又何必羡慕长江无穷、明月永恒呢?又何必哀叹蜉蝣渺小、人生短暂?在这里,他跳出对个体生命哀叹,将其置于宇宙空间,与万物共观,观出生命在别样意义上的永恒——长江反复流转为无穷,明月反复圆缺为永恒,人类代代繁衍为永恒。自己有经典作品永恒,不也没枉活一生吗?于是客喜而笑,情感由悲转喜。苏轼最后运用道家的哲学思想,透过无限的宇宙空间来感悟体验有限的人生,精神获得了解脱。
最终,无论是人生的慨叹还是政治的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山水的依恋中得到了休憩。“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自然山水融入了苏轼的生活、兴趣和情感之中,充满了生命和情意,道化自然,物我两忘,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寄托,如他所羡慕的陶潜一样,纵情自然,心情豁达开朗。
因此文中借水月自然之景,巧妙地表达了作者由乐生悲、由悲转喜的解脱过程。情感的起伏变化既表达了作者失意时的苦闷、不平,又表现了作者在失意后善于自我解脱的旷达胸襟,蕴藉深沉。失意苦闷不平是由于儒家的用世之志受挫而生的,失意后的洒脱旷达则是佛道思想的劝慰。
结尾,既照应开头超然欲仙的快乐,又向政敌暗示:我虽然遭贬,但是日子过得洒脱自在,既不寂寞,也不苦恼。这实际是一种抗议,让我们隐隐地体会到他在自然水月中寻到的自在超脱是一种自我慰藉,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被贬黄州,第一次人生重击,儒家之志碰壁,佛道思想成了他精神的乐园,是他在最短时间内变地狱为天堂的思想武器。没有这一武器,在困难和打击面前他可能会消沉。但是他又不囿于某种思想,而是融合三家、外儒内道,在人生上、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上是进,是儒;在个人荣辱得失和功名利禄上是退,是道;再加上佛家的平常心,如此既超越了入世精神感召诱惑所带来的不安和焦躁,又不完全沉醉于自我解脱的清高与逍遥,以此来适应朝不虑夕、风云变幻的现实。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作品都是由于作者受到现实生活中某种因素的触动后有感而发的,它与作者的生平思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如果能够知人论世,就可以设身处地地揣摩作者的心境,运用合理想象,填补诗歌的空白;而相反,对于一些作品,如果不知其人其世,就看不出其佳致。对于前《赤壁赋》这样一篇较难把握的文章,运用知人论世法以后,解读起来就相对容易而且深入得多了。
★作者单位:辽宁省抚顺市第一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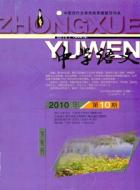
- 大阅读 / 赵 军
- 高中语文“问题教学”之问题探究 / 彭欣欣
- 对语文教学中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理性思考 / 章之文
-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师心理角色定位 / 毕海林
- 节日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价值体现 / 余晓琳
- 高中语文新课程如何实施研究性学习 / 肖革意
- 如何有效实施新课标下的语文教学活动 / 吴 平
- 浅谈语文有效课堂教学方略 / 高蓓蓓
- 新课标背景下的中学语文教学过程刍议 / 缪长春
- 把握教学关键,提高教学质量 / 罗祖堂
- 高中语文课堂调动学生 / 杨友生
- 例谈如何开发文本的“情感因素”进行审美教育 / 郭宏云
- 高中语文《陈情表》教学案例 / 李外平
- 还原语文课堂的灵性和生动 / 刘 建
- 情感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魅力 / 孙华标
- 《环球城市,风行绿墙》教学案例 / 陆炜炜
- 加强口语训练 提高表达能力 / 李娄佳
- 让心与心的距离不再遥远 / 王晓玮
- 给阅读教学少留点遗憾 / 任方菊
- 朗读是提高语文课堂效率的重要手段 / 孙 进
- 辅助 适度 灵活 精当 / 邵君华
- 找回文本的尊严 / 李国栋
- 浅谈朗读在诗歌教学中的运用 / 陈 皓
- 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 / 高 松
- 阅读赏析 / 胡小龙
- 巧借成语辅助文言文教学 / 邹海华
- 浅谈新课程下的古诗文教学 / 刘忠志
- 抓住学生学习特点,精心组织语文教学 / 邓小红
- 如何培养学生解读文章的能力 / 何 跃
- 《小狗包弟》教学设计 / 汪明爽 王良芬
- 多留些“空白”给学生 / 陆珍红
- 在语文教学中开展名著阅读的途径探索 / 易昌隆
- 中学语文活动课教学案例举隅 / 崔 岚
- 用“三激”激出语文教学的效率来 / 周卫芳
- 乐府诗苑的一朵奇葩 / 陈明华
- 高中语文作文指导教学案例 / 姜 玮
- 前《赤壁赋》的思想情感何以如此复杂? / 丁艳红
- 浅议鲁迅小说《祝福》的悲剧根源 / 王 岚
- 小事不小 / 刘小敏
-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如改为“杜媺投江” / 万元洪 孟 丽
- 两次视角换位 实现生命定位 / 王庆林
- 留白的艺术 想象的空间 / 周琴娥
- 屡借山水以化郁结 / 房改华
- 浅谈诗歌的抒情方式与思想内容 / 郭 德
- 善用课本 巧换视角 一材多用 / 李 华
- 马嵬香消千古恨 / 杨继武
- 诗歌教学中诵读和赏析的关系及处理 / 闭秀丽
- 感悟型话题作文的写作技巧 / 李富春
- 语文教学:为谁辛苦为谁忙 / 黄志雄
- 深入文本 品味小说 / 阮士荣
- 文贵合体 / 李俊杰
- 弘扬中华文化,重视书法教学 / 唐泓清
- 一份有失公平\公正的高考语文卷 / 胡锡良 李建林
- “五段三论”,主论“三分”:规范议论文的基本模式 / 杨志芳
- 闲话高考说人文 / 吴锡志
- 创设写作情境 促进协作学习 / 谢奎琴
- 用细节说话 / 周 涛
- 语文个性化教学的三个支点 / 高冬梅
- 原生态生活 / 程华石
- 也谈“异乎三子者之撰” / 杨鸿雁
- 勤写不辍 个性自见 / 张自龙
- 类比论证耶?比喻论证耶? / 胡月丽
- 高三作文教学现状及应对策略 / 陈亚飞
- 比较《诗经》民歌与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 曾 艳
- 让语文教学“灵动”起来 / 陈 华
- 破茧化蝶 / 刘咏梅
- 说说新闻材料的“用”点 / 刘淑梅 李德树
- 语文教学应该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 覃雪梅
- 如何打造考场作文的精品 / 钱嘉永
- 理性.思辨.个性 / 蒋芸云
- 如何发展学生的个性 / 杨猛刚
- 考场作文取胜要素之文采篇 / 黄胜利
- 语文教学妙在读 / 修国富
- 高考语文试题解答方略举隅 / 陶玉鑫
- 对江苏高考作文中呈现的问题的分析 / 徐玉荃
- 语文课上老师多讲些如何? / 云传瑶
- 社科文阅读解题步骤例析 / 石光辉
- “图文转换题”解题步骤及技巧初探 / 瞿德超
- 高考文言文复习应强化几个意识 / 冯 莉
- 高三语文复习的方法策略摭谈 / 杨 灿
- 文言断句 有“法”可依 / 刘 阐
- 万诗题入手 抓题作文章 / 丁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