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10期
ID: 137667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10期
ID: 137667
比较《诗经》民歌与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 曾 艳
【摘 要】作为中国早期民歌的代表,《诗经》和汉乐府在艺术特色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如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比兴手法的运用、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等等。但是它们之所以被后人记住更在于它们的相异之处:《诗经》是我国抒情性民歌的代表,汉乐府的叙事性是它的最高成就;四言和五言分别是它们各自对中国民歌语言的贡献;浪漫主义手法在汉乐府民歌中的添加,丰富了民歌的表现手法。
【关键词】民歌 《诗经》 汉乐府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抒情性 叙事性
一、《诗经》民歌与汉乐府民歌在艺术方面的一脉相承之处
1.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汉乐府民歌对《诗经》民歌艺术特色的最大的继承
我们都知道《诗经》民歌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尤其是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大。是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只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的民歌都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民歌到近代的民歌创作,几乎所有作家、诗人都以其为出发点。汉乐府民歌直接继承由《诗经》“国风”开创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无论是从体裁上、内容描写上,还是现实主义特色的运用上,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引领着后世诗人走向更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因此,它的许多诗篇都起到示范的作用。
汉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但是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体裁都很相似,体现了汉乐府民歌对《诗经》民歌内容上的继承。《诗经》民歌中有许多描写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作品。人类自从有了阶级之分便产生了剥削和压迫,于是从《诗经·国风》的《魏风·伐檀》中我们看到了一群伐木奴隶悲惨的生活画面,《豳风·七月》里劳动人民无冬无夏地劳作,仍过着衣食不得温饱、房屋不得抵御风寒的苦难生活。到了汉代,封建统治正式确立并加以巩固,封建君主不仅从肉体上还从精神上双重地压迫着劳动人民。对此,汉乐府民歌都有反应,而且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更加彻底,描写的事情也更加具体。《病妇行》描述了在残酷的剥削下妻子死亡、父子不能相保的悲剧。《燕歌行》表现了“流宕在他乡”的破产农民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而《平陵东》则揭露了官府的暗无天日、官吏的贪暴枉法,他们敲骨吸髓地剥削还不够,竟然绑架勒索,逼得善良的百姓只好卖牛赎人。
除此之外,无论是汉乐府民歌还是《诗经》民歌,都有许多描写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的作品。“国风”中《邶风·式微》、《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都反映了劳动人民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下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乐府民歌《十五从军行》、《古歌》、《悲歌》、《饮马长城窟行》等诗篇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人民对战争和徭役的怨愤。
《诗经·国风》里有很多歌颂爱情的恋歌作品,汉代虽然封建礼教压迫加重,但也不乏有热情、大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情歌作品,代表作品有《有所思》和《上邪》等。由于劳动人民经济地位、劳动生活的决定,这时的恋歌大都是积极、乐观的基调,这样的作品有《郑风·溱淤》、《郑风·狡童》、《郑风·褰裳》、《邶风·静女》、《卫风·木瓜》等。但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妇女特殊的社会地位,不合理的婚姻带给她们更深的痛苦,于是无论是在《诗经》民歌中还是在汉乐府民歌中都有很多以弃妇为描写对象的作品。
2.比兴手法的使用
“比兴”手法,起源于《诗经》,其基本的含义据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换句话说,“比”就是譬喻,其中“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比兴》),使形象更加鲜明。如《魏风·硕鼠》用大老鼠来比喻贪得无厌的奴隶主。《邶风·新台》用癞蛤蟆比喻荒淫无耻的卫宣公。《魏风·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比喻夫妇爱情的变化,都很生动形象。“兴”的基本含义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以引出所要歌咏的对象。这种起兴,往往起到联想、象征、暗示、烘托的作用,有引人入胜之妙。如《秦风·黄鸟》首章:“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开头首句即是起兴,与下文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它的作用只是为了引起下文,给人以联想,使诗歌曲折委婉。但有的起兴和下文有联系,大抵同样起着比喻的作用。如《周南·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田,宜其室家。”开头的两句起兴,以鲜艳盛开的桃花来比喻行将出嫁的女子光彩焕发的姿容。
汉乐府民歌继续沿用《诗经·国风》传统的“比兴”表现手法。汉乐府民歌“比”的使用一方面除了直接用比喻外,还出现了寓言性的民歌,这是它比《诗经》民歌进步的一个方面。《乌生》与《枯鱼过河》是这方面的代表,诗作用乌鸦和枯鱼的遭遇比喻人民当时的处境。《乌生》借中弹身死的乌鸦的自宽自解,指出即使是山中的白鹭、天上的黄鹂、深渊的鲤鱼也都难逃一死,更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人民的命运,一定也是一样的悲惨。“兴”的运用也与过去一样,如《白头吟》的开头“起兴”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用雪和月比喻自己光明、纯洁的爱情信仰,这与男方卑鄙龌龊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还有《孔雀东南飞》开头“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的起兴,为全文奠定了哀伤的基调,喻示着焦刘爱情的悲剧。
二、《诗经》民歌与汉乐府民歌在艺术特色上的相异处
1.《诗经》民歌好似民间的风情画,而汉乐府民歌宛如人间的冷暖图
《诗经》民歌是周代民间的一幅幅风情画,它大都是直接抒发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抒情性民歌。在讽刺统治者残酷剥削的《伐檀》中,人民大胆地提出正义的责问:为什么整天都在劳动的人民无衣无食,而那些“不稼不樯”、“不狩不猎”的人,反而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它们往往以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事情,感受生活,表达爱憎。不仅如此,作者们抒发感情的方式也是坦率的,如表达相思,就直接说“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爱情受到阻碍,则大呼“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柏舟》);而且,就连一些叙事性的作品也同样有抒情的穿插,如《七月》本是叙述农民一年四季辛勤的繁重的劳作,其中便不时穿插了“无衣无褐,无以卒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样抒情化的诗句。何休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是对《诗经》民歌抒情性的最好的评价。
汉乐府民歌被我们称为人间的冷暖图,是因为它的叙事性。我们知道,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在于它的叙事性,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在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中,许多非常生动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它们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是复杂的生活矛盾的集中表现。通过这些典型的细节,深刻地揭示了作品所反映的主要矛盾及其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因此,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和高度的典型概括相统一,是汉乐府民歌叙事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如《孤儿行》这首诗,描写兄嫂虐待孤弟,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主奴的关系。通篇只讲了三件事,即兄嫂命令孤弟为他们经商、汲水和收瓜。特别是“瓜车反覆”这一个情节,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构成了一个矛盾发展异常集中、紧凑的戏剧性场面。这个情节是写孤儿为兄嫂收瓜,回家途中,瓜车翻了,这时抢瓜吃的人多,帮助扶车的人少,孤儿手足无措,心中十分愁急,他哀告吃瓜的众人说:“愿还我蒂,兄与嫂严!”但又恐惧地在想,即使有了瓜蒂,兄嫂还是不会与他干休的。正如清人李因笃所说:“曰‘愿还我蒂’,将以蒂自明也。又云当兴较计’,则出瓜蒂亦不足塞责。数句之中,多少曲折。”(《汉诗音注》)忽然,里中又传来了一片吵闹的声响,原来兄嫂已经知道了翻车的事而在大发雷霆了。描述这一段情节,仅仅用了三十字左右,却首先说明孤儿因车重力弱而翻了车,正是兄嫂对他的残酷奴役;其次抢瓜人多、扶车人少是旧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活生生的表现,更加突出了孤儿处境的困难;再次是孤儿紧张复杂的内心活动,他预料到兄嫂决不会善罢甘休;最后兄嫂的大吵大闹又把以上一切矛盾集中到主奴之间的主要矛盾上来。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瓜车反覆”这个结点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所以这是一个对于现实生活高度集中概括的典型的情节。汉乐府民歌中这些典型细节的刻画,对于《诗经》民歌中的叙事成分来说是一种显著的发展,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加强了叙事的曲折和波澜,更重要的是使整个故事情节在矛盾斗争中深入展开,因而高度概括地反映出社会现实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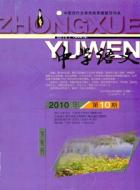
- 大阅读 / 赵 军
- 高中语文“问题教学”之问题探究 / 彭欣欣
- 对语文教学中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理性思考 / 章之文
-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师心理角色定位 / 毕海林
- 节日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价值体现 / 余晓琳
- 高中语文新课程如何实施研究性学习 / 肖革意
- 如何有效实施新课标下的语文教学活动 / 吴 平
- 浅谈语文有效课堂教学方略 / 高蓓蓓
- 新课标背景下的中学语文教学过程刍议 / 缪长春
- 把握教学关键,提高教学质量 / 罗祖堂
- 高中语文课堂调动学生 / 杨友生
- 例谈如何开发文本的“情感因素”进行审美教育 / 郭宏云
- 高中语文《陈情表》教学案例 / 李外平
- 还原语文课堂的灵性和生动 / 刘 建
- 情感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魅力 / 孙华标
- 《环球城市,风行绿墙》教学案例 / 陆炜炜
- 加强口语训练 提高表达能力 / 李娄佳
- 让心与心的距离不再遥远 / 王晓玮
- 给阅读教学少留点遗憾 / 任方菊
- 朗读是提高语文课堂效率的重要手段 / 孙 进
- 辅助 适度 灵活 精当 / 邵君华
- 找回文本的尊严 / 李国栋
- 浅谈朗读在诗歌教学中的运用 / 陈 皓
- 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 / 高 松
- 阅读赏析 / 胡小龙
- 巧借成语辅助文言文教学 / 邹海华
- 浅谈新课程下的古诗文教学 / 刘忠志
- 抓住学生学习特点,精心组织语文教学 / 邓小红
- 如何培养学生解读文章的能力 / 何 跃
- 《小狗包弟》教学设计 / 汪明爽 王良芬
- 多留些“空白”给学生 / 陆珍红
- 在语文教学中开展名著阅读的途径探索 / 易昌隆
- 中学语文活动课教学案例举隅 / 崔 岚
- 用“三激”激出语文教学的效率来 / 周卫芳
- 乐府诗苑的一朵奇葩 / 陈明华
- 高中语文作文指导教学案例 / 姜 玮
- 前《赤壁赋》的思想情感何以如此复杂? / 丁艳红
- 浅议鲁迅小说《祝福》的悲剧根源 / 王 岚
- 小事不小 / 刘小敏
-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如改为“杜媺投江” / 万元洪 孟 丽
- 两次视角换位 实现生命定位 / 王庆林
- 留白的艺术 想象的空间 / 周琴娥
- 屡借山水以化郁结 / 房改华
- 浅谈诗歌的抒情方式与思想内容 / 郭 德
- 善用课本 巧换视角 一材多用 / 李 华
- 马嵬香消千古恨 / 杨继武
- 诗歌教学中诵读和赏析的关系及处理 / 闭秀丽
- 感悟型话题作文的写作技巧 / 李富春
- 语文教学:为谁辛苦为谁忙 / 黄志雄
- 深入文本 品味小说 / 阮士荣
- 文贵合体 / 李俊杰
- 弘扬中华文化,重视书法教学 / 唐泓清
- 一份有失公平\公正的高考语文卷 / 胡锡良 李建林
- “五段三论”,主论“三分”:规范议论文的基本模式 / 杨志芳
- 闲话高考说人文 / 吴锡志
- 创设写作情境 促进协作学习 / 谢奎琴
- 用细节说话 / 周 涛
- 语文个性化教学的三个支点 / 高冬梅
- 原生态生活 / 程华石
- 也谈“异乎三子者之撰” / 杨鸿雁
- 勤写不辍 个性自见 / 张自龙
- 类比论证耶?比喻论证耶? / 胡月丽
- 高三作文教学现状及应对策略 / 陈亚飞
- 比较《诗经》民歌与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 曾 艳
- 让语文教学“灵动”起来 / 陈 华
- 破茧化蝶 / 刘咏梅
- 说说新闻材料的“用”点 / 刘淑梅 李德树
- 语文教学应该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 覃雪梅
- 如何打造考场作文的精品 / 钱嘉永
- 理性.思辨.个性 / 蒋芸云
- 如何发展学生的个性 / 杨猛刚
- 考场作文取胜要素之文采篇 / 黄胜利
- 语文教学妙在读 / 修国富
- 高考语文试题解答方略举隅 / 陶玉鑫
- 对江苏高考作文中呈现的问题的分析 / 徐玉荃
- 语文课上老师多讲些如何? / 云传瑶
- 社科文阅读解题步骤例析 / 石光辉
- “图文转换题”解题步骤及技巧初探 / 瞿德超
- 高考文言文复习应强化几个意识 / 冯 莉
- 高三语文复习的方法策略摭谈 / 杨 灿
- 文言断句 有“法”可依 / 刘 阐
- 万诗题入手 抓题作文章 / 丁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