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5期
ID: 136225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5期
ID: 136225
刘邦无赖说
◇ 肖 科
一、历史与文学:大相径庭的两个刘邦形象
以同一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而塑造出大相径庭的形象,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乏先例。但是。同以刘邦为蓝本、又同以刘邦做了皇帝的第十二年十月“还乡”为创作素材,司马迁和睢景臣却给我们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且尖锐对立的形象,实属罕见。这两个刘邦:一个典雅庄重,是关心民生、对故土乡亲一往情深的贤明君主:一个则低俗卑劣,是恶德昭彰的小人、市井无赖。
在司马迁笔下,高祖的这次荣归故里真可谓“君亲民爱”的佳话。我们看看他笔下其乐融融的景象吧:(高祖)“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酒酣耳热,还亲自击筑,教沛中儿童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还亲自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并满怀深情地对沛县父老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刘邦还宣布,永远免除沛县的赋税徭役。“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县空城为他送行。(《史记·高祖本记》)
元代的才子睢景臣无疑受过历史文献的启示。但他的高明和奇异之处在于。他剥去了传扬了1500年的所谓“君亲民爱”佳话的神圣伪装。而精心变它为一出令人喷饭的闹剧。在睢景臣笔下,刘邦没有了荣耀,缺少了受欢迎的盛况,更没有了故土乡亲的深情。作家选择了一个熟悉刘邦根底的乡民作视角,来看刘邦贵为天子后回乡摆阔的得意情景,还重点将刘邦早年的一些“糗”事抖露出来:
[二煞]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犋扶锄。
[一煞]眷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拔还,欠我的栗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撮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刘三”的“不良记录”有欠账不还,小偷小摸等,从而在乡民的眼中,贵为天子的刘邦的迎驾人员是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象征帝王尊严的仪仗也粗俗不堪,如“凤旗”好像“鸡学舞”。“飞黄旗”是“狗生双翅”,“蟠龙戏珠”是“蛇缠葫芦”……如此种种皆因恨人及物:睢氏鄙弃刘邦的人格品行,故寄怒骂于嬉笑之中,让这个神圣的帝王名誉扫地。
二、个中原因:历史与文学的不同价值取向
在作家队伍中,人们素来偏好较为奇异的那类;同样,无论古今的作品,受众亦都不喜欢平庸。因而作为创造语言艺术的作家,应当有不同凡响的表现。大雅。抑或大俗,在他们那儿不过都是才智奔放的载体,是心灵冲撞的电光石火。司马迁是颇有才情的一代文豪,而睢景臣也不是平庸之辈,并且还是富有才情的高手,据《录鬼簿》记载:睢景臣这个扬州人,心性聪明。可以无讳地说,他所走的路正是一个具有创意与天才的作家所应走的道路,这一点全然可由摆在世人面前的别开生面的《哨遍·高祖还乡》来予以印证。
也许会有人认为睢氏“丑”化了历史人物刘邦。甚至指责他没能像历史学家那样从社会发展过程中去肯定刘邦的历史功绩。对此,笔者只想做两点提醒:一是人们对刘邦人品的反感,应该是普遍存在的。魏晋名人阮籍过广武战场有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可能是我们能见到的文人最早“羞辱”刘邦的语言。开了骂刘邦之先河,打响了对刘邦发难的第一枪。不要小看阮籍的区区九个字,其杀伤力非同小可。而这九个字里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字——“竖子”。正是“竖子”这两个字,就硬生生地把颠秦踬楚的大英雄汉高祖从神坛上拉了下来。《词典》中对竖子的解释是,小子。其贬义色彩非常明显,应该含有“不值得认真对待,不是玩艺儿。不是东西”等意思。那么。后世对汉高祖的痛恨,多多少少与这个用词有绝大关系。二是《哨遍·高祖还乡》明明白白乃一戏曲(元曲之“散曲”),系文学作品;而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对象是“人”,那么戏曲无疑应当写出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而不仅仅是他的历史功绩。如果说,历史学家所关心的主要是可见世界、物质世界,那么文学家则更重视的是内心世界、精神世界。
谁也否定不了,历史的刘邦是个英雄、了不起的帝王,影响推动过历史的进程,但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在另一面(文学的一面),他更多的是以一个颇“赖皮”的阴谋诡计者形象留在人们的道德天平之上;至于各种劣迹也是屡见不鲜,即便是正史的作者也多不回避的:①在战胜敌手、创建霸业的过程中,他曾经挥霍过惨重的人力物力为其服务,《高祖本纪》载:“汉五年……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仅此一例可见一斑。②刘邦少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游手好闲,结交社会闲散朋友,且好酒及色;③刘邦曾经“弃子抛父”——楚汉相争时,刘邦彭城兵败,只身逃走,由于后面楚军追赶急追,刘邦嫌车重太慢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项羽为了要挟刘邦,将刘邦的父亲太公抓去做人质,说:“你若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吃了。”刘邦不为所动,还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④刘邦脸皮厚,喜好大言不惭。一次沛县县令好友吕公。为避仇携带家眷来到沛县投靠朋友。城里众官吏前往聚宴,刘邦身无分文却在自己的贺柬上手书“贺钱万”,并不谦让,做了宴会的第一嘉宾;⑤刘邦为人倨傲。轻侮儒生。他“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儒生郦食其求见刘邦时,刘邦的侍卫对郦食其说:“(刘邦)不喜欢儒生,许多头戴儒生帽子的人来见他,他就当众把这些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往帽子里撒尿。”待郦食其获见刘邦时,“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因此,对刘邦而言。历史功过的评价并不等于也代替不了行为动机与道德情操的评判,其历史贡献的大小多少与道德情操上的是非善恶并不完全一致。刘邦在文艺作品中也就并不必然成为真善美的理想人物和正面形象。
睢氏把刘邦塑造为反面人物自有道理。体现了历史与文学的不同价值取向。这种处理自出机杼。尽管它可能不完全符合历史学家的看法。但刘邦作为艺术长廊中的一个形象,却深深“活”在人们的心中。欣赏者应认识到,睢氏关注的是作为一个“人”的刘邦,更可能是从“见善若惊,嫉恶如仇”的民族共性出发鄙弃刘邦的人格品行。
我们也相信,划邦之卑鄙无赖不会如此之甚。司马迁在《高祖本纪》开篇就流露出好印象:“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而在《高祖本纪赞》中也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健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的口气近乎推崇备至、倾倒不已了:“然王迹之兴,起于闻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据说直到元代。刘邦庙中的香火始终很盛。
只是睢景臣既然想把他当反面典型来刻画。于是就天下无赖之恶行皆归焉,把功大于罪的历史评价一改为恶多于善的道德评判。这种做法,若按严格的历史真实性的要求,对划邦确有某些不公之处。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一形象在艺术上是真实可信的。文学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自这首元曲《高祖还乡》问世以来,赢得了代代读者异口同声的赞誉:著名的《录鬼簿》认为,在众多写高祖还乡的元曲中。最为新奇的是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从而成为“压倒各家”的作品;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称之为“讽世的喜剧”;郑振铎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赞它“确实一篇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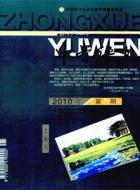
- 语言训练的批判与重构 / 申宣成
- 古典诗词教学三重奏 / 沈海中
- 课堂提问的辩证艺术与逆反处理 / 葛德均
- 应重视引导学生感受课文 / 殷长青
- 简约,让预设更精致 / 戴继华
- 阅读教学要强化“六种意识” / 杨生栋
- 文学知识形态转换模型简说 / 胡根林
- “花木”深处见“禅房” / 李仁甫
- 阅读者的身份转换:阅读教学的起点与可能的终点 / 朱建军
- 专制奴役的整体性隐喻 / 文 勇 孙绍振
- 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的定位思考 / 洪合民
- 孤独远行 卓尔不群 / 龙 健
-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实录及评点 / 余映潮 柳咏梅
- 天然去雕饰 浓情出淡语 / 张 坤 王志强
- 刘邦无赖说 / 肖 科
- 吹尽黄沙始到金 / 谭梦诗
- 谈借重《说文解字》提高汉字教学质量 / 赵乔翔 常萍萍
- 生态学视域下的作文教学策略初探 / 袁爱国
- 浮华洗尽见真淳 / 唐弋菱
- 新课标下的实践性作文教学 / 王庆林 翟启明
- “北”为何当打败仗讲? / 石 云
- 老师,你会指导写作吗? / 崔益林
- 谈谈《勾践灭吴》中三个疑难旬的翻译 / 唐家龙
- 动态命题的层递性 / 肖炎方 肖 郁
- “理论”与“实践”的合璧 / 屠锦红
- “创新”作文该休矣 / 刘思明
- 例谈文学作品中的“两个世界” / 张旺生
- 反向调节法:语文教学中心育渗透的有效途径 / 邹艳萍
- 浅谈高中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心理基础 / 冯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