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5期
ID: 136224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5期
ID: 136224
天然去雕饰 浓情出淡语
◇ 张 坤 王志强
追求用词的绮丽,是中学生在写作中常犯的毛病。文章的优美是不是靠语言的华丽?不是的。真正优美动人的文章,语言往往是最朴素、自然和平易近人的。苏联文学家高尔基说的好:“真正的艺术往往是十分朴素的,明白如话的,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的。”著名作家杨绛的文章《老王》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很值得我们读一读,品一品。
《老王》这篇文章并没有华丽的形容词和优美的修饰语,文章只是把老王不幸的遭遇、艰难的人生、金子般宝贵的品质和人间最珍贵的真情,寓于平淡如水、质朴无华的叙述中。作者以一种平和、平静的态度款款道来,无论记叙事件,还是赞否人物,都是淡淡的、悠悠的,言浅而意深情浓,浑然天成,深深打动了读者。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语言的功力。
具体说来,《老王》语言的朴素之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品味:
一是朴素之中现真情。这篇文章的语言虽朴实无华,但因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因此显得相当的感人。如文章在讲到老王的一只眼睛为什么会瞎时,文中说:“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我”在前面所闻的基础上做了两种推测,两次提到“不幸”,在平淡的叙述中对老王的遭遇寄寓深深的关切和同情。又如在文章结尾,当“我”知道老王在送鸡蛋和香油后的第二天就死了,写道“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一个著名的学者对社会上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发出肺腑的感叹,流露了对弱者的悲悯情怀,它可贵在“我”毫无掩饰,敞开心扉,反省自己,“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了他”。“我”在人格上真正尊重老王了吗?它的深刻在于用最朴实最本色的语言引发我们关注并帮助社会上的弱者。思考如何尊重他们,因为平凡的他们以诚实的品格守护着社会的良知,他们的人格是高尚的,他们的精神如同日月星辰,在历史的苍穹中永远发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曲高和寡难以产生演奏者和欣赏者共鸣的效应。寻常的人和事,实实在在的感情,用本色无华的语言串起。人眼人心,欣赏者不被感动都难!
二是朴素之中显匠心。这篇文章中语言的朴素与平淡。并不是作者随意而为,草就而写,而是处处显示出了作者的匠心独运。《老王》是一篇写入记事的散文,重点回忆了“我”与老王交往的四个生活片段。在记叙的过程中前三个片段略写,详写了他在去世前的一天硬撑着身子给“我”送香油和鸡蛋一事,人物刻画极其细致逼真,有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从语言描写看,有“嗯”“我不吃”、“我不是要钱”,简简单单,却意味无穷。老王是一个老实巴交、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善言辞的入力车夫,因此他的语言非常简短。仔细推敲,“我不吃”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同样最后一句话也没有从正面回答。如果要直接明确地回答,可以说:“杨先生,您平时对我很照顾,我也没有什么送给您,这点儿鸡蛋和这瓶香油您一定得收下,算让我表示点谢意,可千万别跟我提钱。”但这像一个垂死的、忠厚老实的平民说的话吗?矫情失真,还不如简约。
这里我们所说的匠心与刻意是不同的,刻意会留下痕迹,匠心是不露蛛丝马迹。语言是思维的载体。精辟的语言和思维是浑然天成的。
三是朴素之中见理趣。这篇文章语言的朴素并不是平淡如自开水,而是处处显示出一种理趣之智、情趣之美,读来让人爱不释手。如文章在写“老王”给我家送冰块时写道:“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前任”一般用在比较庄重的场合,比如美国前任总统布什,在此处用“前任”有诙谐幽默之感。同时,文章仿佛又在说“老王”虽然在做送冰这样一件非常普通甚至不起眼的事,但是他很努力认真地在做,他老实本分。不欺骗消费者。这又在诙谐的外表下多了一种厚重。又如在写他在去世的前一天硬撑着身子给“我”送香油和鸡蛋一事时对他肖像的刻画:“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白骨”。作者用夸张的修辞凸显老王临死前消瘦无力的情形,非常逼真,还有点滑稽感。但读者是笑不出的。只会觉得心灵深处在隐隐作痛,只会为他知恩图报、至死不忘的善良的心而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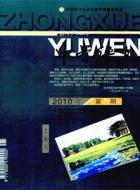
- 语言训练的批判与重构 / 申宣成
- 古典诗词教学三重奏 / 沈海中
- 课堂提问的辩证艺术与逆反处理 / 葛德均
- 应重视引导学生感受课文 / 殷长青
- 简约,让预设更精致 / 戴继华
- 阅读教学要强化“六种意识” / 杨生栋
- 文学知识形态转换模型简说 / 胡根林
- “花木”深处见“禅房” / 李仁甫
- 阅读者的身份转换:阅读教学的起点与可能的终点 / 朱建军
- 专制奴役的整体性隐喻 / 文 勇 孙绍振
- 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的定位思考 / 洪合民
- 孤独远行 卓尔不群 / 龙 健
-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实录及评点 / 余映潮 柳咏梅
- 天然去雕饰 浓情出淡语 / 张 坤 王志强
- 刘邦无赖说 / 肖 科
- 吹尽黄沙始到金 / 谭梦诗
- 谈借重《说文解字》提高汉字教学质量 / 赵乔翔 常萍萍
- 生态学视域下的作文教学策略初探 / 袁爱国
- 浮华洗尽见真淳 / 唐弋菱
- 新课标下的实践性作文教学 / 王庆林 翟启明
- “北”为何当打败仗讲? / 石 云
- 老师,你会指导写作吗? / 崔益林
- 谈谈《勾践灭吴》中三个疑难旬的翻译 / 唐家龙
- 动态命题的层递性 / 肖炎方 肖 郁
- “理论”与“实践”的合璧 / 屠锦红
- “创新”作文该休矣 / 刘思明
- 例谈文学作品中的“两个世界” / 张旺生
- 反向调节法:语文教学中心育渗透的有效途径 / 邹艳萍
- 浅谈高中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心理基础 / 冯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