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5期
ID: 13619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5期
ID: 136197
语言训练的批判与重构
◇ 申宣成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语文教育“泛人文化”的取向遭到批评和质疑,“语文知识”、“语言训练”等一度被淡出的词语再次回归语文研究的视域。2007年第10期的《中学语文教学》,集中刊发了一组讨论语文知识的文章,王荣生、王鹏伟、陈钟樑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语文知识的重要性。2008年,吴忠豪在《关于语文训练的讨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语文课程不能没有训练”的观点(《课程·教材·教法》2008年第12期);2009年,倪文锦在《正确处理和认识语文教学中的多种关系》(2009年第6期《中学语文》)以及其他相关文章中反复强调了语文知识和语言训练的价值。
2009年,语文界在对“语言训练”作出价值澄清的同肘。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其做了重构和批判。如,语文教学为何要回归语言训练?回归的语言训练的内涵将发生哪些改变?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怎样落实语言训练?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教师理解和落实语文课程标准,准确把握语文课程发展的方向。及时调整语文课程实施的策略,无疑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的3篇文章,分别从知识分类、认知过程、实离策略的角度对“语言训练”做了重构和批判,为深入理解语言训练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视角。
[评议文章]李海林《重构“语言训练观”》,原载于《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12期。
[原文提要]
“训练”的放逐与回归都是语文教学的进步,语言训练被放逐是因为它把一些不该与自己联系在一起的知识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回归语言训练需要重构知识和训练的关系:新的语言训练观是“用知识去练”,而不是“操练知识”,它是一种言语智慧训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活动化的教学形态构建;什么样的知识介入活动过程:活动完成时学生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等诸多方面。
该文从新的知识分类入手,以逻辑推理的方式,构建了“活”的语言训练观。
1.以颇具理性力量的逻辑分析,反思了十多年前“语文大讨论”的价值和局限。
李海林先生认为十多年前,由《北京文学》发轫的语文大讨论的价值在于以典型的案例击中了语文教学的“软肋”:教了不需要教的知识(如“翁”字的第七画是点还是折):把无法或不必要知识化的内容教成知识(如解释“灰溜溜”的意思);将不必标准化的知识以标准化形式教给学生(如答案只能是齐心协力,而不是同心协力)。进而肯定这次大讨论的价值:批判了语文教学中的唯“知识化”倾向,对正确认识现代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同时,作者认为,本次讨论最大的局限在于对语言训练做了简单化处理,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站在新的知识观的角度反思当时的讨论,作者认为,当时的讨论忽略了一些关键的问题,如:①在语文课中有没有需要教的知识,需要什么样的知识;②什么样的知识必须知识化,什么样的知识不必知识化,如果不必知识化,那么这些知识又以什么形态出现;③什么样的知识可以标准化,什么样的知识不可以标准化。它们各自在语文课中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等等。而正是这些思维的断点埋下了新课程改革中“泛人文化”的隐患。
2.以新的知识观为基础推演并重构了新的语言训练观。
连接起这些思维的断点,需要新的知识观。因为在作者看来,曾经被称为语文教学“八字宪法”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仅仅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偏狭的语文知识观导致了偏狭的语言训练观,使语文教学陷入了单纯的知识操练、繁琐的内容肢解和静态的语言分析的泥潭。为此。作者作了三步推演:
第一步,引入新的知识分类体系。把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无意识知识(语感)、言述性知识(李海林先生在他和王荣生主编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新探·学理基础》的第33-48页对各类知识有详细的解释)。
第二步,把新的知识分类与语言训练匹配,获得四种语言训练的类型:练知识(训练陈述性知识);练然后知或知然后练(训练策略性知识):用知识练(训练程序性知识);练即知识(训练无意识知识)。
第三步,其中的“用知识练”(训练程序性知识)意味着语言活动的开展必须“用知识来指导”,对于这类知识来说,语言教学非要有“语言训练”不可。
这一结论的巨大价值在于,它以新的知识观和严密的逻辑推演。从学理分析的角度证明了语言训练的合理性。就世界课程与教学研究发展的路向而言,知识类型的研究一直与其相依相伴。2001年,我国启动了新课程改革,本次课程改革提出了淡化知识、强调能力的理念。而恰在这一年,由当今最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课程与教学专家、测量评价专家和一线教师合作(皮连生语),出版了《学习、教学与评估的分类学: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该书从新的知识分类人手。重构了知识和教学的关系。研究者把知识归纳为四类,即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概念性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onwledge)和反省认知知识(metacongitive knowledge)。这充分表明,在世界课程与教学领域。知识并没有丧失其重要的地位。在新课程改革进入森林腹地之时,李海林先生从新的知识观推演出新的语言训练观,既是对语文学科历史和现状的思考,也符合世界课程与教学发展的逻辑。
3.把语言训练定义为言语智慧训练。
作者认为,所谓的“言语智慧”。是指言语主体(学生)在处理与言语对象和言语环境各要素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质和自由状态。这一定义所传达的意思是,言语智慧就是语言运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自由性。语言训练,就是由“练知识”向“练技能”、“练智慧”转变;就是引导学生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学会语言怎么用。而不是在知识系统传授的过程中记住语言是什么。与过去机械记忆和操练的语言训练形式不同,新的语言训练必须具备新的教学形态。这种新的教学形态,用课标的语言说,就是“言语实践”,通俗地讲,就是“搞活动”。然而,这里所谓的“活动”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老师讲讲,学生动动”,作为语言训练的新的形态,它必须具备明确的教学指向,具体表现在,学科知识的介入程度、学生个体的参与程度和学生经验的改变程度等。
[评议文章]王尚文、王诗客《语文课是语文实践活动课》,原载于《课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4期。
[原文提要]
为了纠正目前语文教学领域普遍而严重存在着的非语文、泛语文现象,有必要再次强调“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一语文质的规定性,进而明确在教师的引领之下,以学生为主体的读写听说等实践活动是培养、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主要途径。而“语文实践”和“语文训练”虽有联系,更有质的区别。
该文从认知过程的分析人手,批判了“死”的“语言训练观”,强调了以“运用”为核心的语文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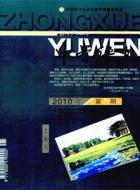
- 语言训练的批判与重构 / 申宣成
- 古典诗词教学三重奏 / 沈海中
- 课堂提问的辩证艺术与逆反处理 / 葛德均
- 应重视引导学生感受课文 / 殷长青
- 简约,让预设更精致 / 戴继华
- 阅读教学要强化“六种意识” / 杨生栋
- 文学知识形态转换模型简说 / 胡根林
- “花木”深处见“禅房” / 李仁甫
- 阅读者的身份转换:阅读教学的起点与可能的终点 / 朱建军
- 专制奴役的整体性隐喻 / 文 勇 孙绍振
- 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的定位思考 / 洪合民
- 孤独远行 卓尔不群 / 龙 健
-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实录及评点 / 余映潮 柳咏梅
- 天然去雕饰 浓情出淡语 / 张 坤 王志强
- 刘邦无赖说 / 肖 科
- 吹尽黄沙始到金 / 谭梦诗
- 谈借重《说文解字》提高汉字教学质量 / 赵乔翔 常萍萍
- 生态学视域下的作文教学策略初探 / 袁爱国
- 浮华洗尽见真淳 / 唐弋菱
- 新课标下的实践性作文教学 / 王庆林 翟启明
- “北”为何当打败仗讲? / 石 云
- 老师,你会指导写作吗? / 崔益林
- 谈谈《勾践灭吴》中三个疑难旬的翻译 / 唐家龙
- 动态命题的层递性 / 肖炎方 肖 郁
- “理论”与“实践”的合璧 / 屠锦红
- “创新”作文该休矣 / 刘思明
- 例谈文学作品中的“两个世界” / 张旺生
- 反向调节法:语文教学中心育渗透的有效途径 / 邹艳萍
- 浅谈高中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心理基础 / 冯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