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12期
ID: 147388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12期
ID: 147388
展开想象之翅 品读诗歌之境
◇ 武银华
前人在对诗歌的鉴赏实践中,总结了一个可贵的经验,即设身处地。也就是说,在诗歌鉴赏过程中,一定要发挥读者的想象力,对诗歌作品的还原度越高,意境入得越深,就越有助于鉴赏的成功。因此,对于诗歌鉴赏的读者而言,想象意识的培养以及善于发挥想象就尤为显得重要了。
虽然想象力是人类特有的秉赋,但它更依赖于后天的造就。作为一个诗歌鉴赏者,需要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通过各种途径来培养、强化自己的想象能力,从而在诗歌鉴赏中取得更大的自由,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
首先,鉴赏想象力的形成,必须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基础。
生活经验不仅仅是对文艺创作者显得重要,对于鉴赏者来说也尤为关键。在创作上,不管是言情、叙事还是摹景,都是对生活的一种艺术概括和表现,都是生活经验和生活感受的一种折射。而读者鉴赏诗歌的过程,是一种思维的“逆过程”,即通过诗歌的语言符号入手,玩味其意象,一直“逆”到作者所置身的生活情景中,从而把握作者的创作形象、创作心境与创作原动力。至于能否“逆”得进去,能“逆”得多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是否具备某方面的生活经验作为鉴赏这首诗的参照系。如果读者具备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就容易与作者建立起心理同构,也就会产生艺术共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在怎样的生活基础上创作出诗歌来,读者也就应该在相似的生活基础上才能鉴赏诗歌。下面我们围绕一个诗歌鉴赏的事例来加以说明,如唐代诗人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诗: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对于此诗,各评论家众说纷纭。如沈德潜认为“势险节短,句句用韵,三句一转”,着眼于该诗的句法变化和用韵特点。而方东树《昭昧詹言》评为“奇才奇气,风发泉涌”,是激赏其才气的卓越超群。黄香石《唐贤三昧集笺注》说:“大如斗者,尚谓之碎石,是极写风势,此见用字之诀。”他是从炼字角度说明岑诗善于夸张形容。然洪亮吉在亲历实境后对岑诗的欣赏就别有一番风味。他在《北江诗话》卷五中说:
又尝以已未冬抄,谪戍出关,祁连雪山,日在马首,又昼夜行戈壁中,沙石吓人,没及髁膝,而后知岑诗“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之奇而实确也。
正是因为洪氏有过置身于戈壁大漠之中的亲身经历,所以其他评论家的鉴赏只能是一种“案头的鉴赏”,与洪氏的鉴赏相比,不免有“纸上得来终觉浅”之感了。因此,一个缺乏生活,头脑中生活想象十分贫乏的读者,即使他具有兰心慧质、天性聪颖,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难以进入艺术想象的天地。有些读者轻视生活经验的作用,把想象看成随心所欲、全凭才气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其次,想象力的形成和发挥,必须建立审美的文化心理结构。
因为一个读者对待诗,如果不是抱着艺术欣赏的态度即审美的态度,而是以科学的、实用的眼光来衡量,那么,他在诗中看到的就仅仅是物理事实,而不是随着情感的支配、想象的扩展而形成的艺术形象。如对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我们不能用现实的尺度来衡量“三千丈”,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夸张之辞,并且在脑海中还应该想象出李太白愁情似海、白发顿生的情境。可见,要使想象的翅膀高高翱翔,就必须建立审美的心理机制。
中国是一个悠久文明的古国,在古典诗歌的文字符号和意象上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美国人看待字面的意义一般比较单纯,“一只鹰就是一只鹰”;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除了表层意义外,还往往具有深层或多层的含义。所以,阅读古典诗歌,应该对其意象的深层意义或象征意义要有所了解。只有对之有很熟稔的掌握,阅读时才能产生几乎是出于本能的、不假思索的联想。如看到“柳”的意象,就会联想到依依惜别的镜头,如柳永在《雨霖铃》中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来表达别离的伤感之情。“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的是笛声中《折杨柳》的曲子倒是传播得很远,而杨柳青青的春色却从来不曾看见,以此来表达伤春叹别的感情。“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说的是今夜听到《折杨柳》的曲子,又有何人不引起思念故乡的感情呢?又如看到“杜鹃”的字眼就会与悲苦之事联系在一起。李白《蜀道难》:“又闻子归啼夜月,愁空山。”白居易《琵琶行》:“杜鹃啼血猿哀鸣。”秦观《踏莎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文天祥《金陵驿二首》:“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杜鹃的啼叫又好像是说“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它的啼叫容易触动人们的乡愁乡思。宋代范仲淹诗云:“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再如“明月、白云”。杜甫《恨别》:“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这两句就是借白云明月寄托对友人的怀念。刘长卿《谪仙怨》:“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写别后相隔之遥与思念之深,希望悠悠的白云,把自己的一片思念之情带给千里万里之外的友人。至于对月思人就更多了。如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张九龄:“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诸如此类意象数不胜数:“松柏”象征坚贞,“梅竹”象征高洁,“幽兰”象征隐逸,“夕阳”象征晚年,“鱼雁”象征音讯往来……这种借物而达以情感的比附,开始也只是一些偶然的譬喻,后来用的多了,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思维定势,诗人们创作时是如此,读者在鉴赏时也如此。作为读者,就应该加深对古代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表现形式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发展自己的联想能力,在古典诗歌中获得更多的意蕴和美感。但我们在鉴赏中也要注意防止另一种弊端:由于某些意象的象征内涵已经相对的固定化,所以也可能在鉴赏时导致索解过深,妄生美刺;其次,象征内涵的固定化,也会使想象之翼难以多方位地飞翔,有碍于鉴赏想象的灵活性和多元化。
再次,培养鉴赏想象力,必须培养特殊的感觉能力。
这首先表现为多种感觉的共存。在想象的境界中,有声、有色、有味,这就需要听觉、视觉、嗅觉的“全面开花”。如《琵琶行》中的“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等等,几乎要读者调动全部感官的功能才能在想象中真切地把握这些形象。其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还存在一些多种感官交通,即所谓“通感”现象。如李贺《天上谣》中的“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以流水比喻流云,因为流云的形状本来就与流水相似。但作者又作进一步想象,将流水的声音挪移到流云之上,使人们感到,天上的白云不仅像溪水一样在流动,而且还发出潺潺之声。这些是视觉和听觉相互沟通的例子。再次,读诗时不能头脑过于实际,而应具有“别材别趣”的审美感受。文学作品中有些形象虽然不合情理,如唐代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句,如果质疑是否有“千里”,那么审美鉴赏的情趣和兴趣就被破坏了,就难以获得美的享受。因此,那些不能容忍虚构、想象、夸张、比兴等艺术手法所导致的与现实生活间的距离,把诗的意象直接与生活实际进行比照,就很难获得诗的审美特质。
如以上所说,想象力具有天赋的性质,但它更赖于后天的培育。读者只要参与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获得丰富的感性材料和记忆表象,以审美的心灵去观照周围的事物,将会使你的心智更加灵动活泼,使你想象的思路更加敏捷开阔,在古诗欣赏的园苑中,你将迎来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作者单位: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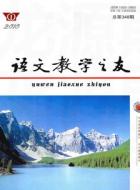
- 论语文教学内容的不确定性 / 姚永峰
- 抓住文体特征 深化审美教育 / 徐曼宇
- 优化环节,呈现语文教学的简约之美 / 谢守俊
- 浅谈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空白艺术 / 杨俊天
- 语文课堂提问的几种变式 / 于剑国
-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 王长球
- 小说教学中的美育 / 刘广生
- 语文学科属性:人文性,文化性,还是人文精神性 / 万 虹
- 《拳打镇关西》该不该从课本中拿掉 / 赵儒迎 焦玉峰
- 睫在眼前长不见 却往别处寻秋波 / 孟前进
- 痛并快乐着 / 田德荣
- 展开想象之翅 品读诗歌之境 / 武银华
- 七字诀 / 董 杰
- 语文课堂教学:繁荣背景下的喜悦与隐忧 / 卜廷才
- 杨贵妃能吃上新鲜荔枝 / 余晓容
- 浅说诗歌阅读教学的着力点 / 吴厚明
- 我看凤姐和林妹 / 韦立顺
- 平实朴实见巧思 / 汪为洪
- 吟咏之间花满蹊 / 马晓翠
- “可是,这能全怪我吗?” / 郑建华
- 在情在理 真实自然 / 吴学峰
- 也谈“夏水襄陵”之“陵”应作何解 / 杨海凤
- 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两处商榷 / 杜江伟
- 犹抱琵琶半遮面 / 杨依国 靳 杰
- 苏教版初语文言文补注三则 / 周 雷
- 《荷塘月色》:“独处”“群居”皆可自由 / 高家风
- 活用手机短信 激活作文语言 / 盛壮厚
- 爱,让她重生情感的幻想 / 胡英姿
- 蜗居.蚁居.房奴及其他 / 王安吉
- 《报任安书》中“勉励”可否译为“磨砺” / 张 华
- 《月下独酌》新解 / 陈俊江 李仁甫
- 成语误读的常见类型 / 路书体
- 由高考作文想到的几个作文教学问题 / 张建霞
- 《六国论》对议论文写作的几点启示 / 储红霞
- 网络环境下的作文互动批阅模式初探 / 柴兆科
- 颁奖辞:诗情和才气飞扬,智慧与哲思溢动 / 张永彪
- 说“军团” / 吴为民
- “阿房宫”之“房”读音探析 / 王 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