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4期
ID: 137181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4期
ID: 137181
既要“好看”,还要“好吃”,更要有“营养”
◇ 寇安炳
【摘 要】新课改以来,阅读课堂教学的最大变化,就是在“怎么教”的“理念”上有着翻新出奇、翻空出奇的“新变”。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怎么教”,却大都总是在“盲人摸象”般的热闹、“邯郸学步”般的滑稽、“东施效颦”般的蹩脚的层面上,继续着“聋子的对话”的“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迷醉痴情。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恐怕还得在“既要好看(形式恰当),还要好吃(趣味雅致),更要好营养(素养提升)”三方面,多多地讲究一番“讲究”。
【关键词】课堂教学 怎么教 形式恰当 趣味雅致 素养提升
最近听了一节所谓公开示范课,所讲课文是传统经典篇目《鸿门宴》。听课之后,老师们对这节课多有“商榷”、“疑问”之说道。可是,从教已有二十余年的这位讲课教师依然“自以为是”而且言之凿凿地自认为颇有“新意”,而且每每针对老师们就这节课上“表现”出的既悖离了传统,又荒诞了课改,更糊涂了“常识”的“教学设计”所提出的“重塑性建议”,全都给予了“那是下一节课的事”,或以“我原先早就是这样考虑的,这些我还不知道?”“我以为是亮点、新意,没想到你们却把它看作是盲点!”的“反讽”来了一通很不“心悦诚服”的回应。这种“醉死不认这壶酒钱”的“精气神”,在“新课改、新理念”已经日渐“常识化”的今天,竟然还有如此这般的“堂而皇之”、“信步悠哉”的“声口情色”,虽是其来有自,亦不免顿生“夏虫不可语冰”之慨。本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切磋砥砺与磨垢刮光的讲究,乃至于对“截伪显真”的尊崇,现谨奉呈这节课的“原生态”的“气象”,并略作反思评说,以期引起更为广泛的“惊悚性”的注意。
这位教师一上课,即“请同学们先听一首歌”。说完之后,一摁键,录音机里立即就响起了由屠洪刚倾情怒唱的《霸王别姬》。在享受了足足超过七分钟震耳欲聋的听觉冲击之后,教师随即问道:“这是谁唱的?”学生们马上张口答道:“是屠洪刚唱的。”“大家回答的对。这首歌很悲壮。歌名叫《霸王别姬》。现在我们就学一篇新课文——《鸿门宴》。”如此“高歌劲唱”地切入新课,虽非标新立异于一时,可教师确有东施效颦之嫌:一是费时太长,整个“听唱过程”耗时近八分钟。这样起兴激趣,学生也会因之“兴奋”于莫名其妙与意兴阑珊之中;二是音量过高且无画面及歌词显示,难以让学生由听歌品辞而化变为“意象景象”进而与课文的意义产生相关“链接”;三是歌曲情感基调与课文叙事情调纯属“驴嘴不对马唇”;四是“切转”新课的“拐点”太过浮浅生硬,主旨指涉不明,延展失据,难见必要的“意义”联系。如果这样安排新课导入语,或许还有可以激扬起“思考辨析”的意义张力:“这位‘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令‘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西楚霸王项羽,是在巨鹿之战中而‘一战成名’的:其诛杀宋义的义正词严、果敢坚毅,渡河救赵、破釜沉舟的决心信心,与秦军主力章邯九战大胜的英雄气胆,两千多年以来,对‘羽之神勇,千古无二’的感佩之情,依然会令人油然腾涌。可是为什么会有‘垓下之围’的慷慨悲歌呢?太史公认为: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原来的旧将,在被刘邦新拜为大将的韩信是这样评价项羽的:‘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而晋朝的阮籍‘登广武’,观看楚汉相争之地时,更是叹言鄙夷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至于苏东坡在《论项羽范增》一文中却认为:‘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凡此种种,古人的评价论说自是别具只眼,而各得旨要。现在,我们参照这几种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生发、流传至今的不同观点,走进《鸿门宴》,去打量观察、分析思考项羽、刘邦的言语行藏的‘特异’,感悟古人‘评语’的精义,体验阅读的悟会快乐。”我们知道,这首曾经广为传唱的歌曲,虽然十分激越高亢、悲怆狂放,似乎也仅仅只在彰显或吐放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时,“天地英雄”式的悲怆长叹与气贯长虹性的“自诩自信”的豪雄劲气。而这千般柔情与万丈豪情,又是直面于红颜知己虞姬不想成为自己的拖累挂碍而自刎的柔情侠骨之举,以及更因自己身处四面楚歌而无法无计无能呵护保护时的怆然悲歌。这倒让人不由得联想起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人张玉榖《古诗赏析》对其评析是:“上二,自表平素无敌,点清目下被围,顺插‘骓’字。三句承上递下。末句,收到爱姬可惜,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奈何’、‘奈若何’,真极缠绵呜咽。”其英雄末路的慨然悲叹,正如沈德潜《古诗源》的点评:“呜咽缠绵,从古英雄必非无情者。”假如以此陡起波澜,而直接课文,或许更有阐释思考的意义魅力。如果因之再联系到钱钟书《管锥编》中“……‘言语呕呕’与‘喑噁叱诧’,‘恭敬慈爱’与‘僄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阬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的这一对于我们可为之借鉴而颇有启示的评说,人物自身的矛盾性格集于一身的复杂丰富的魅力内涵,就非常值得我们去咀嚼、挖掘一通了。那么,文言文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张力,或许就更为光彩丰润了。为什么不借此做一番因果意义上的、辩证情理上的“性质对比”,却偏要别出心裁地来一番这样的与课文主题毫不搭调且又“荒腔走板”的“表演唱”?
可是,这位教师接下来的又是围绕《鸿门宴》的作者司马迁与《史记》的关系,来了一番颇为孙绍振先生在《名作细读》中所诟病讥刺的“所问肤浅,所答弱智”(实为教学识见“肤浅”所致——笔者注)的“回环往复性师生问答”。这番“费时颇长”、共三分钟的“常识预知”的内容与进程是怎样展开的呢?请看:
教师问:“课文选自哪本书?”学生答:“《史记》。”教师又问:“谁写的?”学生接答:“司马迁。”教师再问:“司马迁是哪个朝代、哪个地方的人?”学生一齐顺答:“西汉史学家、文学家,陕西韩城人。”教师说:“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人,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一通“问答”,让人确有“不厌其烦”的“莫名其妙”和“不言而喻”的“惊异”,更有不得要领的“昏庸”。而且,在学生回答之后,教师理应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断,给予指向性的“激扬”,将语文的文学教育的本真与史传文学的文化教育的风神尽量挂链结合起来。可是教师却沿着“扫盲”般的水平线,继续做着粗浅得不能再粗浅的“知识”顺延问答。真不知道学生完全可以通过手头已有的教辅参考书或“耳食”即可获取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如此煞有介事地“秀它一出”?从学生课堂回答情况来看,显然这些一连串的所谓“问答”,是多此一举的。在这里,丝毫看不出在“知识和能力”之间的生趣妙成联系,也看不出在“过程和方法”之中应有的生机生成之飘逸风情,更看不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这一所谓的“问答演进过程”中,所应张扬流泻的“生意张力”。所谓“与学生一起成长”的育养需求,竟是如此苍白、虚弱、浅薄,竟然浮浅到了如此“不知今夕何夕”的地步。当初难以理解和想象的,为什么要确立“与学生一起成长”的“理想”目标的理念,在今天看来,真不是什么海外奇谈、方外谶语。而且,就目前的情况去扫描,因为“文本”的存在,而必然要在“教什么”与“学什么”这一双向同构的价值取向层面上,活泛起有益、有味、有得、有趣的“清逸”浪花,恐怕还真的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的“愿景”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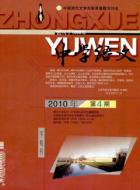
- 语文教学应由“教什么”决定“怎么教” / 李跃进 向守富
- 语文教学研究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 / 万云武
- 构建多边互动交流平台,营造有效自主学习氛围 / 张丽萍
- 浅谈语文课堂教学中各环节的衔接艺术 / 马正荣
-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中教师角色作用的思考 / 金宁静
- 善教乐学\一课一得是构筑高效课堂的根基 / 王燕飞
- 浅谈影响初中生语文听话能力的因素及对策 / 吕松和
- 来自新闻标题教学场上的收获 / 黄坚起
- 中学语文“感悟教学法”初探 / 王建明
-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之我见 / 张志顺
- 浅谈多媒体技术与语文课堂教学的整合 / 丁 伟
- 转变师生角色,强调自主学习 / 周春飞
- 充分开掘语文课本资源 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 杨建国
- 《登泰山记》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 郭庆东
- 激活高中语文课堂的方法初探 / 林西西 韦 健
- 浅析如何运用语文教学平台促进学生心理素养的提升 / 郭沁梅
- 《永远的尹雪艳》教学设计 / 李 梅
- 创设启发性的板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 吴恋燕
- 着力打造语文课堂,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 李明霞
- 《牲畜林》教学设计 / 潘昭娣
- 准.顺.情.味 / 杨 云 尹继东
- 开展语文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整体素质 / 欧阳梅 郭娟华
- 让思想的激情光芒四射 / 朱文焕
- 新课标下高中文言文有效性教学的几点尝试 / 江忠虎
- 阅读 / 佚名
- 两句诗,一个悬疑 / 戴宏华
- 让学生获得最大的发展 / 向冬云 向红梅
- 浅谈“放开式”阅读教学 / 仲乃亨
- 结庐在人境 守拙归园田 / 佚名
- 运用智慧,重新整合 / 何雪梅
- 研究性学习在农村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邵先凡
- 弦弦掩抑声声泪,诉尽平生不得志 / 徐有三
- 千年唱和 珠联璧合 / 峥嵘
- 高中古诗词中代表历史永恒的意象 / 程 娟
- 细腻深沉 情思绵邈 / 赵 伟
- 古典诗歌中“用典”手法的运用 / 闫子强
- “描”出了不幸,“比”出了愧怍 / 周树根
- 并列式议论文怎样构思更快速 / 刘绍芬
- 为古典诗歌阅读架桥 / 李丹阳
- 既要“好看”,还要“好吃”,更要有“营养” / 寇安炳
- 高中语文写作教学有效性研究 / 殷小平
- 倾听语文中的音乐 / 葛翔中 盛 丽
- 在作文教学中凸现人文教育 / 夏 薇
- 让高中生作文闪耀文化的光辉 / 卢 霞
- 古诗词教学应注意版本问题 / 汪玉龙
- 走进心灵指导学生作文 / 肖桂姣 董亚军
- 立足语文的根本 / 陈 卫 廖昌明
- 浅谈高中古典诗歌教学 / 高 峰
- 让生活走进语文课堂 / 刘凤梅
- 启迪智慧 燃烧灵感 / 陈 红
- 让语文课堂成为学生的快乐阵地 / 郭新华
-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任徘徊 / 孙 旺
- 语文学习贵在积累 / 刘思成
- 真情淌于文,作文才动人 / 况阳花
- 如何鉴赏诗歌的字词句 / 龙卫武
- 谈语文教学与素质教育 / 刘晓华
- 让学生走出“套话作文”的尝试 / 韦明书
- 下水日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 许川萍
- 联通阅读写作,提高学生素质 / 瞿云华
- 新课标背景下新材料作文写作方法探微 / 谭美平
- 利用语文资源 培养创新思维 / 马 燕
- 课堂观察 / 杨开珍
- 让作文的首尾亮起来 / 石 璟
- 让“垃圾”变为“养料” / 张 娟
- 考场议论文快速构段模式 / 邝培祥
- 新课改下如何奏响课堂语言 / 刘旭慧
- 巧比显文采,妙喻铸华章 / 柳志福
- 2010年高考语文复习备考方略 / 苏天武
- 新课程背景下名著阅读高分策略 / 黄汉宗
- 抓准文章主旨,把握文章结构 / 王艳丽 付玉秋
- 论述类文本阅读考点类析 / 卢福东
- 如何打动高考作文阅卷老师 / 徐 佳
- 题好文一半 /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