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4期
ID: 137167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4期
ID: 137167
两句诗,一个悬疑
◇ 戴宏华
【摘 要】《圆圆曲》把吴三桂和陈圆圆从初识、定情、分离、被掠到团圆,在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渲染,不过是文艺作品中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和煽动读者情绪的方法,不代表吴三桂降清的真实动机和目的。这首诗让读者解读吴三桂降清原因时如隔雾观花,乃至误将一个寡廉鲜耻的汉奸视为重情重义的情种。
【关键词】《圆圆曲》 赋比兴手法 寡廉鲜耻 重情重义
《圆圆曲》是清初诗人吴伟业(1609-1672)诗歌作品中最为有名的一篇,同时也是在清诗中享有最高声誉的七言歌行。
该诗写于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初,即作者由明入清后第八年。诗中的“圆圆”,本姓邢,名沅,字畹芬。“圆圆”乃小名,后随养母改姓陈,是明末清初苏州名妓,色艺双绝,几经辗转,为吴三桂之爱妾。诗中“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两句最为人们传颂,其中“红颜”即指陈圆圆。这两句使吴三桂成为万口争传的好色误国的汉奸,如陆次云《圆圆传》:“(吴伟业)效长恨以刺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然而,吴三桂果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为陈圆圆才开关降清的吗?吴三桂果真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的痴情的情种吗?
这就要看这首诗所写事件的历史背景了。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所部农民起义军向北京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明廷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命吴放弃宁远,火速入关勤王,安插未定,京都陷落,崇祯帝吊死在煤山(今景山),明朝覆亡了。吴三桂听到这一消息后,就把队伍撤回山海关。当时,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共有五万军队,局促于关内永平府(府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一隅,正好处于清顺两大强敌之间。继续效忠明室是不现实的,因为崇祯帝自尽,弘光朝廷尚未建立,明朝已呈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且吴与淮河以南的残明势力相距太远,彼此音讯不通。仅靠吴三桂和高第的五万军队单独对抗清或大顺的任何一方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覆灭。吴三桂才不那么傻呢。于是,剩下的道路就是投降满清,或归附大顺。
满清对吴三桂进行招降是比较早的。早在李自成攻下北京之前,清统治者就利用早已降清的洪承畴、祖太寿与吴三桂的特殊关系(洪是吴的旧上司,祖是吴的舅父),下书吴三桂。书曰:“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吴三桂后来的表现可真是“相时度势”呢)洪承畴、祖大寿和吴三桂的哥哥吴三凤、表兄弟祖可法及亲友张存仁等也先后写信劝降。吴三桂当时态度暧昧,犹豫未决。
然而明亡之时,大顺政权一派唐通招降,吴三桂就很快决定接受招降。这主要是因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早已投降李自成农民军,吴三桂的家室和大量财产也在北京,明朝的文武官吏投降大顺政权的亦有三千人,大顺政权颇有一统天下之势。另外,大顺政权毕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吴三桂等辽东官兵长期与清方对峙,与大顺军没有多少恩怨。于是吴三桂“相时度势”,“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
到了1644年3月22日,吴三桂在永平府张贴文告,有“本镇率所部召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随即领兵向北京进发。3月26日前后,行到河北玉田县,离北京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带领部下直奔山海关,打败守关的唐通,占领山海关,准备降清。
吴三桂变卦的原因,据《甲申纪事》所载:
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言君父之仇,必以死报。
引文中“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是指李自成农民军追赃索饷。针对当时现实矛盾,李自成农民军提出了“均田免粮”、“三年不征,一民不杀”、“霸占土地,查还小民”的政策。农民军的军饷以及大顺政权的日常开支,便只能从官僚、地主那里取得。但由于刑罚太重,打击面太大,没有区分首恶、从恶,策略上失当,导致许多后患,吴襄案即属此类。对吴襄下手太重引起吴三桂的不满。吴三桂归附大顺本不是为革命而是为保家护产,可农民军策略上的失当,使吴三桂产生“归降大顺家破人亡,不降大顺也许能活”的想法。加之,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又被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所占有。(见《清史稿·吴三桂传》)如《圆圆曲》中所说:“相约思深相见难,一朝义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可以说,追赃索饷是使吴三桂理智上作出叛顺降清的选择的原因;圆圆被虏则是吴三桂叛顺降清的感情上的激发点。与大顺政权相比,清廷劝降在先,并许以高官厚禄;吴之从亲友又在清廷效力。——“相时度势”后,吴三桂不投降清廷才怪呢!撇开陈圆圆不说,即使陈圆圆在北京没有受到任何骚扰,有以上几点,吴三桂在深思熟虑后也会转投清廷的怀抱。这完全是由吴三桂的思维逻辑决定的,他可不是什么痴情儿女,他心中也没有什么忠君爱民的绳索。吴三桂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他的一己之私而展开的。不信,请看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吴三桂。
清廷在北京安定下来以后,加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留镇云南。吴三桂便把云南作为他的私人王国,“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逆臣传》卷上,《吴三桂列传》),“用人,吏兵工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刘键:《庭闻录》卷四),甚至还向全国各地安插自己的亲信,称为“西选”,一时出现了“西选之官满天下”(《明季稗史汇编》卷十)。同时,把明朝黔国公沐氏的田计七百顷全部占为己有,又圈已经归各族农民所有的卫所军田,把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变成他的官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杂税赋役,强迫农民纳租再纳租,其部下更是为虎作伥,“杀人夺货,无所畏忌”(刘键:《庭闻录》,卷四),“百姓苦疲难堪”(清《圣祖实录》卷二)。此外,庞大的军费开支(三藩总兵力十万余人,其中吴三桂有兵力六万余人),全由国库支付,造成“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魏源《圣武帝》卷二),给清政府以很大的压力。康熙帝因此打算撤藩。然而,吴三桂岂会自动放弃他的土皇帝生活?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故伎重演,公开叛乱反清。他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扯起“复明”旗号。三十年前,他开关放敌时没想到“复明”;他做平西王,伺候清廷近三十年,他也没想到“复明”;待到“撤藩”了,他立即“复明”了,这不是扯淡吗?再看,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初一,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称帝,国号周,建元昭武。八月十七日,吴三桂病死。这是复的哪门子的“明”?
综观吴三桂的一生,有三变:一变“弃明降顺”,为的是保家产;二变“背顺投清”,为的是保前途;三变“叛清自立”,为的是保其独断专权和奢糜的生活。从未有哪一变事关忠义、廉耻、道德,更不用说民生了。因此,即使没有陈圆圆,吴三桂也会有此三变,这是由他自私的本质所决定的,吴三桂可不是什么痴情儿女,在吴三桂眼里,妻子从来就无关大计,他最后一变就是在没有人抢他的陈圆圆而是抢他的特权下完成的。不要再说寡廉鲜耻的吴三桂是多情的“种子”了,与其说“冲冠一怒为红颜”,倒不如说他“冲冠一怒为红钱”。这里的“红”指的是“红顶”。
所以,《圆圆曲》把吴三桂和陈圆圆从初识、定情、分离、被掠到团圆,在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渲染,不过是文艺作品中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和煽动读者情绪的方法,不代表吴三桂降清的真实动机和目的。当然,在这中间也有一个严肃的主题贯穿于全诗,即入清的故明士大夫对吴三桂深怀愤激与讽刺,并由此曲折表达故国之思。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诗让读者解读吴三桂降清原因时如隔雾观花,乃至误将一个寡廉鲜耻的汉奸视为重情重义的情种。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兴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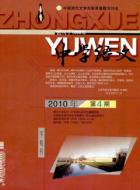
- 语文教学应由“教什么”决定“怎么教” / 李跃进 向守富
- 语文教学研究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 / 万云武
- 构建多边互动交流平台,营造有效自主学习氛围 / 张丽萍
- 浅谈语文课堂教学中各环节的衔接艺术 / 马正荣
-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中教师角色作用的思考 / 金宁静
- 善教乐学\一课一得是构筑高效课堂的根基 / 王燕飞
- 浅谈影响初中生语文听话能力的因素及对策 / 吕松和
- 来自新闻标题教学场上的收获 / 黄坚起
- 中学语文“感悟教学法”初探 / 王建明
-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之我见 / 张志顺
- 浅谈多媒体技术与语文课堂教学的整合 / 丁 伟
- 转变师生角色,强调自主学习 / 周春飞
- 充分开掘语文课本资源 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 杨建国
- 《登泰山记》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 郭庆东
- 激活高中语文课堂的方法初探 / 林西西 韦 健
- 浅析如何运用语文教学平台促进学生心理素养的提升 / 郭沁梅
- 《永远的尹雪艳》教学设计 / 李 梅
- 创设启发性的板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 吴恋燕
- 着力打造语文课堂,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 李明霞
- 《牲畜林》教学设计 / 潘昭娣
- 准.顺.情.味 / 杨 云 尹继东
- 开展语文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整体素质 / 欧阳梅 郭娟华
- 让思想的激情光芒四射 / 朱文焕
- 新课标下高中文言文有效性教学的几点尝试 / 江忠虎
- 阅读 / 佚名
- 两句诗,一个悬疑 / 戴宏华
- 让学生获得最大的发展 / 向冬云 向红梅
- 浅谈“放开式”阅读教学 / 仲乃亨
- 结庐在人境 守拙归园田 / 佚名
- 运用智慧,重新整合 / 何雪梅
- 研究性学习在农村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邵先凡
- 弦弦掩抑声声泪,诉尽平生不得志 / 徐有三
- 千年唱和 珠联璧合 / 峥嵘
- 高中古诗词中代表历史永恒的意象 / 程 娟
- 细腻深沉 情思绵邈 / 赵 伟
- 古典诗歌中“用典”手法的运用 / 闫子强
- “描”出了不幸,“比”出了愧怍 / 周树根
- 并列式议论文怎样构思更快速 / 刘绍芬
- 为古典诗歌阅读架桥 / 李丹阳
- 既要“好看”,还要“好吃”,更要有“营养” / 寇安炳
- 高中语文写作教学有效性研究 / 殷小平
- 倾听语文中的音乐 / 葛翔中 盛 丽
- 在作文教学中凸现人文教育 / 夏 薇
- 让高中生作文闪耀文化的光辉 / 卢 霞
- 古诗词教学应注意版本问题 / 汪玉龙
- 走进心灵指导学生作文 / 肖桂姣 董亚军
- 立足语文的根本 / 陈 卫 廖昌明
- 浅谈高中古典诗歌教学 / 高 峰
- 让生活走进语文课堂 / 刘凤梅
- 启迪智慧 燃烧灵感 / 陈 红
- 让语文课堂成为学生的快乐阵地 / 郭新华
-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任徘徊 / 孙 旺
- 语文学习贵在积累 / 刘思成
- 真情淌于文,作文才动人 / 况阳花
- 如何鉴赏诗歌的字词句 / 龙卫武
- 谈语文教学与素质教育 / 刘晓华
- 让学生走出“套话作文”的尝试 / 韦明书
- 下水日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 许川萍
- 联通阅读写作,提高学生素质 / 瞿云华
- 新课标背景下新材料作文写作方法探微 / 谭美平
- 利用语文资源 培养创新思维 / 马 燕
- 课堂观察 / 杨开珍
- 让作文的首尾亮起来 / 石 璟
- 让“垃圾”变为“养料” / 张 娟
- 考场议论文快速构段模式 / 邝培祥
- 新课改下如何奏响课堂语言 / 刘旭慧
- 巧比显文采,妙喻铸华章 / 柳志福
- 2010年高考语文复习备考方略 / 苏天武
- 新课程背景下名著阅读高分策略 / 黄汉宗
- 抓准文章主旨,把握文章结构 / 王艳丽 付玉秋
- 论述类文本阅读考点类析 / 卢福东
- 如何打动高考作文阅卷老师 / 徐 佳
- 题好文一半 /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