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3期
ID: 147859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3期
ID: 147859
孤独的清醒者
◇ 刘婧芳
摘要:庄子、《沉沦》主人公,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同样喜欢在大自然中品味孤独,拥有自身的想象世界;他们同样身处乱世却都有着脱于俗世的心态,他们对现实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他们对生死的看法却不同,也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路:庄子选择了“游戏人间”,《沉沦》主人公却选择了投海自尽。
关键词:孤独清醒生死
一个是战国中期人,一个是二十世纪初的人。然而时间的长河却没有阻隔二人共同的精神气质,他们同样喜欢徜徉在孤独的海洋中,他们同样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有着他人无法体会的看法和认识,然而他们又是不同的,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庄子和《沉沦》中的主人公“他”。
一、孤独者
庄子的孤独主要表现在他具有独立人格,或者说是一种孤傲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庄子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算什么,根本不值得他正视它!如《庄子评传》中所言:“这‘心不屑与之俱’就是对世事有意识的轻蔑,并在轻蔑中品味骄傲的孤独。”[1](P160)另一方面,庄子品味孤独是一种回归自然,是一种壮阔的想象,也是一种精神的遨游。
庄子的孤傲态度在《庄子》许多篇幅中都有体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龜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途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途中。’”[2](P474)然而庄子家里实为贫困,甚至穷到借粮的地步。但是从上述例子也可以看出庄子名声很大且为政治人物所看重,他改变贫困状态实属简单之事,然而他的清高孤傲却让他继续着他的贫困生活。
另外,“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户闾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癕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百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2](P891)可见孤傲的言语和与众不同的认识也是其孤独的体现。所以不得不说庄子的孤独与他的傲气是透彻的,看看先秦诸子中,有谁如庄子这般藐视一切,又有谁可以如庄子这般敢于对帝王说“不!”。庄子让自炫的曹商丢尽面子,庄子不给楚王面子……或许就如冯伟林所说的那样,“超越是一种孤独,世俗庸众不配孤独”[3]。而我们的庄子已经超越了。
庄子孤独着,主要体现在他回归自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并非简单指自然物或自然界,而是指本性、本然,或者说是“真”。《庄子·渔父》云:“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曷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2](P868)在庄子看来天人应该是合一的,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庄子有了“逍遥游”这种品味孤独的快乐。庄子的逍遥游是一种精神畅游,会带着我们进入一个幻想且奇特的领域。蒙培元也指出:“所谓‘逍遥’,就是摆脱一切主观与客观的限制和束缚,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4](P22)亦如陈鼓应所言,“《逍遥游》提供了一个心灵世界,一个广阔无边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一个精神空间,一个辽阔无比的精神空间。人,可以在现实存在上,开拓一个修养境界,开出一个精神生活领域,在这领域中,打通内作重重的隔阂,突破现实种种的限制网,使精神由大解放而得到大自由。”[4](P23)如《逍遥游》开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2](P5)同篇还有如“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2](P25)这些都是庄子带给我们的想象,且在同篇中继续带领着我们环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2](P90)不仅《逍遥游》带领我们进入想象的世界,《齐物论》中“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况利害之端乎!”[2](P601)《应帝王》篇“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这些展现的也都是一种超脱世外的环境,带给我们无边的想象空间。
《沉沦》是郁达夫的代表作品,小说主人公“他”,是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他渴望着爱情,渴望着自由,然而他是孤独的。“他”出生在富春江边的一个小市,三岁丧父,家中贫困,小学毕业后又多次转换中学,后来便干脆不进中学了,蛰居在家读书、创作。之后随长兄到日本,在日本读书,最终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成仿吾曾说过《沉沦》主人公“对于爱的缺乏是最灵敏的,孤独的一生与枯槁的生活,也使爱的缺乏异常明显,也使他对爱的要求异常强烈。”[5]《沉沦》开篇就点明了“他”的孤独,“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6](P16),他的孤独正如他所言,“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天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要难受”。[6](P21)所以他喜欢把自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中,来品味孤独。“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尾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6](P16)环境是清和的,是寂静的,他一个人欣赏着周边的一切,在这静静的大平原上他陪同他的孤独一起精神畅游。
每当他独自在这大自然中品味时,他往往会进入一种幻境,进入他自身的乌托邦:“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巷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6](P17)这样的状况如同庄子“逍遥游”那里在自己的世界中获得快乐的感受,尽管那是孤独的。
他内心十分明白自己是孤独的,但自己并不害怕孤独。当他租房子的时候,房主人担心他因为寂寞呆不久时,他说:“我可同别人不同,你但能租给我,我是不怕冷静的。”[6](P40)也正因为他是了解自己的,所以他会故作冷漠,“向四边一看,太阳已经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饱受了一天残照,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岚气,反射出一种紫不紫红不红的颜色来。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喀的咳嗽了一声,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装改了一幅忧郁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6](P20)他喜欢孤独,内心里面已经认定了自己的欢乐,自己的笑容是同自己的品味孤独联系在一起的,他容不下别人打破他的这种欣赏孤独的境界。
二、清醒者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一切旧制度旧势力正在为新的制度新的力量所取代。正是在这样的乱世,名利的诱惑尤为凸显,思想家们十分活跃,各色策士穿梭各个国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下,庄子依然做到了“不为物役”。庄子还打比方,把拼命追逐外物的人们比喻成猪身上的虱子,说这些人找到点蹄边胯下猪毛疏长的地方就以为自己得到了大的宫苑。《齐物论》中一段话可以说是总结性地说明人生受外物所困是悲哀的: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荧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乱世中的庄子是个清醒者,而同样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沉沦》主人公“他”,也是个清醒者。他在异国他乡留学,那些日本人,都把他看做是“支那人”,不把他看做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平等对待,在根本上歧视他、蔑视他。这种歧视给他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的孤独感和这种精神压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深感弱国子民所背负的痛苦,他内心深处渴望着祖国的强大,小说中也常会反映出他的这种呼唤: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另外,也可以说他选择的孤独也是他清醒的一个表现,他的祖国贫穷和落后,使他无法实现他的理想和愿望,反而受到排挤,他甚至被看成是精神病,这样就把他逼着走向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去追求他的自由和解放,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才可以想自己所想,不必为俗世所累,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是快乐的。他的这种逃避现实,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抗,从中可以听见他强烈的个性解放的呼声!而他选择死亡,选择了放弃这个世界也是一种抗争,一种悲壮而无奈的反抗。
三、不同的人生选择
王博教授在《无奈与逍遥——庄子的心灵世界》中说过,“在庄子看来,人生也许是悲剧,这么说可能重了一点,但是绝对不是喜剧,不是一个肥皂剧。人生是一大无奈,一大不得意,这就是庄子给我们的东西。”[7](P93)所以庄子抗拒了外物对他的召唤,躲开了世间的利诱,选择了“游世”,这是他与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他充分利用着他的“无用”思想来思考着生活。在庄子看来要学会在尘世夹缝中生存,就要做到不为功利,不为权势所动;就要回避矛盾,不触碰争执的浪尖;就要隐藏思想情欲,不患得患失,总之是要保持自然天性。
《沉沦》主人公“他”,渴望自由,具有打破桎梏的精神,然而他又为传统文化所束缚,渐渐地与世格格不入,最终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路,他宁愿自己死亡也不愿沉入这浑浊得透不过气的世界里,于是伴随着渴望祖国强大的呼唤投入了大海。
注释:
[1]颜世安:《庄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3]杨济舟:《千年孤独看月人——庄子墓前的沉思》,山东文学,2009年,第S3期,第282—283页。
[4]席格:《与天地精神往来——论庄子美学时空观及其视域中的逍遥游》,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第20—24页。
[5]梁吉:《苦闷的岁月——对郁达夫小说<沉沦>主题的探讨及其他》,名作欣赏·现代回眸,2006年,第2期,第40—44页。
[6]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2页。
[7]王博:《无奈与逍遥——庄子的心灵世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刘婧芳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400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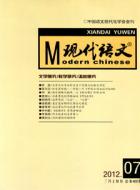
- 两汉纪行赋纪实性风格初探 / 韩佩佩
- 陶渊明田园诗中的理想与现实 / 黄三平
- 浅谈“清谈”误国论 / 游琦
- 论唐代贬谪诗歌中的巴渝 / 李毅 张华清
-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赏析 / 杜中伟
- 伪喜的生存,孤独的灵魂 / 梅海江
- 《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 赵风杰
- 对“有余力,则学文”的新解读 / 路炳明
-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之探究 / 梁新荣
- 是瞒天奇谋,抑催命拙计? / 郭曼
- 论《九歌》的性质 / 刘瑞学
- 论秋瑾的咏植物诗 / 黄剑光
- 沿着鲁迅的思路细读《阿Q正传》 / 聂国心
- 试论鲁迅作品的童年世界 / 唐军军
- 打不败的硬汉:海明威小说中的斗牛士形象 / 陈霄
- “辣”——强势女人的必备武器 / 马雪萍
- 在路上 / 万春怡
- 一曲健康优美“人生形式”的牧歌 / 王永章
- 虚幻的洁净和现实的肮脏 / 孙彦萍
- 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本质观的再认识 / 白淑杰
- 试分析《伤逝》中的婚恋悲剧 / 潘万里 王艳
- 此中有真意,“微笑”更“落泪” / 钟伟建
- “过失”的产生 / 李程
- 珠散意联 情牵一线 / 王军文
- 作为他者的吉普赛人 / 李昌燕
- 奏响生命之歌 / 李婷
- 文学文体学分析方法下的颜元叔散文研究 / 陈丽 夏家楠
- 常理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 李胜志
- 跨越世俗\时空的真爱 / 路王娟
- 物犹如此 / 张潇萌
- 知音其难哉 / 袁贝贝
- 孤独的清醒者 / 刘婧芳
- 由《荷塘月色》中“妻子”这一形象想到的 / 刘忠伟
- 浅谈职校生语文教学中口语交际能力的评价与培养 / 王珠云
- 新课程下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误区及应对 / 顾文琦
- 以文本为支点 提高阅读能力 / 钟脆鸣
- 浅议中职语文课堂教学目标设计现状 / 程祖芳
- 浅析古诗词“六步鉴赏法” / 陈志刚
- 谈积极情感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 李洪华
- 五年制高职语文实用能力训练题设计的思考 / 马原
- 激发兴趣学古诗 / 朱敬允
- 对初中名著导读教学的几点思考 / 马建军
- 从现代心理角度审视高中作文教学的困境 / 刘卫平
- 开发生活资源,丰富写作素材 / 黄慧齐
- 语文课堂审美原则初探 / 苏税华
- 小活动,立大功 / 王维升
- 点亮学生理性智慧 / 习萍
- 影子跟读法在日语教学中的作用 / 冯淳
- 一块新奇而充满挑战的跳板 / 董秀琴
- 初中语文对比教学探微 / 陈元芬
- 竞赛式教学法引入中职语文课堂的尝试 / 钟巧玲
- 放飞心灵 感受生命 / 王艳敏
- 语文课堂,缺失了什么? / 苟昌革 崔志钢
- 《歧路灯》詈骂语略谈 / 申利歌
- 概念整合理论对网络生僻字的认知分析 / 干敏
- 语言接触与翻译:以《国际歌》汉译为例 / 邓科
- 网络汉字词的造词研究 / 岳艳红
- 大陆台湾英译汉四字格对比研究 / 刘唯一
- “打”字的字形和语音问题 / 罗晓春
- 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 / 王丽滨 曹晨光
-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再读《论语》 / 邓颖平
- 诗歌朗诵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 王静
- 汉民族意象思维及其流失 / 高璇
- 谈单用的“之后”\“之前” / 胡晓萍
- 抬杠言语行为的语用分析 / 马若宏
- “绿色”的词义扩大和语义组合问题 / 李华云 连辉
- 闻喜方言与婚俗文化 / 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