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3期
ID: 147850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3期
ID: 147850
“过失”的产生
◇ 李程
摘要:在《诗学》中,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冲突的本质是过失,而非希腊传统观念中的命运。但是对于“过失说”,尤其是对于过失的根源,亚里斯多德并未进行详细的阐述,只是表明悲剧的源起在人而不在天。本文在此将就“过失”的根源进行追问,探索悲剧“过失”这一重要的诗学命题。
关键词:过失中庸普遍特殊
《诗学》是对西方文论与美学影响至为深远的一部著作。在此书中,亚里斯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悲剧冲突的“过失”说,认为悲剧冲突的本质在于好人的过失,由于好人犯了错误,因而导致了矛盾冲突,使其个体自身以及与其相关的人陷入不可克服的生存悖谬,从而导致悲惨的结局。希腊悲剧中的错误有两种:一种是明知故犯,如悲剧《美狄亚》中的主人公美狄亚为了对丈夫伊阿宋进行报复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另一种是在不知不觉中犯错,如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亚里斯多德不赞成欧里庇得斯对美狄亚的写法,而认可索福克勒斯对俄狄浦斯的写法。具有优良品质的个体在不自知的境况下陷入罪恶的渊薮,这才是好人犯错,才能引起怜悯和同情,因此本文只对不知而误犯的过失进行阐释。
一、人本主义的诗学命题
在希腊传统观念中,命运占有极为重要地位,连诸神都要在命运的面前低下高傲的头颅。在希腊人眼中,命运的根源是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命运的力量是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在命运的引领下向着某个既定的目标前进,个体的在世性情在命运的车轮的碾压下,只能发出痛苦而微弱的呻吟。罗素曾说:“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感情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祗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运命对于整个希腊思想起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这也许就是科学之所以能得出对于自然律的信仰的渊源之一。”[1](P33-34)在古希腊人的精神观念中,个体生命的幸与不幸,欢乐与苦痛,乃至整个人生轨迹都是神秘命运安排、框定的,个体的自由伦理必然服从于天命伦理。但亚里斯多德并不这样认为,他从科学的视角来思考文艺,认为一切悲剧的发生都有其人为的合理性,“亚里斯多德要求一切合理,在《诗学》里从来不提及希腊人所常提的‘命运’二字,并且明白地谴责希腊戏剧所常用的‘机械降神’即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就请神来解决的办法。”[2](P85)与此相应,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与命运观相悖的“过失说”:“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声名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家庭的著名人物。”[3](P39)
由此观之,过失并非来自超验运数的摆布,邪恶神谕的命定,并非是一种我们不可把握而又将我们推向某种必然的形而上存在,一切都是偶然,即使太阳升起在过去的无数个晨曦中,仍然无法保证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神会来拯救我们。当然亚里斯多德并非无神论者(关于亚里斯多德思想的矛盾性,本文无力论及),但是在《诗学》中,他绝口不提命运,并且反对“机械降神”。既然没有一个超验的存在来规定个体生存的轨迹,陷我们于疾痛惨怛的境地,也没有这样一个存在来拯救我们免于灾祸,承负我们的罪恶,那一切的错误,一切的承负的指归都在人自身。
悲剧主人公的错更多的是不知实情而犯错,是在事实真相被遮蔽,在自以为看清了世事的经纬而实际却是盲目的状态下犯错,我们称之为无辜犯错。没有犯错的动机,而最终却陷自己并陷他者于生命的被撕裂状态,这是内在的无罪而外在的有罪。在内心的意向中,我们要实现的是合乎情理的愿望,而在外部现实中,我们却遭遇了价值的毁灭,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面对生存的残酷,渺小的生命个体只好去问天问地。而亚里斯多德认为这些过失都在于人自身,而这种悲剧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因为没有上天,没有运数的回应,我们只能返回自身。正如李泽厚所言:“人必须在自己的旅途中去建立依归、信仰,去设定‘天行健’,并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任何外在的拯救、希冀和寄托,因此其内心之悲苦艰辛、经营惨淡、精神负担便更沉重于具有人格神的精神文化。”[4](P23)
虽然亚里斯多德并非无神论者,但在《诗学》中却表现出很强的人本主义精神,这种人本主义诗学,将悲剧的过失归于个体生命自身,那么我们到底错在何处呢?
二、从《伦理学》看“过失说”
悲剧的本质冲突是好人犯错误,悲剧人物是好人,但不是完人,他“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所以犯了错误。然而他的个体性情又是善良的,是“比一般人好的人”,是与我们相似的人,惟其如此,当他遭遇了生命的破碎时,才能引起旁观者的怜悯与同情。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错误的缘由是生命自体自根的品质缺陷而不是命运的必然性,那么这品质的缺陷到底是什么?
亚里斯多德对悲剧的看法与他的道德观有关,也与他对人的看法有关。在《伦理学》中,亚里斯多德提出的重要观点即中庸之道:“每种德行都是两个极端的中间之道,而每个极端都是一种罪恶。这一点可以由考察各种不同的德行而得到证明。勇敢是懦怯与莽撞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荡与猥琐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耻与无耻之间的中道。”[5](P226)
俄狄浦斯的极端在于他极端的审慎与极端的激情。在一个人身上拥有这两种相悖的品质并不难理解,如著名学者熊十力,如果他没有极为理智的审慎,就不能写出深奥的哲学著作;同时,在生活中他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但亚里斯多德认为德行应是一种避免极端的中庸之道,任何一种极端都将导致灾祸。如此,我们来看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因为具有极端的审慎与理智,所以对神谕极为敏感,害怕弑父娶母,因而逃离科任托斯,但科任托斯的国王与王后并非俄狄浦斯的生身父母。而当他在岔路口遇到拉伊俄斯时,又因为一时激愤,将其杀死,这显然是不审慎的表现。对于审慎与热情,罗素写道:“人类中最伟大的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会没有趣味;有了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是危险的。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全部历史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应完全偏袒任何一方。”[6](P39)而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只有介于两种极端中的中庸之道才是德性,显然我们需要以必要的理智来约束激情,但并不意味着要以中庸之道来作为我们行动的准则,激情的迸发也可以带来创造性成果,如在艺术家的工作中,只是这种激情并未完全丧失理智,并且是在正确的场合中。我们应当尽可能享受激情带来的愉悦的生存体验,而避免陷于激情带来的毁灭的漩涡。
三、从“相论”看“过失说”
古希腊人的理性智慧高度发达,并且引以为傲。他们往往醉心于寻求事物的共性,而忽视了事物的个性,以至于最终发展出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的理念是超越于具体事物之上的,它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自足。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知识、智慧是属于超越特殊事物的永恒世界的,如,意见涉及的是个别的美的事物,而知识则涉及美的自身的世界。而追求这种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做一个“洞见真理”的人正是许多哲人呕心沥血的目标。但此种普遍的知识果真足以使我们在处理现实事件时左右逢源而不致犯错吗?
俄狄浦斯显然是有智慧的,他很快就破解了斯芬克斯的谜语。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这正是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的表征。这是所有人的共性,毋宁说,俄狄浦斯认识了某种人的共性,得到了知识。但他却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世,没有认清自己的父母,从而犯下了弑父娶母的深重罪恶。俄狄浦斯的过失在于认识了共相的人,却没有认识殊相的人,而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共相是不能脱离殊相而存在的。亚里斯多德说:“任何一个共相的名词要成为一个实体的名词,似乎都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每个事物的实体都是它所特有的东西,并且不属于任何别的事物;但是共相则是共同的,因为叫做共相的正是那种能属于一个以上事物的东西”。 [7](P213)总而言之,共相不能独立自存,而只能存在于特殊的事物中,即普遍寓于特殊之中,而我们又要从特殊中抽象出普遍的规律。单纯的演绎或归纳都不是科学的方法。而大部分的古希腊哲人热衷于寻找普遍的知识,俄狄浦斯正是这样一个哲人王。他高度的智慧可以理析出人的共性,但是却忽视了人的复杂性。而每一个人都包含了巨大的存在丰富性,情感的丰富性,思想的丰富性,伦理关系的丰富性,生命经历的丰富性等等。尊重个体生命的丰富性,重视每个人的特殊性,这似乎是一些善于形而上思考的哲人所缺乏的品质。认清自我及他者的品质,在世的伦理坐标,生命的情感偏好,这些才是真正的认识人,认识自己,而不仅仅是摭拾一个抽象的普遍概念,编织一个可以网罗一切个体的话语经纬。探寻个体生命渊深的黑暗罅隙,认识每个生命的独特的生存情状,把握“这个”之所以不同于“那个”的特殊性,如此才可在幽微曲折的人生峡谷中顺利行舟,而不至于犯下俄狄浦斯式的错误。
找到了悲剧个体自身的缺失,也就为我们避免悲剧的重演开启了希望的户牖,正如荷尔德林所歌唱的:“但哪里有危险,那里也生拯救”。[8](P21)既然好人的犯错并非由于命运的必然性,既然外在世界充满了偶然性,既然犯错是因生命自身的品质欠缺所致,那么个体便有希望调整自身的在世性情、感觉偏好、认知结构来避免过失。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提出了与命运观截然不同的悲剧“过失说”。这种“过失说”将悲剧冲突的本质归咎于人自身。而过失的根源也是人自身的情感失调及认知缺陷,这种诗学理论显示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重视,体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特色,值得我们反复涵咏,体会其微言大义。
注释:
[1][5][6][7]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34页,第226页,第39页,第223页。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
[3]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诗学·诗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4]李泽厚:《论语今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8]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亚里斯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李程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050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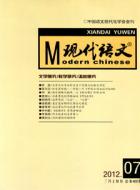
- 两汉纪行赋纪实性风格初探 / 韩佩佩
- 陶渊明田园诗中的理想与现实 / 黄三平
- 浅谈“清谈”误国论 / 游琦
- 论唐代贬谪诗歌中的巴渝 / 李毅 张华清
-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赏析 / 杜中伟
- 伪喜的生存,孤独的灵魂 / 梅海江
- 《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 赵风杰
- 对“有余力,则学文”的新解读 / 路炳明
-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之探究 / 梁新荣
- 是瞒天奇谋,抑催命拙计? / 郭曼
- 论《九歌》的性质 / 刘瑞学
- 论秋瑾的咏植物诗 / 黄剑光
- 沿着鲁迅的思路细读《阿Q正传》 / 聂国心
- 试论鲁迅作品的童年世界 / 唐军军
- 打不败的硬汉:海明威小说中的斗牛士形象 / 陈霄
- “辣”——强势女人的必备武器 / 马雪萍
- 在路上 / 万春怡
- 一曲健康优美“人生形式”的牧歌 / 王永章
- 虚幻的洁净和现实的肮脏 / 孙彦萍
- 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本质观的再认识 / 白淑杰
- 试分析《伤逝》中的婚恋悲剧 / 潘万里 王艳
- 此中有真意,“微笑”更“落泪” / 钟伟建
- “过失”的产生 / 李程
- 珠散意联 情牵一线 / 王军文
- 作为他者的吉普赛人 / 李昌燕
- 奏响生命之歌 / 李婷
- 文学文体学分析方法下的颜元叔散文研究 / 陈丽 夏家楠
- 常理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 李胜志
- 跨越世俗\时空的真爱 / 路王娟
- 物犹如此 / 张潇萌
- 知音其难哉 / 袁贝贝
- 孤独的清醒者 / 刘婧芳
- 由《荷塘月色》中“妻子”这一形象想到的 / 刘忠伟
- 浅谈职校生语文教学中口语交际能力的评价与培养 / 王珠云
- 新课程下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误区及应对 / 顾文琦
- 以文本为支点 提高阅读能力 / 钟脆鸣
- 浅议中职语文课堂教学目标设计现状 / 程祖芳
- 浅析古诗词“六步鉴赏法” / 陈志刚
- 谈积极情感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 李洪华
- 五年制高职语文实用能力训练题设计的思考 / 马原
- 激发兴趣学古诗 / 朱敬允
- 对初中名著导读教学的几点思考 / 马建军
- 从现代心理角度审视高中作文教学的困境 / 刘卫平
- 开发生活资源,丰富写作素材 / 黄慧齐
- 语文课堂审美原则初探 / 苏税华
- 小活动,立大功 / 王维升
- 点亮学生理性智慧 / 习萍
- 影子跟读法在日语教学中的作用 / 冯淳
- 一块新奇而充满挑战的跳板 / 董秀琴
- 初中语文对比教学探微 / 陈元芬
- 竞赛式教学法引入中职语文课堂的尝试 / 钟巧玲
- 放飞心灵 感受生命 / 王艳敏
- 语文课堂,缺失了什么? / 苟昌革 崔志钢
- 《歧路灯》詈骂语略谈 / 申利歌
- 概念整合理论对网络生僻字的认知分析 / 干敏
- 语言接触与翻译:以《国际歌》汉译为例 / 邓科
- 网络汉字词的造词研究 / 岳艳红
- 大陆台湾英译汉四字格对比研究 / 刘唯一
- “打”字的字形和语音问题 / 罗晓春
- 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 / 王丽滨 曹晨光
-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再读《论语》 / 邓颖平
- 诗歌朗诵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 王静
- 汉民族意象思维及其流失 / 高璇
- 谈单用的“之后”\“之前” / 胡晓萍
- 抬杠言语行为的语用分析 / 马若宏
- “绿色”的词义扩大和语义组合问题 / 李华云 连辉
- 闻喜方言与婚俗文化 / 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