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3期
ID: 147844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3期
ID: 147844
在路上
◇ 万春怡
摘要:冯至曾深受克尔凯郭尔与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其代表作《十四行集》中有着明显的表现。本文运用以上两位哲学家的基本思想,浅析了《十四行集》中的相关诗歌,表明了《十四行集》与克尔凯郭尔与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思想在精神上息息相通,并揭示出人生存的旨归所在。
关键词:《十四行集》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
冯至《十四行集》的精神与存在主义关注人现实的“生存性”息息相通。冯至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受其开创者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影响最大。关于冯至受此二位哲学家的影响,学界已多有论证,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在此欲用“在路上”来概括《十四行集》,因为,这二十七首十四行体诗,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冯至对于生命过程的重视和领悟。他曾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多多经历,多多体验,为人的可贵在乎多多分担同时同地人们的苦乐。”克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他主张“真正重要的是选择的行为本身,而非选择什么”,“使个体永远地走在通往‘真理’的路途上,去不断地‘接近’‘真理’”。雅斯贝尔斯关注的同样是现世“生存”的本身,他强调的是行为或者说生活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他认为,生命意义即产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我们仿佛看到一位踽踽独行于道路上的旅人,他永远“在路上”,在路上,也就是其旅途的全部意义所在,也许有终结,却没有最终的目的地。雅斯贝尔斯作为一名存在主义的继承者,继承了克尔凯郭尔“在路上”的关注现世生存性的哲学思想,同时,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人固然要做出选择,人永远在路上,然而,“在路上”这一单纯的过程,同样会对人造成限制,封闭人生,因此,人还要在路上有所发展,不断吸收,进行超越,这样的生存才是有意义的无限的生存。冯至的《十四行集》是对二者的吸收与兼容,它既强调了人生的意义在于体验,要时时刻刻“在路上”,也具有丰富的入世思想,要求人不仅要“在路上”,还要有所为。这一兼容的思想,构成了冯至《十四行集》中的“在路上”的思想。
一、对现实的把握,对过程的体验
生命的价值在于存在过程:感受、体验并领悟。这是克尔凯郭尔与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也浸润在《十四行集》中。作者甚至赞颂那些生命短暂的小飞虫,因为在它们短短的一生中,其生命过程已足够美妙,或完成了繁衍的天职,或勇敢抵抗了一次灾难。
第十五、十六和十七首诗歌,直接以路作为诗歌的意象,明显地体现了“在路上”的哲学思想。“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这些经历的印记,这些经历,也成为了人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如同一卷长长的胶带,一幕幕已印于生命的底板上,只要它们出现过,便有价值,便是意义,是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克尔凯郭尔在《附言》一书中说:“生存就是无限与有限、永恒与瞬间所孕育的孩子,因此它是持续不断地斗争着的。……那个正在思想着的主体是生存着的。”“在路上”看过的风景固然短暂,然而,一旦这些风景与主体的精神发生了关系,那么,对于这个风景和这一刻来说,便镌刻进了生命历程,甚至可以对主体的未来产生影响——这就是永恒。“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每一刻美妙风景的认真欣赏和把握,便赋予了风景和这一刻人生以不朽的存在——瞬间,便成了永恒。
对于“在路上”体验的珍视,是生命产生意义的基础。
二、个人体验的孤独性
正是由于有了个人体验的存在,这一个人性的体验便相应产生了孤独性。这种孤独是人最根本也是无法消除的情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与自我思维之后,这种孤独感便已深深扎根在了人类的血液之中,代代相传。克尔凯郭尔历来主张,人当以“个体”或者“单一者”的形象出场;雅斯贝尔斯也认为,在生存哲学所处的时代精神背景下,人不可归类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个人体验产生了孤独性,而反过来,孤独也令个人体验具有了意义。
在“小小的茅屋里”,“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如此狭小的空间中,在用具的中间,也似隔了“千里万里的距离”。而正是这些冷冰冰的“面孔”,令作者感到了生命的温暖,如那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第七首诗歌中,人们从不同的路上汇聚而来,而最终又从不同的路上离散,“那些分歧的街衢/又把我们吸回,海水分成河水。”路的意象再次显现,不同的道路预示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风景构建着不同的人生可能性。生命不是知识的概念,它不可复制,它需要人去体会、感悟,在体会和感悟中明确生命过程的内涵。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在路上”才具有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路上”也有了存在的必要。
三、“在路上”成长
《十四行集》中的诗歌多带有对于成长的礼赞。冯至强调人内在生命的丰满与充实,因而这是一种更具精神内涵的喜悦与完成。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保持生存的超越性”是他认为生命永恒的重要保证。“在生存吸收本质,又超越被吸收的本质这一过程中,只有不局限于任何本质的生存才是绝对的。”“在路上”提倡对现实的珍视和把握,而对体验重视的旨归,其实在于生命的成长与完善。
油加利树和万物一样,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它“无时不脱你的躯壳”,然而,这棵树又是永恒的,获得永生的,因为它的变化,是对于生命质量的提升,“凋零里只看着你成长”。这些成长的瞬间,具备了生存的深刻性,它的价值永远不会消失,所以,成长的瞬间伴随着生命的过程而具备了永恒的价值内涵,“现时可对过去做出全新的解释,赋予过去以生存性意义,使得过去不再是独立的过去,而获得了相对于此刻这一瞬间所作抉择的意义。现时还可赋予未来以生存性意义。”这一刻的改变,不仅改变了过去和现在,同时还改变了未来,所以,这一刻,便是进入生命内涵与未来发生联系永恒的一刻,并将永垂不朽。同样对于成长的礼赞的诗歌,还有第九首。在此诗中,作者以一个全知叙述者的身份,藏在一边,全知全能地观察着英雄归来时的所见所思。作者在此诗的前两段大笔挥洒着英雄归来时的情态与思想,轮廓粗粗拉拉,在思想升华处却又不吝精雕细琢;后两段则完全是这个全知叙述者的思想活动。战士已 “永向苍穹”,“超越了他们,他们已不能维系住你的向上,你的旷远”。英雄的战士与庸俗的民众产生的对比十分强烈,而最后,崇高的不断斗争的战士获得了超越,卑俗的大众只有向下坠落。
冯至的《十四行集》初版印行于1942年,正是中国抗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在写作这二十七首诗时,冯至已在西南联大任教,居于滇池旁一块幽静的处所。作者在一篇序言里提到诗作的写成经过:“一九四一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这两句话透露出了两个信息:一是,在这个人的悠然独处中,诗人冯至将思索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内心,因而,这思考的成果也应是个人化的;二是,诗人与前线的抗战距离较远,故诗人才能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人类处境这一形而上而不是现实层面的思考上。然而,当时文坛中的其他诗人,却抛弃了对个体的发掘,将诗作汇入了抗战的集体语流之中,正如诗人艾青所描述的:“他们几乎和抗战发动的同时,一面撇开了艺术至上主义的观念……撇开了日常苦恼的缕述,撇开了对于静止的自然的幸福凝视,一面……以人群的悲苦为悲苦,以人群的欢乐为欢乐。”因此,在那时的语境中,《十四行集》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孤立事件,它远离尘世的争斗、革命、政治,以心灵轻微的波动,抵御着宁静的滇池外的喧哗,似一株空谷幽兰,孤独地绽放,寂寞的散发出幽幽清香。从有限到达无限,这是人类世世代代苦命的愿望和执著的追求。庄周曾慨叹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在路上”要求的是一份对于生命过程的珍重,尽管人生的旅程免不了孤独,但也正是这孤独,赋予了每个人的生命以存在的意义。这意义要求人们,走在自己的路上,要不断保持生命的丰盈,在生命的过程中认真体验,赋予每一个时刻以积极的内涵。那么,新鲜的心灵之花和智慧之果,便会使有限的时刻获得永生。《十四行集》是作者冯至数十年思索的艺术结晶,它以诗性的哲理参透了永恒的秘密,而其本身,也成为了这一秘密的最好证明。
参考文献:
[1]周棉.冯至传略[J].新文学史料,1992,(3).
[2]黎荔.冯至与里尔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2).
[3]顾彬著,张宽译.路的哲学——论冯至的十四行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2).
[4]陶熔.论冯至十四行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1).
[5]周棉.论冯至的十四行诗[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2).
[6]陈卫.西方山水理念与冯至的《山水》《十四行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7).
[7]冯金红.体验的艺术——论冯至四十年代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3).
[8]解志熙.诗与思——冯至三首十四行诗解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3).
[9]张同道.生命的风旗——论冯至《十四行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4).
[10]陆耀东.论冯至的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2).
[11]杨志.冯至与杜甫诗歌的时空体验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5).
[12]姜涛.冯至、穆旦四十年代诗歌写作的人称分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4).
[13]杨志.从德国浪漫派到存在主义——论冯至对德语文化的接受与消解[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5).
[14]冯至.《十四行集》[EB/OL].http://bbs.zhiyin.cn/viewthread.pdf?tid=336449.
[15]王树人,叶秀山等.西方哲学史·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万春怡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0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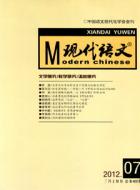
- 两汉纪行赋纪实性风格初探 / 韩佩佩
- 陶渊明田园诗中的理想与现实 / 黄三平
- 浅谈“清谈”误国论 / 游琦
- 论唐代贬谪诗歌中的巴渝 / 李毅 张华清
-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赏析 / 杜中伟
- 伪喜的生存,孤独的灵魂 / 梅海江
- 《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 赵风杰
- 对“有余力,则学文”的新解读 / 路炳明
-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之探究 / 梁新荣
- 是瞒天奇谋,抑催命拙计? / 郭曼
- 论《九歌》的性质 / 刘瑞学
- 论秋瑾的咏植物诗 / 黄剑光
- 沿着鲁迅的思路细读《阿Q正传》 / 聂国心
- 试论鲁迅作品的童年世界 / 唐军军
- 打不败的硬汉:海明威小说中的斗牛士形象 / 陈霄
- “辣”——强势女人的必备武器 / 马雪萍
- 在路上 / 万春怡
- 一曲健康优美“人生形式”的牧歌 / 王永章
- 虚幻的洁净和现实的肮脏 / 孙彦萍
- 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本质观的再认识 / 白淑杰
- 试分析《伤逝》中的婚恋悲剧 / 潘万里 王艳
- 此中有真意,“微笑”更“落泪” / 钟伟建
- “过失”的产生 / 李程
- 珠散意联 情牵一线 / 王军文
- 作为他者的吉普赛人 / 李昌燕
- 奏响生命之歌 / 李婷
- 文学文体学分析方法下的颜元叔散文研究 / 陈丽 夏家楠
- 常理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 李胜志
- 跨越世俗\时空的真爱 / 路王娟
- 物犹如此 / 张潇萌
- 知音其难哉 / 袁贝贝
- 孤独的清醒者 / 刘婧芳
- 由《荷塘月色》中“妻子”这一形象想到的 / 刘忠伟
- 浅谈职校生语文教学中口语交际能力的评价与培养 / 王珠云
- 新课程下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误区及应对 / 顾文琦
- 以文本为支点 提高阅读能力 / 钟脆鸣
- 浅议中职语文课堂教学目标设计现状 / 程祖芳
- 浅析古诗词“六步鉴赏法” / 陈志刚
- 谈积极情感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 李洪华
- 五年制高职语文实用能力训练题设计的思考 / 马原
- 激发兴趣学古诗 / 朱敬允
- 对初中名著导读教学的几点思考 / 马建军
- 从现代心理角度审视高中作文教学的困境 / 刘卫平
- 开发生活资源,丰富写作素材 / 黄慧齐
- 语文课堂审美原则初探 / 苏税华
- 小活动,立大功 / 王维升
- 点亮学生理性智慧 / 习萍
- 影子跟读法在日语教学中的作用 / 冯淳
- 一块新奇而充满挑战的跳板 / 董秀琴
- 初中语文对比教学探微 / 陈元芬
- 竞赛式教学法引入中职语文课堂的尝试 / 钟巧玲
- 放飞心灵 感受生命 / 王艳敏
- 语文课堂,缺失了什么? / 苟昌革 崔志钢
- 《歧路灯》詈骂语略谈 / 申利歌
- 概念整合理论对网络生僻字的认知分析 / 干敏
- 语言接触与翻译:以《国际歌》汉译为例 / 邓科
- 网络汉字词的造词研究 / 岳艳红
- 大陆台湾英译汉四字格对比研究 / 刘唯一
- “打”字的字形和语音问题 / 罗晓春
- 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 / 王丽滨 曹晨光
-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再读《论语》 / 邓颖平
- 诗歌朗诵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 王静
- 汉民族意象思维及其流失 / 高璇
- 谈单用的“之后”\“之前” / 胡晓萍
- 抬杠言语行为的语用分析 / 马若宏
- “绿色”的词义扩大和语义组合问题 / 李华云 连辉
- 闻喜方言与婚俗文化 / 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