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3期
ID: 147836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3期
ID: 147836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之探究
◇ 梁新荣
摘要:袁宏道是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以他为核心的公安派文人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力主以心为师、“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袁宏道的思想在万历二十八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本文具体分析了他后期诗文理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尚“淡”,尚“质”,追求浑厚蕴藉的风格。
关键词:袁宏道诗文理论浑厚蕴藉
在晚明诗文革新运动中,袁宏道作为公安派的主将,以其锐利的目光、直率的语言道出文坛积弊之所在,并与之针锋相对,一扫文坛之摹拟之风。他的诗文理论是公安派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破了复古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对明代和后来文学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笔者通过对袁宏道诗文理论的研究,强烈感受到他思想转换的脉络。作为晚明文学革新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袁宏道的诗文理论是一定的时代思潮、学术文化、自身天赋及成长经历等诸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前行的发展完善的过程,表现为中郎由任性狂傲到淡定自适。在这一过程中,中郎始终坚守“自由”和“真”的信念,用充满才情之笔,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一、倡“淡”
万历二十九年之前,中郎受王学左派和禅宗影响颇深,又直接继承李贽的“童心说”,在诗文理论上大力推行“性灵说”。对于他这一时期的作为,钱谦益曾评价说:“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1]在生命的后期,中郎深入、系统地研读了大量唐宋著作。他通过研读宋代诗文,特别是批点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一方面为自己的诗文改革理论找到依据;另一方面也感到自己以往的文学创作过于粗率。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和自身心境的转变,中郎开始反省以往的矫枉之论。在悼念同是公安派的好友江盈科的文中,他说:
进之才俊逸爽朗,务为新切,嘉、隆以来所称大家者,未见其比。但其中尚有矫枉之过,为薄俗所检点者。往时曾欲与进之言,而竟未及,是余之不忠也。然余所病,正与进之同证。[2]
同时在阅读了大量宋朝大家作品的基础上,他感到自己以往的诗多刻露之病,对于自己盲目的反对复古多有内疚之情。“近日始学读书,尽心观欧九、老苏、曾子固、陈同甫、陆务观诸公文集,每读一篇,心悸口,自以为未尝识字。”心态日趋沉稳平静,文风也在发生转变。小修在描述中郎文风转变时说:“盖自花源以后诗,字字鲜活,语语生动,新而老,奇而正,又进一格矣。”
他秉承性灵,但已由前期的矫枉趋于平淡,不再强调自我感情的真、直率是诗歌精神所在,而以“淡”为诗歌的完美状态。在写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叙呙氏家绳集》中,中郎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淡”:
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东野、长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极,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学,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3]
中郎以苏轼的话来阐述“淡”。苏轼曾云:“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4]他认为陶渊明、柳宗元的诗歌于淡泊中寄托着韵味,冲淡宁静,浑然天成。中郎将“淡”的审美范畴扩展到性灵说之中,认为“淡”是诗文的真性灵,而不再将直率、狂放之真作为性灵的精髓。淡与真都出于自然,真只是自然的不加修饰、缺少内涵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激情的衍化,表现出率真疏狂的风格特征;而淡是自然有所沉淀、有所提炼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激情的蜕变,表现出物我相融、平和的风格特征。对于如何才能求得淡,中郎认为它是不可造,又无不可造的,不可以强求,而应该顺其自然。淡是不加修饰的,与真、自然相联系而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淡”与其说是中郎所追求的一种文学风格,不如说是他所追求的最高的一种审美理想。因为淡之不可强求,中郎感慨说:“往只以精猛为工课,今始知任运亦工课。精猛是热闹,任运是冷淡,人情走热闹则易,走冷淡则难,此道之所以愈求愈远也。”
中郎还认为具备理想的人格才可能达到“淡”的诗文创作境界。他继承了庄子论“淡”的观点,追求一种自然而恬淡的意境。庄子曾说:“淡而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认为“淡”是由自然派生出来的,是朴素的、恬淡的。中郎之“淡”也是企慕一种自然闲淡的境界,向往一种闲淡的生活。只有心境平和、恬淡,才能创作出真正“淡”之作品:“(遂溪)公以身为陶,故信心而言,皆东篱也。”
在晚年生活中,中郎本人即是如此。他超越了世俗生活,安居柳浪馆,看山光水色,与友泛游,读书念佛,寻求一种“韵”之理想人格:
大都士之有韵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可以得韵。故叫跳反掷者,稚子之韵也;嘻笑怒骂者,醉人之韵也。醉者无心,稚子亦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由斯以观,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韵者大解脱之场也。[5]
中郎认为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应表里如一,以身为陶,以韵为理想人格,才能在诗文创作中真正达到“淡”。
二、尚“质”
中郎于《行素园存稿引》中在前期强调“真”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更加注重内在特质,真正从新的角度对“真”加以变通。他云:
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故今之人所刻画而求肖者,古人皆厌离而思去之。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极也。博学而详说,吾已大其蓄矣,然犹未能会诸心也。久而胸中涣然,若有所释焉,如醉之忽醒,而涨水之思决也。虽然,试诸手犹若掣也。一变而去辞,再变而去理,三变而吾为文之意忽尽,如水之极于淡,而芭蕉之极于空,机境偶触,文忽生焉。[6]
他认为文章仍然应该表现作者的真感情,但又不能仅仅满足于“真”,而应该有“质”。中郎的“质”与孔子所讲的“文质彬彬”的“质”、荀子所讲的“情者,性之质也”的“质”是同一个含义,指的是人或事物的本质特征,而不仅仅是文风的朴素自然。如果说真文的生成是性灵的抒发,那么有质之文则需要创作者不仅有一个真诚的心灵,更要有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底。中郎将“质之至”作为诗文的最高目标,质之文要求创作者有真实的情感,又要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只有这样,灵感与积累碰撞出的火花才是最绚烂的。
中郎论“质”,又有怎样的含义呢?首先,“质”是作品成为好作品、长期流传下去的必然要求。“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他以“物”来作比喻,说明只有好的内容、好的思想才能使得一部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淘洗,才能使后人喜爱并保存它。其次,“质”的精神内核是“真”,“质”是“真”之文所显现出来的自然、纯朴并有内涵的美学风格。没有“真”的“质”是无根之水,无法持久地流淌;没有“质”的“真”如冬天的树简单苍白,无法让人感到赏心悦目。“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最后,达到“质”的完美境界是经过学识的积淀,去除浮华的表面装饰,最终触机而发的过程。最初在生活和学识的积累方面,“博学而详说,吾已大其蓄矣,然犹未能会诸心也。久而胸中涣然。若有所释焉,如醉之忽醒,而涨水之思决也”。积累到一定境界,作文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当作文如庖丁解牛般文字自心中自然流泻而出,那么创作出来的文章就是至文。“古之人不自以为文也,曰是质之至焉者矣。大都人之愈深,则其言愈质,言之愈质,则其传愈远。”
中郎的尚“质”之论表现了他后期的美学追求,显示了与前期诗文理论不同的追求。中郎之“质”是含蓄、有所蕴藉的,不再追求前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的创作风格;中郎之“质”又是在博学多识的基础上达到的,而不再出自于赤子之心。从中郎论“质”可以看出他受儒学影响较深。儒家要求作文应该“文质彬彬”,质与文要配合适当,相得益彰。在中郎的诗文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质”的提出使内容与形式、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起来,使中郎的诗文理论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成熟。
三、追求浑厚蕴藉
随着中郎学术思想渐趋稳实,早年的锐气逐渐消退,诗文也在发生着变化。中郎在晚年悔悟狂禅、注重禅净双修,这种稳实的学风影响到诗文创作方面就是变疏狂轻灵为含蓄蕴藉。小修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曾形象地表述中郎的这一变化:
况学以年变,笔随岁老。故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诘,有杜陵,有韩昌黎,有长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笔与之会,合众乐以成元音,控八河而无异味,真天授,非人力也。[7]
这段话道出了中郎晚年诗文风格的转变和诗文追求内蕴的事实。小修说中郎“无一字不无来历”,虽然言之太过,但中郎注重字句的锤炼、诗文意境的深厚却是事实。中郎自己也对以前作品的刻露直白非常不满,而开始变俚俗为雅致,变直露为蕴藉:“常云我近日始稍进,觉往时大披露,少蕴藉。”
他后期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都和前期不同,内容上多为隐居生活和山水题材,而语言平淡清丽,呈现出清新宁静的蕴藉风格。在诗歌风格方面,后期的作品少了些锐气,多了些平允中和,和对生死命运的无奈。这在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邺城道》:
何处魏离宫,荒烟断苇中。猎蹄晴卷雪,高隼怒盘风。苑古梧桐秃,墙崩枸杞红。空台与流水,想象旧廉栊。[8]
这首诗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郎作于赴京途中。意境幽远,遣词凝练。他以荒烟断苇、猎蹄卷雪、高隼盘风、梧桐秃、枸杞红这组意象表现了旧时宫阙颓败的景象,最后点出作者的感叹,情景深远,结构严谨。
他也有些后期的作品简洁、清新,如《王郡丞邀饮阳和楼》:
青天一碧翠遮空,浪卷云奔夕照中。郭外荷花三十里,清香散作满城风。[9]
诗中描写诗人与王郡臣畅饮于阳和楼,语言简洁,表现出一种安静闲逸的情怀。同样是描写山水风光的诗歌,这首诗无论在语言的娴熟,还是意境的深厚,都比前期的作品圆熟。
概而言之,在袁宏道生命的后期,生活的变故和思想的转向,使得颂经礼佛、游山读书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在生活方式上,他有意效仿陶渊明,隐居山林,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对自我意识的刻意压制和生活环境的详和安静,使得他的内心世界逐渐平和,并逐步向传统回归。中郎后期文学革新思想的变化,是与其为学主张、人生态度、为文风格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变化的内容主要是对过去矫枉之论的纠正,但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反对复古主义的决心没有改变,对“真诗”、“真文”之美的追求也没有改变。
注释:
[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7页。
[2][3][5][6][7][8][9]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伯修》,《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评韩柳诗》,《苏轼文集》(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09-2110页。
(梁新荣新疆伊犁师范学院83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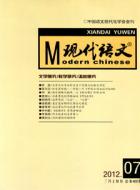
- 两汉纪行赋纪实性风格初探 / 韩佩佩
- 陶渊明田园诗中的理想与现实 / 黄三平
- 浅谈“清谈”误国论 / 游琦
- 论唐代贬谪诗歌中的巴渝 / 李毅 张华清
-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赏析 / 杜中伟
- 伪喜的生存,孤独的灵魂 / 梅海江
- 《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 赵风杰
- 对“有余力,则学文”的新解读 / 路炳明
-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之探究 / 梁新荣
- 是瞒天奇谋,抑催命拙计? / 郭曼
- 论《九歌》的性质 / 刘瑞学
- 论秋瑾的咏植物诗 / 黄剑光
- 沿着鲁迅的思路细读《阿Q正传》 / 聂国心
- 试论鲁迅作品的童年世界 / 唐军军
- 打不败的硬汉:海明威小说中的斗牛士形象 / 陈霄
- “辣”——强势女人的必备武器 / 马雪萍
- 在路上 / 万春怡
- 一曲健康优美“人生形式”的牧歌 / 王永章
- 虚幻的洁净和现实的肮脏 / 孙彦萍
- 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本质观的再认识 / 白淑杰
- 试分析《伤逝》中的婚恋悲剧 / 潘万里 王艳
- 此中有真意,“微笑”更“落泪” / 钟伟建
- “过失”的产生 / 李程
- 珠散意联 情牵一线 / 王军文
- 作为他者的吉普赛人 / 李昌燕
- 奏响生命之歌 / 李婷
- 文学文体学分析方法下的颜元叔散文研究 / 陈丽 夏家楠
- 常理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 李胜志
- 跨越世俗\时空的真爱 / 路王娟
- 物犹如此 / 张潇萌
- 知音其难哉 / 袁贝贝
- 孤独的清醒者 / 刘婧芳
- 由《荷塘月色》中“妻子”这一形象想到的 / 刘忠伟
- 浅谈职校生语文教学中口语交际能力的评价与培养 / 王珠云
- 新课程下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误区及应对 / 顾文琦
- 以文本为支点 提高阅读能力 / 钟脆鸣
- 浅议中职语文课堂教学目标设计现状 / 程祖芳
- 浅析古诗词“六步鉴赏法” / 陈志刚
- 谈积极情感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 李洪华
- 五年制高职语文实用能力训练题设计的思考 / 马原
- 激发兴趣学古诗 / 朱敬允
- 对初中名著导读教学的几点思考 / 马建军
- 从现代心理角度审视高中作文教学的困境 / 刘卫平
- 开发生活资源,丰富写作素材 / 黄慧齐
- 语文课堂审美原则初探 / 苏税华
- 小活动,立大功 / 王维升
- 点亮学生理性智慧 / 习萍
- 影子跟读法在日语教学中的作用 / 冯淳
- 一块新奇而充满挑战的跳板 / 董秀琴
- 初中语文对比教学探微 / 陈元芬
- 竞赛式教学法引入中职语文课堂的尝试 / 钟巧玲
- 放飞心灵 感受生命 / 王艳敏
- 语文课堂,缺失了什么? / 苟昌革 崔志钢
- 《歧路灯》詈骂语略谈 / 申利歌
- 概念整合理论对网络生僻字的认知分析 / 干敏
- 语言接触与翻译:以《国际歌》汉译为例 / 邓科
- 网络汉字词的造词研究 / 岳艳红
- 大陆台湾英译汉四字格对比研究 / 刘唯一
- “打”字的字形和语音问题 / 罗晓春
- 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 / 王丽滨 曹晨光
-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再读《论语》 / 邓颖平
- 诗歌朗诵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 王静
- 汉民族意象思维及其流失 / 高璇
- 谈单用的“之后”\“之前” / 胡晓萍
- 抬杠言语行为的语用分析 / 马若宏
- “绿色”的词义扩大和语义组合问题 / 李华云 连辉
- 闻喜方言与婚俗文化 / 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