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3期
ID: 147069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3期
ID: 147069
试析《窗》中人物形象所体现的人性美丑
◇ 沈凤飞
人物形象历来是文学创作者精心构思、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刻画的成功与否决定了作品的成败。澳大利亚女作家泰格特的短篇小说《窗》,虽只有1200余字,但鲜明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尤其是人物形象所体现的人性美丑更令人回味和思索。
每一时代,社会都呼唤人性美,同时也无情鞭挞人性的丑恶。作者在小说中精心设计了两个人物——近窗者、远窗者,他们是病友。通过两个灵魂的猛烈撞击,飞溅的点点星火中折射出人生哲理、世态人情。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深入探讨两个人物人性美丑的体现及根源。
一、生活态度极其相似
两个病人的病情都很严重,由于医院的无意安排,一个病人成了近窗者,有机会欣赏窗外的美景;另一个则成了远窗者,无缘窗外精彩世界。作者并未交代人物的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这样的设计说明了人物形象更具有普遍意义。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两个人物聊得很投机,聊生活、聊工作,按照这样的逻辑判断他们应该相处得很默契、很友好,同时也说明在病重时期,两个人能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生活。从这点看,近窗者、远窗者是很相似的。
二、性格内涵截然不同
泰格特这位作家因《窗》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人物形象揭示一个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适用的道理:性格内涵决定人性美丑。近窗者性格的开朗与乐观、友善与仁慈,使他乐意每天忍受疼痛,在一小时的仰坐里为同伴描述他所见到的窗外的一切,然而故事的结局揭示了其实窗外并无美景,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试想,他为了让同伴在疾病折磨中分散一些注意力,减少一些痛苦,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积极的心态。首先他必须在讲述之前作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在讲述时吞吞吐吐,思路混乱,势必影响同伴的心情。其次他描述的景象中有静景、动景,但只有乐景,没有悲景,画面五彩缤纷,绚丽多姿,这足以说明他的描述是用心良苦的,以此来激励自己同病魔作顽强的斗争;同时也用生机勃勃的人类活动去点燃同伴奄奄一息的生命之火,激发病友的生之欲望,活之动力。这样的描述效果也来源于近窗者的善良心灵,为他人着想的美好品质,而且他的这种热忱是无私的,不求任何回报的。在临终之前,面对呼吸急促、生命垂危,也许他有力气向病友发出求救,给自己赢得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但他没有这么做,可能这辈子他从来不要求别人帮他做些什么,但这种性格也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死亡。而远窗者呢,虽然每天能从近窗者口中听到牡丹花、金盏花、摆弄游艇、情侣散步等美景,但毕竟不是亲眼所见,出相同的钱,为何自己享受不到欣赏窗外美景的权利,于是心里极度不平衡,嫉妒、怨愤,自私心膨胀,直至最后见死不救,按门铃让值班护士过来是举手之劳的事。文章最后用“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作结,采用“欧亨利式笔法”,给人以丰富的遐想空间。读者可以想象,这个远窗者得知近窗者因他的自私、冷酷而死后,会沉浸在怎样的自责和愧疚之中?这样的结局也是性格内涵决定的。一扇窗户照出了两个灵魂,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态度,揭示了人性的美与丑。
三、人性美丑根源探究
《窗》这篇小说,短小精悍,寓意深刻,人们盛赞近窗者,鄙视远窗者。那近窗者、远窗者的人性美丑根源在于什么呢?内外单调的环境在近窗者眼里何能幻化成五彩斑斓、生动活泼的景象?这种动力来自他对生活的满腔热爱,来自他对病友的关心和友善。只有纯洁的心灵、高尚的人格才能幻化出充满生机、其乐融融的生活图景。人性美的根源在于对生活的热爱,对周边人的关心及无私的品质。远窗者是人性丑恶的代表,他虽然热爱生活、珍惜生命,“躺着的病人津津有味地听这一切”,这足以说明他渴望健康和阳光。可他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是建立在病友死亡之上的,只有近窗者死了,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占有靠窗的位置,这时候他心中应该有的善良倏忽即逝,反衬出的是丑恶无比的灵魂。人性丑恶的根源是他的自私欲,他虽有过矛盾和挣扎,但自私的本性占据了整个灵魂,以病友的生命为代价来摆脱心灵的困扰,但最后的结局“一堵光秃秃的墙”证明了自私的最后下场,也反映了作家创作这一人物形象的意义。
其实,世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但教育和习惯却使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就如文中的近窗者和远窗者。天性好比种子,既可长成香花,也可长成毒草,人应当时时检查,以培养前者拔除后者。这也是泰格特《窗》给予我们的启示。
(作者单位:海宁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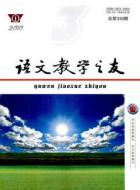
- 指向生命关怀的高中文言文教学 / 胡云信
- 让文言文教学奏出和谐的音符 / 徐庆龙
- 论语文课的语文味 / 王 飞
- 当前语文课堂教学的再思考 / 曹永华
- 文言文岂能一“读”了之 / 黄志达
- 古诗文当堂速背三招 / 何爱民
- 《故乡》教学课例点评 / 王鸿斌
- 对高中语文选修课程的教学反思 / 欧小红
- 孩子,这笑声应该是泪水 / 王术春
- 谈语文网络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必然性 / 张和新
- 该模糊时就模糊 / 师建军
- 性格改变命运 细节生发魅力 / 王针桂
- 仲永之哀与木兰之幸 / 王子义
- 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新” / 金伟方
- 《背影》的眼泪从哪里来 / 孔小波
- “不”为文眼表志趣 / 郜富勤
- 与名家商榷有关语言的表达 / 王德玉
-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几处商榷 / 郑建华
- 试析《窗》中人物形象所体现的人性美丑 / 沈凤飞
- 小说教学中文本细读的若干载体 / 杨秋益
-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到底如何翻译 / 万向群
- 浅谈“个性化解读文本”中教师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 / 苏 凯
- 浅谈文学形象的特殊形态——意象 / 马小纯
- 《归去来兮辞》课文注解指瑕 / 李世川
- 也说“丹凤三角眼” / 张玉明
- 如何上好高三专题复习课 / 潘晓琳
- 试卷评讲也要精心备课 / 周 虹
- 周朴园身上的“人性”与“阶级性”天平该偏向哪端 / 贾佑智
- 高考感悟类散文五步阅读法 / 魏雁飞
- 叶落知秋 福祸相倚 / 陆春建
- 例谈排序题的解题技巧 / 张 持
- 为“名著阅读”呐喊 / 余志明
- “事实材料”在议论文\记叙文写作中的不同价值取向 / 邹 萍
- 谈作文批改中评语的积极性 / 陈秋生
- “夫妇”古今谈 / 吴秀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