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3期
ID: 147065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3期
ID: 147065
《背影》的眼泪从哪里来
◇ 孔小波
《背影》是朱自清先生颇为成功的一篇叙事兼抒情散文。2001年,人教版新课标教科书八年级上册选用了该篇文章。作为书写父子亲情的典型代表,在各个不同时代,入选了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时期,人们对《背影》有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认为父亲家中的光景很是暗淡,透露出对黑暗社会的愤意;有的人认为《背影》抒发的是一种“人到中年”的复杂感情,是中年人成熟的心理活动;还有的人认为《背影》负载了一种晚辈对长辈的忏悔情结,是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对《背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从社会学、心理学,还是文化学的角度来解读,都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宏观阐释,往往淡化了“我”的存在。事实上,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我”并不是作为一种符码依附于父亲这个主体,相反,“我”在文中表现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三重人格结构,替我们找到了阐释“我的泪又来了”的另一种维度。
本我、自我、超我是弗洛伊德人格论的核心。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的人格是由三大心理动力系统组成的,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实际上是社会潜意识状态下人们渴望逃避他人约束或意识控制而寻求自由的张力状态。主张“快乐”的本我不愿受到任何伦理、道德规训,本身也不具备理性因素而往往表现为冲动,渴望自由,寻求解脱,感性因素多一些。正是由于处在这样一种潜意识状态下,作为儿子的朱自清要求自主,他不愿意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听从父亲的支配。这在文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我”认为自己早已不是小孩子了,能照顾好自己了,自己需要快乐自由。
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
年轻人有年轻人自尊的一面,有自己想法的一面,尽管有时很冲动,很感性。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对自己充满自信,对自己的自主愿望受到父亲的支配,还是存在着较强的不满的。
本我所具备的“快乐原则”必然使“我”违背父亲的美好愿望,认为他的言语、思维已经过时,于是“我”成为反传统的连接点。本我或有或无地展现着年轻人的活力、自强,迫使“我”这个实体或隐或现地对封建父权发出了挑战。
往往这个时候,超我要通过意识去管制本我的冲动,尽力使它回到自我的轨道。超我作为一种道德化、伦理化的要求,主要依赖于人在生活中形成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尤其是儿童时代受到父母的影响。传统观念认为,个体的一切来自父母,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孝敬父母、听从父母的安排成为个体不可规避的职责。道德规训将这种职责“超我化”,逐渐演变成道德感召、生命认同和行为约束。文本中父亲命令似的口吻,正是让“我”超我化的因素:
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仿佛小时在大街上,父亲突然有事情,让“我”不要乱跑,以免丢失。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去他不放心,“我”被剥夺了离开的权利,超我化地服从父亲的意愿。
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儿子听从父亲的话是天经地义的,是儿子超我的道德准则。因此,父亲在事情的决定上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关怀的背后,“我”不是原来的本我,也不愿意成为理想的超我。于是,“我”面临服从父亲和主张自主的两维选择的冲突。一方面,儿子本我化下,要独立自主;另一方面,本我来自父亲的冲击、规约,又使得超我要求下的儿子十分压抑自己的言语、行径、情感。超我、本我的较量,构成了文本效果的暗中颠覆,外化的表现就是父子冲突。父与子,作为两个对立的实体之间的背离,即是对文本传达出的父子情的有力消解。尽管这种消解在朴实的行文中没有表露痕迹,但还是让我们体会到了《背影》的另一种苦涩。这种苦涩需要通过自我来调节,才能完成《背影》的审美置换。
自我的任务是按照“现实原则”来调节和控制本我的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超我的活动。本我与超我之间过度或缺失都会引起自我的焦虑。本我不能打败超我,超我也不能说服本我,两者之间的交叉要求自我的介入。此时,本我的冲动、超我的感化演变成一种感情压抑在体内沸腾。于是,“我”哭了: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此时的泪水,是感情压抑的爆发,本我、超我都为自我让了路,自我在哭泣。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人海茫茫,年年相似。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父亲的背影呢?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缕清情绪后的自我,摆脱了本我、超我,平静的心态下的真情流露,泪水中交融着本我自我的重合,成为自我的认同。
《背影》作为经典名作,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篇作品,便不等于否定其所传承的父子亲情,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教材只是一种载体或者工具,囿于教材的解读是苦涩的,语文教学应该用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和思考。
参考文献:
①张怀久 《语文教材中的朱自清散文简介》, 载《上海教育》1980年第11期。
②岑健《〈背影〉魅力新说》,载《语文学习》1987年第12期。
③傅书华 《永远的〈背影〉》, 载《语文教学通讯》2001年第17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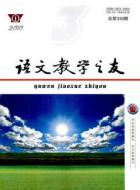
- 指向生命关怀的高中文言文教学 / 胡云信
- 让文言文教学奏出和谐的音符 / 徐庆龙
- 论语文课的语文味 / 王 飞
- 当前语文课堂教学的再思考 / 曹永华
- 文言文岂能一“读”了之 / 黄志达
- 古诗文当堂速背三招 / 何爱民
- 《故乡》教学课例点评 / 王鸿斌
- 对高中语文选修课程的教学反思 / 欧小红
- 孩子,这笑声应该是泪水 / 王术春
- 谈语文网络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必然性 / 张和新
- 该模糊时就模糊 / 师建军
- 性格改变命运 细节生发魅力 / 王针桂
- 仲永之哀与木兰之幸 / 王子义
- 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新” / 金伟方
- 《背影》的眼泪从哪里来 / 孔小波
- “不”为文眼表志趣 / 郜富勤
- 与名家商榷有关语言的表达 / 王德玉
-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几处商榷 / 郑建华
- 试析《窗》中人物形象所体现的人性美丑 / 沈凤飞
- 小说教学中文本细读的若干载体 / 杨秋益
-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到底如何翻译 / 万向群
- 浅谈“个性化解读文本”中教师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 / 苏 凯
- 浅谈文学形象的特殊形态——意象 / 马小纯
- 《归去来兮辞》课文注解指瑕 / 李世川
- 也说“丹凤三角眼” / 张玉明
- 如何上好高三专题复习课 / 潘晓琳
- 试卷评讲也要精心备课 / 周 虹
- 周朴园身上的“人性”与“阶级性”天平该偏向哪端 / 贾佑智
- 高考感悟类散文五步阅读法 / 魏雁飞
- 叶落知秋 福祸相倚 / 陆春建
- 例谈排序题的解题技巧 / 张 持
- 为“名著阅读”呐喊 / 余志明
- “事实材料”在议论文\记叙文写作中的不同价值取向 / 邹 萍
- 谈作文批改中评语的积极性 / 陈秋生
- “夫妇”古今谈 / 吴秀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