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2期
ID: 147047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2期
ID: 147047
无缘对面不相逢
◇ 施孟文
放眼19世纪后期的世界文坛,法国的居伊·德·莫泊桑无疑是耀眼群星中璀璨的一颗。《羊脂球》的横空出世,使他一举成名,步入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巨匠之列,其作品的批判力度与艺术造诣堪称后世楷模。
《我的叔叔于勒》作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而入选中学课本,其巧妙的布局构思和突出的对比反衬形成表现主题的两大手段。而主题及其表现手段又集中于文章结尾的“邂逅”部分。历来文学鉴赏品评大同小异,均认为这一部分是全文情节的高潮,最能集中、鲜明而深刻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的罪恶——菲利普夫妇惟利是图,嫌贫爱富,以致六亲不认,逃避似地主动躲开了于勒。
笔者在此要说的是:虽然菲利普夫妇极力逃避“兄弟相认”的尴尬,但对结局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更多归功于我们的主人公——于勒。正是他认为兄弟“无缘”才使得“对面不相逢”。
附带说一下,有部分读者认为本文的主人公应该是菲利普夫妇,正是他们截然不同的言行举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丑恶。笔者只想提个简单问题:为什么《孔乙己》的主人公不是丁举人、《范进中举》的主人公不是胡屠户?同样《我的叔叔于勒》这个题目不是个别的后人臆度而加,是作者的本意所在,创作的动机所归。他塑造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失败者和受害者形象。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泥潭和小职员的小染缸使于勒从小就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恶习,从而先是受到家庭排斥(虽然也做过花花公子),后遭到社会鄙弃(虽然也当过便便款爷)。经济的世界,金钱的关系,毁灭了像于勒这样一些没有金钱意识的人的生活,把他们推进了人生悲剧的深渊;也扭曲了菲利普这样一些不得不重视金钱的人的心灵,使他们淡漠了对人的同情、关爱,变得庸俗自私。
于勒的两起两落,深受其害、深为失败的同时最大的收获就是生活使他看清了金钱主义的罪恶,看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那么,对于“兄弟邂逅”,我们试想一下,于勒是在“回家”,必然会时刻注意着轮船的航向,甚至乘客、游人中有无熟悉的面孔(他们毕竟传递着家乡的讯息);而菲利普一家则是在“游玩”,他们则必然尽兴于山水风光而心无旁骛。另外,于勒的衣貌神态变化巨大,而菲利普基本上应是老样子。
有了以上两点比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菲利普看上于勒一眼就已认出弟弟的80%,那么,于勒只要扫上菲利普半眼就能完全认出哥哥的,并且肯定早在哥哥发现自己之前就已发现哥哥了。这种情况下,如果于勒有兄弟相认的念头甚至像发现救命稻草一样叫嚷着扑向菲利普,那可远远不是这对小职员夫妇所能预料得到、提防得住、躲避得开的!
而在此时,早已落魄的于勒反而变得分外清醒,他回哈佛尔仅是想落叶归根而绝非寻亲。历经沧桑后洞察世态,对相对现在自己而言的“有钱哥哥”不作任何企求,不报丝毫幻想,这种无望性的失望正是绝望!
以失败者与受害者的身份对资本主义进行无言的批判、无声的控诉,笔者认为这远比揭露惟利是图、六亲不认等资本主义制度的表层腐朽更富有力度、更发人深思。
(作者单位:沙河市高庄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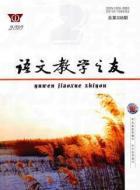
- 现代社会环境对语文教育的负面影响 / 胡 慧 陈家彦
- 教学“实”录:形同“虚”设 / 马新桥
- 读图时代:守护文字的诗性 / 徐 燕
- 语文教师不妨“懒”点 / 章桂周
- 要抓住文章的本质来教学 / 陈庆云
- 浅论语文的想象美和想象力的培养 / 李德新
- 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看课堂教学优化 / 张 清
- “意象”三“象” / 宋 峥
- 追求语文教师教材驾驭力的高境界 / 郑 勇
- 语文教材他山之石的介绍 / 黄金丽
- 超越功利,成就阅读的价值 / 余耀清
- 意外的收获 / 王 季
- 把握时机 灵活处理 / 王丽霞
- 让“话题式”阅读教学告别“三无” / 肖连珠
- 新课程下的文言文教学现状分析及教学策略 / 桑芝华
- “言”字释义辨析 / 王化斌
- 此情可待成追忆 / 戚光宇
- 游子“床”前月光明 / 杨青舟 吴 婧
- 《送东阳马生序》结构之我见 / 杨景太
- 杨贵妃能不能吃上新鲜荔枝 / 刘小成
- 巧用叠字——《采薇》的独特风景线 / 陈 欣
- 解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五把钥匙 / 肖 武
- 《中国建筑的特征》指瑕 / 陈正春
- 摆正两个关系触动学生情弦 / 周国飞
- 敬畏生命源于惊异 / 杨金平
- 作文应彰显个性色彩 / 缑克喜
- 《使至塞上》一处注释的质疑 / 方勇军
- 关于散文《雪》的开头之我见 / 叶久平
- 《藤野先生》中一处离题的文字 / 黄兴亚 黄兴东
-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 青 秀
- 朴素的开首 真实的魅力 / 李桂萍
- 无缘对面不相逢 / 施孟文
- 学生自主阅卷:提高语文复习训练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 刘国志 宋保万
- 考生读懂题目了吗 / 朱元勇
- 反义合成词的产生原因探析 / 齐红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