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2期
ID: 147034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2期
ID: 147034
《送东阳马生序》结构之我见
◇ 杨景太
在教学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二十三课《送东阳马生序》时,我和学生深深地被宋濂的勤学苦练精神所感动,也深感其文章用词、写法的高妙。不过,我们在赞叹之余,也发现了文章中一点小瑕疵。
有人会说:“宋濂乃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他的文章在当时堪称一流,哪有瑕疵之处呢?”可是,认真读过《送东阳马生序》一文的人们可能会发现,整篇文章在第二自然段与第一自然段的照应顺序上恰好相反,这就违背了一般性的照应规律。前面与后面既然要照应,就应当一一对准,像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写的《有的人》,其照应就非常严谨,顺序一点不乱。
而《送东阳马生序》一文的第一自然段是作者在讲述自己求学之难和在极端艰苦情况下的勤奋、用心之专。而这一自然段中作者是按幼时借书抄录之难、成年后求师之难、行路之苦、生活之苦的顺序来安排结构的。但是,行文到第二自然段时,作者虽然是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今日太学生学习条件的优越,可写作是按照生活、住宿、求师、借书的顺序来完成的,刚好与第一自然段的叙述顺序相反,这是宋濂大学士故意安排的呢,还是其疏忽之处呢?我认为这一点很值得推敲和商榷。
笔者拙见,第二自然段若能这样安排顺序,则更天衣无缝。即:“今诸生学于太学,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也;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而原文是这样:“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大家可以做个对照,便一目了然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我们知道,第一自然段作者主要是按时间顺序,即以自己从幼时到成年后的求学经历为顺序来安排的;而第二自然段作者可能又按由主到次的顺序,即先写当今太学生的主要优越之处,再写他们的次要优越之处。而第二自然段的内容刚好又与第一自然段倒着照应,虽然它与一般的照应规律不相符合,在结构安排上似也合情合理。
不管怎么讲,《送东阳马生序》一文的第二自然段在行文结构上是值得我们质疑探究的。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之下,教师和学生都应在平时的阅读学习中,要敢于质疑名家名篇,敢于读出自己的见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阅读的乐趣;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以便不断提高阅读文章的能力。
(作者单位:方城县赵河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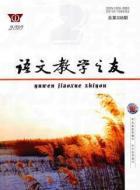
- 现代社会环境对语文教育的负面影响 / 胡 慧 陈家彦
- 教学“实”录:形同“虚”设 / 马新桥
- 读图时代:守护文字的诗性 / 徐 燕
- 语文教师不妨“懒”点 / 章桂周
- 要抓住文章的本质来教学 / 陈庆云
- 浅论语文的想象美和想象力的培养 / 李德新
- 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看课堂教学优化 / 张 清
- “意象”三“象” / 宋 峥
- 追求语文教师教材驾驭力的高境界 / 郑 勇
- 语文教材他山之石的介绍 / 黄金丽
- 超越功利,成就阅读的价值 / 余耀清
- 意外的收获 / 王 季
- 把握时机 灵活处理 / 王丽霞
- 让“话题式”阅读教学告别“三无” / 肖连珠
- 新课程下的文言文教学现状分析及教学策略 / 桑芝华
- “言”字释义辨析 / 王化斌
- 此情可待成追忆 / 戚光宇
- 游子“床”前月光明 / 杨青舟 吴 婧
- 《送东阳马生序》结构之我见 / 杨景太
- 杨贵妃能不能吃上新鲜荔枝 / 刘小成
- 巧用叠字——《采薇》的独特风景线 / 陈 欣
- 解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五把钥匙 / 肖 武
- 《中国建筑的特征》指瑕 / 陈正春
- 摆正两个关系触动学生情弦 / 周国飞
- 敬畏生命源于惊异 / 杨金平
- 作文应彰显个性色彩 / 缑克喜
- 《使至塞上》一处注释的质疑 / 方勇军
- 关于散文《雪》的开头之我见 / 叶久平
- 《藤野先生》中一处离题的文字 / 黄兴亚 黄兴东
-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 青 秀
- 朴素的开首 真实的魅力 / 李桂萍
- 无缘对面不相逢 / 施孟文
- 学生自主阅卷:提高语文复习训练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 刘国志 宋保万
- 考生读懂题目了吗 / 朱元勇
- 反义合成词的产生原因探析 / 齐红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