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5期
ID: 135820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5期
ID: 135820
一个“作战参谋”的招降信
◇ 何永生
《与陈伯之书》这封战前策反的招降书的高妙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般而论。自在文采。文采当然在必学之列,但以为《与陈伯之书》的力量仅在于文采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一封书信,如缺乏内在玄机的话,纵然文采斐然,也不可能招劲敌来降。何况文采对于真正的文学经典而言,不过就是一个入门的标准。说的诙谐一点,所谓文采就是一种“文字美色。被赞许为有文采,意味着该作者的文字眉眼,长得格外玲珑俊俏,类似语言里的西施潘安”。有些时候,过分的讲究辞采往往会适得其反。因为“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危。则心理愈翳”。
作为一篇阵前策反的实用文书,《与陈伯之书》从文本上值得推崇和学习的。首先还是表现在话语角色的选择和修辞心理的机要上。文采带给我们的观止,是作者戴着镣铐还能舞蹈的惊艳。是一种锦上添花的风雅。
什么是话语角色的选择?就是让谁来说话(写信)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此次行动方案能否奏效的关键,涉及到话语的信度和效度。用一句掉书袋的话来说,话语角色的选择或调整是由修辞行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就一般情况而言,话语角色的选择至少要遵守如此两个原则:第一,交际双方一定存在一种话语角色关系。比如丘迟和陈伯之二人现在分属两个不同的且具有高度利害关系的政治、军事集团。第二,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交际双方只选择一种角色关系。比如,此时此地,丘迟和陈伯之只选择“故旧”这样一种“情义”关系,其它角色暂时隐退。
当然,话语角色一经选定之后。并不是不变的,相反,在修辞过程中必须根据话语动机,不断地进行话语角色的调整。这一点也正是下文要作详细分析的。
修辞行为方式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本次事件中。作为修辞行为的主体丘迟,对自身修辞行为方式的选择主要表现如下。
书信言说方式的选择,有隐蔽。不给对方造成不便的考量,同时又兼顾了“尺牍书疏。千里面目”的亲切,我们今天还有“见信如见人”的说法,在一个重证据的时代,则更是庄重的体现。此外,采用书信的好处主要是真诚,易为对方接受,有思虑酝酿斟酌的空间。
至于在书信形式下,选择骈文的体式,也是颇符合当时书信往来时尚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牍文的发展表现在,“一是它大大地扩大了书牍文的内容。这时出现的书牍,有的论政,有的论学,有的叙交谊,有的述情趣,有的记旅游,有的酬问答,而成为一种广泛的应用文体。二是在书牍文的写作上,极大地加强了艺术色彩,仿佛写信不仅是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还要骋才华。托风采,叫读者欣赏一篇美文。于是书信也就不单纯是一种社会必需的应用文体,而且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成为文学之林的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文学样式”。
正因为是一种文坛、政坛和上流社会的时尚,一种高雅的体现,所以,尽管陈伯之从小就“好著獭皮冠,带刺刀”,即使做了大官,主政一方还是“不识书,及还江州,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从小就不会识字断文,后来当了封疆大吏。于“文牒辞讼”也不过对付而已,完完全全是一介武夫,然而,丘迟还是把一篇《与陈伯之书》作得花团锦簇。想必这既是时尚使然,也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和抬爱,当然也不排除心理优势的展现。事实上如果没有《与陈伯之书》,很难想象,除了文史专家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纷繁复杂的南北朝曾经有一个叫陈伯之的人。俗话讲,江山之美,古来共赏,这共谈与共享,还不是借助了文章。同样的道理,人物春秋,古来共谈,也都沾了文章的光,特别是那些被历朝历代经典化,成为不朽的传世之篇。
丘迟的这封人选《昭明文选》的书信,融私谊与公义、情感与逻辑、体恤与惑窦、怀柔与声斥于一体。不仅喻之以义,示之以势,而且动之以情。义、势、情相辅相成,义正而辞严,势利而娓娓,情挚而理喻。既如此,则言随意转,或鼓动、或宣传、或批驳、或声讨。不仅旗帜鲜明、观点明确、逻辑严谨、论证有力,而且感情真挚,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势胁人,足以引起读信人的强烈共鸣和共识,因而极富鼓动性和感召力。
全篇文字除书信必要的客套话语外,推心置腹,所叙不过“时势”与“英雄”两个内容。究其详略。可概述为“四评”。
一是史评:对于对方历史行为的评价,功过两分,臧否有度,责中有谅,绵里藏针,促使省思。
所谓“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这话一半真,一半假,有赞有弹,所以既是恭维,也是提醒。
这里叙说的是陈伯之第一次归附南梁的事,实际的情形是当时担任南齐江州刺史的陈伯之,在萧衍(粱高祖)率领的军队讨伐南齐时,坐待机变,自己没有组织抵抗,而是一个名叫东昏的将军“借伯之节、督前驱诸军事、豫州刺史”。萧衍以“安东将军、江州刺史”之职诱降陈伯之,“伯之虽受命。犹怀两端”。萧衍认为“其心未定”。于是辅以军事压力逼其就范。归降之后的陈伯之,外托服从之名。内怀犹豫之计,在建康(南京)被萧衍攻破之后,“每降人出,伯之辄唤与耳语”,这使得放心不下他的萧衍更加担心“其复怀翻覆”,于是设计断其后路,死其心。私下里告诉陈伯之:“耳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为虑”。然而,陈伯之仍然不信。萧衍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让一个叫郑伯伦的降将去拜访陈伯之,对他说:“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诱卿以封赏。须卿复降,当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复欲遣刺客杀卿。宜深为备”。至此,“伯之惧,自是无异志矣。力战有功。城平,进号征南将军,封丰城县公,邑二千户”。所以说,这里的话真假互现,有赞有弹,棉里藏着针。“勇冠三军,才为世出”是评赞;“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是为其背叛原主的变节行为贴金,为其变节的行为附上大义的名号;“因机变化,,一句更是一语双关,褒贬之义,全赖读者心得;“遭遇明主”与“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之间暗存明显的前因后果关系,引入深思。这种因果关系,在遭遇了下文的“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的对比之后,更加明显。这种对比在强化了成败荣辱与遭失“明主”的因果关系的同时,还起到了开启读信人弃暗投明的深思,悟生昨是而今非的挫败之感的煽诱作用。
接下来的几句文字几乎是通过预设的反思和忏悔“请君入瓮”。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为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这几句话若译成现代汉语似乎更能理解为责中有谅。推想你投向北魏的当时。没有别的缘故,只不过没有经过反复思考,听信了外界的谣言。沉迷于狂妄强横之中,才搞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一句“非有他故”把陈伯之当初的“反复”就大事化小了,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直……以”(只不过。才)这种旬式和不值一提的语气,更是一种开脱、谅解。甚至是安慰的表述方式。所谓有错不过是欠考虑(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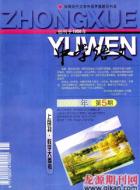
- 走向人文的科学主义与科学的人文主义 / 张悦群 沈文涛
- 关于高考作文错字评分标准的反思 / 杨利景
- 孔子的教育之道(五) / 韦志成
- 还原法:与文本深度对话的智慧 / 胡根林
- 用艺术手法点燃文章的真情 / 梅晓华
- 一种独特的教学风格的存在 / 徐 萍 曹明海
- 议论文怎样展示分析过程 / 刘 惠
- 关于树的诗文赏析(三) / 孙绍振
- “前理解”指导策略之我见 / 赵 婷
- 愚公谷何以及愚溪 / 李震海
- 一个“作战参谋”的招降信 / 何永生
- 语文味的教学生成 / 张从德
- 《琵琶行》中“回”字的确切含义 / 莫丽莎
- 城乡人情冷暖悲悯的见证者 / 章国华
- 静心倾 / 申银群
- 2009年台湾高考国文试题的三大特点 / 王明建
- “闪电”意象与海子的“幸福” / 李兴茂
- 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的实践性结合 / 刘洪丽
- 君子兰的气 / 龙 曾
- 追寻基于文本的作者意义 / 吴诗斌 章浙中
- 有效地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与转化 / 郎慧娣
- 写作的奥秘 / 杨邦俊
- 散文写作中的“造境”与意义拓展 / 刘 祥
- 时文标题有妙用 / 王万忠
- 语文教材中的现代主义文学试解 / 杨红燕
- 语文多媒体教学应突出语文味 / 周显峰
- 初中文言文教学策略探微 / 李 斌
- 如此“开窍” / 张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