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2期
ID: 13574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2期
ID: 135747
教育智慧隐喻箴言
◇ 何永生
说到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智慧,中国有一句格言,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用“树木”来喻“树人”,琢磨起来,多少有点“仿生”的认知意味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从其面世开始就不断地被继承发扬,作为教育理想的旗帜,成为抵御历史上各个时期现实功利教育的盾牌。
如果从语文的角度。对这句话做修辞学上的分析,其解读可能不止一种说法。例如,它是一个对比,通过对比来说明“树人”之不易。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再如,它是一个夸张,理由大概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何来百年成才之说,其言夸饰,以明养成之不易也。这些离开原有语境。对语词孤立的修辞学分析难免牵强,管子的“树人”之说大概旨言教育培养人是一项长远的打算,与“树谷”、“树木”相较,其利长远而获利良多。从教育学的角度解读,恐怕有更深层的意义还可以发掘:它不只是一个修辞上以类相比,将奥义显俗,深义浅出的言语巧饰问题,而是以“人”的成长与“树木”生长的同源性和相似性考察,来隐喻人们对教育规律的一种认知:教育遵循一种自然的规律,任何违拗规律的人为作用,都可能会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上述的一些说法,无论从哪一个具体的修辞视角去观照,都没有排斥隐喻这种修辞手段兼具修辞性与认知性双重身份及转换生成关系的特点,这是隐喻修辞的共性,不单在教育智慧隐喻表述的时候所独具。本篇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语文》教科书中所编选的荀子之《劝学》、柳宗元之《种树郭橐驼传》和龚自珍之《病梅馆记》,分析各自隐喻表述的特点,并总结其蕴含的教育智慧。
这三篇文章进入人教社的教材,分别被编排在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的古诗文单元。从编写安排的顺序可以看出,《劝学》是编选者自觉意识到了其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的隐喻表述,这一点从教材的文本构成不难看出。教材中的《劝学》是编者对荀子“劝学”原章经过了整体解构,然后为我所需。从中撷取了四个段落,重新构建的一篇旨在开蒙学智(弃绝空想。力行力践,循序渐进,宁静专注的修学境界)的励志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全新的“劝学”。这个“劝学”文本所生成或者说所能生成的意义与荀子的“礼论”、“性伪”、“劝学”和“天人之分”一整套严密的思想体系中的“劝学”已全然两样,此其一。其二,教材编写者在课后的“思考与练习”中还专列了一个供学习者在整体阅读和理解基础上,对文章的观点及表述方式、结构层次、立论特点作综合学习、思考和记忆的一个训练。
而柳宗元之《种树郭橐驼传》,由老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思想出发、,提出“顺天致性”不违道的“养人术”,其初衷针对的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和各级官吏政令繁苛,民不堪扰的现实而提出的治事之言。其所言“养人术”并非教育养成之制之法之术。然而,在笔者看来,因同源,事同理,其所言“顺天致性”于教育养成亦切中肯綮,且这样另类解读在文本上的改易也并不复杂。如果将全文卒章显志的最末一段:问者日:“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文中的“官”改为一个“教”字,将文章所言本事一段,即倒数第二段或删除或更易数字(详见下注括号中为更易字词)则言柳文讽喻“教育之失”即全然契合。
至于龚自珍之《病梅馆记》虽然并非针对今之所谓教育而生发议论,而是托梅议政,揭露封建专制制度和病态社会对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的罪恶,表达改革政治和社会,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然而,由于其文托物议事,喻梅言志,所指广泛,百读百解,仁志之见,不限一域,言之教育,更是契合无间。
这三篇文章在笔者看来,不仅都可以作教育和人才培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性培植的思想提炼,具有教育智慧隐喻表述的共同特点,而且让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当我们作这样打破陈规。自组课程资源的时候,出于巧合,这三篇选文分布的时代分别是中国古代的上古时期、中古时期和近古时期,就时间分布而言,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上中晚三个重要的时期。虽然每一作品生成的动机各不相同,从发生的语境而言,也并非专为教育认知而表达,但文本中蕴藏的共同教育思想,为我们把它们作为主题集成的研究性教与学和学以致用的教学个例无疑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从这种偶然中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推测中国古代文献中其实一直贯穿着“教育即生长”的哲学思想和隐喻思维及表述的必然呢?这也是笔者在教学中很感兴趣的,这当然是一个需要小心求证的课题。
三篇文章虽然都自觉运用了隐喻的策略,然而在策略方向的选择上却存在明显差异。
《劝学》采取的隐喻策略可以视为认知的必需,如果从一般修辞学的意义上去评判,其隐喻策略的运用在于构句,而不在于谋篇,更不在于造境。其喻之句可以分门别类为明喻、暗喻和隐喻,作者或者说编者是通过想象的方式将学习这样一种认知的活动比同于日常生产、生活和自然界中的其它事物。并将后者的特性施加于前者。它的隐喻特征明显限于句与句的生成关系,在于内容则表现为本体事物和喻体事物,一一对应(一个本体对应一个喻体),或多质对应(多个喻体对应一个本体),聚集起来形成连喻和博喻。全篇文章基本由隐喻构成。但篇章结构上并不呈现本喻段落对应的比类关系。在篇章段落构成方面仍然是主题内在需要表达或并列或层进的自然演绎。所以,《劝学》中的隐喻可以说既是认知的修辞,也是修辞的认知,如此而已。
《种树郭橐驼传》的隐喻策略则是表现在篇章结构上的努力,这种努力可以看做是出于情感需求而倾向于在不同感觉、经验和认知领域中发现相似之处,而言说自如的需要,是一种说理表达和文篇修辞策略。所以。全文在结构上呈现明显的喻事言说和本事言说对称的特点。这样写作的目的在于彰显言说的亲和力,通过引入异事异见而转入本事事理,将读者或听者引入相似的语境而产生情理上的共鸣,学理上的共识,或事理上的共知。即不是出于言说压抑而采取的迂回策略,而是出于像孔子所谓“群”的目的而做的写作者希望和阅读者达成共同认知的努力。
《病梅馆记》的隐喻策略则完全是出于一种政治修辞的需要,或者说言说安全与自由的需要,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者。这一点只要熟悉清代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史的人,即不难理解作者言事曲折的苦衷。在那样一个言治惨烈的环境下,曾如歌德所言:“谁可以对认识直言无隐?历来有所认识的少数几个人,都太愚蠢而不会明哲保身,向公众公开他们的观察和感情,如果不是受磔刑,就是被焚身。”正是类似于这样一种政治高压、言论管制的环境,使得“龚自珍的诗文‘文词俶诡连犿”,“隐晦曲折,骤读之下,难于索解,须透过文字上的烟幕,寻出‘怨去吹箫,狂来舞剑’的思绪,才能悟出本意来。”龚自珍采取隐喻的策略完全是出于保障写作安全与自由,通过“隐”的手法“彰”显其真义本衷的考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病梅馆记》中只看到对喻事(疗梅)的言说,而不见本事一个字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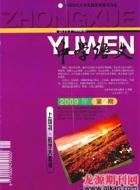
- 语文教育的哲学思考 / 田泽生
- 把好“度”才能摆好波 / 冯碧芬
- 关于《花未眠》的教学构想 / 许红英
- 孔子的教育之道(之二) / 韦志成
- 仙山琼 / 余力文
- 同一文本多元拓展例谈 / 黄群芳
- “民族意识”与“全球视野”的交融 / 徐林祥
- 《安塞腰鼓》的不同解读与教学设计 / 申国君
- “简”而“丰” / 王 芳
-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有效设计的思考 / 杨润芝
- 授之以渔,扶之仗藜 / 付 蓉
- 语文“自主学习”方式的若干思考 / 彭 超 郝 萧
- 编制思想变革下的教材革新 / 孙慧玲
- 以人为本,催生个性化作文之花 / 陈伟秀
- 说说“提问” / 朱宗明
- 用纯美的心去经营“纯美的事业” / 任爱芬 曹明海
- 目前高中作文教学存在的四点问题 / 王乃宁
- 让有效思维漫溢课堂 / 蔡志贤
- 再读唐诗《山行》更疑“晚”字注释 / 王中正
- 教育智慧隐喻箴言 / 何永生
- 中美口语交际课程标准(指南)折射出来的问题 / 李震海
- 休矣,不和谐的话文课堂用语 / 毕泗建
- 教材选文一定要名篇吗? / 王家伦
- 中学教材文言文选词释义二则 / 郭晓红
- “具于五刑”考辨 / 何 伟
- 《鸟啼》的生命意蕴 / 庄平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