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5期
ID: 135821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5期
ID: 135821
语文味的教学生成
◇ 张从德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读书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鲁迅少年读书的“三味书屋”有一副对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读书味美如肉汁太羹,何其妙哉。
然而,读书如果被功利之心困扰,方法不当,寻章摘句老雕虫,美味就变成了苦味。清朝袁枚说:“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遗憾的是,读书不知味,在今天的语文课堂里还大量地存在着,因为我们老师的教学理念中没有“滋味”的位置。单调沉闷的讲解。机械乏味的训练,抛开语言而进行的空洞的人文讨论,割裂语言工具和人文内容的联系,有味的语文享受变成了乏味的言语折磨。提倡语文教学要有“语文味”,源于汉语教学的传统。将语文课上出语文味,这是语文课最基本的要求。
语文味生成于情感,蕴含着情感的滋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刘勰认为文章无情即无味。同样道理,语文课要上出语文味,首先要师生和作者之间心灵共鸣,情意浓烈。缺少激情的语文课虽然没有知识上的错误、结构上的不妥,但是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语文是最富有人性美和人情味的学科,课本中的所有课文,包括议论文和说明文。都渗透着作者的爱憎情感和审美态度,找准课文的情感点,是教出情感的基础。语文教师对每一篇课文都要情深似海。大力倡导语文味教学的华南师大兼职教授、深圳教研员程少堂先生说:“如果把上课比做结婚,把培养感情比做恋爱,那么教师对自己不喜欢的课文不能先结婚后恋爱,而应先恋爱后结婚。只有这样,教师才能教得神采飞扬,学生才能学得兴致高昂。”当然,培养情感不能毫无节制,不能矫揉造作,而应不温不火,张弛有度,含蓄奔放,阴阳协调。充满激情的语文课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读书读到动情处,“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情感如涓涓细流注入学生的心田:魏巍的老师蔡芸芝“爱用歌唱的音调教我们读诗”,学生觉得她是最美的老师;韩麦尔先生上最后一课,“连声音都发抖了”。给学生以终生难忘的印象。
语文味生成于美感。蕴含着超越功利的审美滋味。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释名》解释“文”字:“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文”的本义是华美的图式,引申为华美的文采。汉代夏侯湛在纪念张衡的《张平子碑文》中,评价张衡的《二京赋》《南都赋》:“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欤”。所谓“有味”就是语言优美如花,内蕴典雅如诗。语文学习的过程也是审美的过程。用审美的角度去学习语文,就不能停留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而是要上升到精神陶冶、审美体验的高度,使学生在审美王国和诗意世界中体悟自然之美,人物之美,科学之美,语言之美。选人课本的文章都是典范的作品,它们在教学上的审美价值是通过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帮助学生掌握美丽的表达和美丽的创造的本领。审美性是语文教育艺术的源头活水和最高境界,它隐含在语言的深层结构里,需要师生经过敏锐的感知、丰富的想象、切身的体悟、精心的鉴赏才能发掘出来。由于它的内隐性、模糊性、复杂多元性,在实际教学中常因不易操作而被忽略,因此,提倡审美滋味是有现实意义的。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诗意的人生追求越来越稀薄,加强审美教育,有助于拓展学生心灵的审美空间,为他们一生打下精神的底子。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腹有诗书气自华”,中国古代的语文教学讲究培养学生的君子风度,圣贤气质,正是利用读书美容的道理,通过审美教育改变人的气质。曾国藩诫子说:“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语文味生成于文化。蕴含着文化的滋味。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还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它和语文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文化背景下开展的语文教学,着意对学生的精神世界进行文化的塑造。语文课程既要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言技能,也肩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在语文实践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对语言的运用。都是在特定情境中的文化行为。既是内含了文化主体价值判断和文化观念的言语实践,也是把外在的客体文化内化为学生心灵的积淀过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文明化。语文这一古老的学科,是与中国文化一道成长的。我国的传统教育一直以文化为核心。《易经》上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文明的极致,关注入文在于洞察人性,根据人性法则去建设和谐的社会,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之魂。
庄子说“道也,进乎技矣!”文化就是语文的“道”。文化语文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从文化视角找准切入点,挖掘拓展课文中的文化意蕴。传承弘扬课文中的文化思想。文化课程追求文化意义的创生。而不是对外在文化的盲从。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任何文本都是一个开放性的创生体,蕴含着多元意义建构的可能,由于知识、经验、视角、目的等不同,课程文本呈现出多元的理解,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和批判的意识。比如教学《愚公移山》,有学生不理解为什么愚公搬山而不搬家。从寓言文体的角度去解释,寓言多用夸张的手法,荒诞的情节,寄寓深刻的主题。《愚公移山》的寓意在于呼唤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而搬家则与文本的思路相悖。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因为黄河流域地处北温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愚公不愿搬家,正表明我们的祖先对哺育自己的家乡的热爱,也表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留恋故土、安土重迁的心理。语文课要上出文化味,首先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带领学生在语言的海洋里捡拾智慧的贝壳。从文化的角度教学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每个人都有听雨的经历,但这里的听雨却富有丰富而多样的文化意蕴,它似乎是人生所经历的错综复杂的文化风云的高度凝缩,少年时在歌楼的灯红酒绿中消磨时光,壮年漂泊于客舟旅社,老年时孤居于僧庐下。这些形象化的描写生动地勾勒出个人生活的文化曲线,不亚于一篇富有修辞效果的人生劝导书,品味此词,不一定要追究它所寓言式地描绘社会文化状况,而完全可以在三幅想象的场景中驰骋情怀,领悟到人生体验的深长意味。程少堂用另一种眼光读孙犁,从《荷花淀》看中国文化,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的考察,发现中国文化的中和之美,它的基本思想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使之处于协调状态,教人学会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这堂课打通了文史哲的联系,从大文化的视角引发学生的思考,开辟出一片令人耳目一新的语文新天地,至今仍被人认为是语文味教学的经典。文化语文的建构要避免空洞无物,就要以语言感受为基础,使学生在文本体验中领会语言精华的同时。汲取文化的营养。有深厚文化内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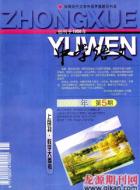
- 走向人文的科学主义与科学的人文主义 / 张悦群 沈文涛
- 关于高考作文错字评分标准的反思 / 杨利景
- 孔子的教育之道(五) / 韦志成
- 还原法:与文本深度对话的智慧 / 胡根林
- 用艺术手法点燃文章的真情 / 梅晓华
- 一种独特的教学风格的存在 / 徐 萍 曹明海
- 议论文怎样展示分析过程 / 刘 惠
- 关于树的诗文赏析(三) / 孙绍振
- “前理解”指导策略之我见 / 赵 婷
- 愚公谷何以及愚溪 / 李震海
- 一个“作战参谋”的招降信 / 何永生
- 语文味的教学生成 / 张从德
- 《琵琶行》中“回”字的确切含义 / 莫丽莎
- 城乡人情冷暖悲悯的见证者 / 章国华
- 静心倾 / 申银群
- 2009年台湾高考国文试题的三大特点 / 王明建
- “闪电”意象与海子的“幸福” / 李兴茂
- 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的实践性结合 / 刘洪丽
- 君子兰的气 / 龙 曾
- 追寻基于文本的作者意义 / 吴诗斌 章浙中
- 有效地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与转化 / 郎慧娣
- 写作的奥秘 / 杨邦俊
- 散文写作中的“造境”与意义拓展 / 刘 祥
- 时文标题有妙用 / 王万忠
- 语文教材中的现代主义文学试解 / 杨红燕
- 语文多媒体教学应突出语文味 / 周显峰
- 初中文言文教学策略探微 / 李 斌
- 如此“开窍” / 张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