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1期
ID: 35637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1期
ID: 356377
古典人格观照下的烛之武
◇ 何永生
上古中国哲人造就理想人格的标准,仅从孔孟到汉儒这一学源来说,虽有损益,但核心的价值标准除了更见丰富和完善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孔子有三达德:智、仁、勇;孟子有四端:仁、义、礼、智;汉儒又有五常:仁、义、礼、智、信。”①烛之武退秦师事发公元前630年,孔子生活于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两者相距一个世纪,用后者的理想人格标准来评说前者的人格形象是否可行呢?我以为是没有问题的。理由之一是,在上古时代,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先于理论抽象的,人格行为与人格理想的关系也不例外;二是在《烛之武退秦师》中所反应出来人格标准已与孔子的三达德相去不远。文章的结尾,事件的结束,就是以晋公的一番高调的人格表白收场的:“因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借助人家的力量又去伤害他,是不仁德;失去同盟者,是不智慧;用自相冲突去改变一致的步调,是不勇武)。如果说晋公的表白不过是一种标榜的话,那烛之武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一种人格理想。理想人格总是具有超越性的,具有理想人格的人也常常具有属于未来的特点。于是,我想到了用孔子评价人的标准来观照烛之武的问题。如果说这样立论还属于大胆假设的话,那就不妨来小心求证吧。
先从“智”的方面来看吧。孔子说,“智者不惑”,这是很高的境界。“惑”就是糊涂,“不惑”就是不糊涂。人犯糊涂要么是遇到了与自己利害密切的问题,身陷其中而当局者迷;要么是事情复杂到了超出了自身生活经验和智慧。看来犯糊涂的不是价值失衡,就是能力不济。智者不易,也不多。烛之武的“智”恰恰表现在,一能超过个人的利害得失,二有判断非常是非和驾御复杂局面的能力。
烛之武先拒绝出使秦国,游说秦君的理由是“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这自然是对郑文公不能知人善任的批评,对自己一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怨愤之语,不平之言。按照人常事理,拒不从命于情于理也无大碍,然而,在郑文公一番“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的歉言和“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的利害之理之后,烛之武终于超越个人的委屈,答应郑君。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在关键的时候懂得孰轻孰重的人,无疑是一个智者。
烛之武的“智”还表现在对当时诸侯各国形势的准确把握上:大国争霸,身处大国之间的小国,常常成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夹缝中求生存,要么依附大国强国,寻求保护;要么严守中立,互不得罪;要么两面讨好。然而实际的情形很可能是结盟常常招致别的大国或所依附国敌国的攻击,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骑墙往往弄成骑虎难下;两面讨好两面受罪。事实上,郑文公正是因为“贰于楚”才招致了“晋侯,秦伯围郑”。
烛之武的智慧表现在反其道而行之,巧妙地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瓦解其联盟,说退秦国围郑之师,使国家幸免于难。
烛之武离间秦晋联盟的方法就是罗陈秦晋矛盾的历史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分析扩大矛盾,激将秦伯,促使作出“正确”的选择:是继续联晋攻郑,还是班师回国。烛之武成功了。
再说“仁”。在说烛之武人格因素中“仁”的一面之前,我们不妨就“仁”这样的一个人格标准作一番梳理,这当然是为了证明烛之武是否是一个“仁人”。“仁”是《论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概念,共计105次。孔门弟子向老师求教其内涵的也特别多,孔子赋予“仁”的内涵也特别丰富。丰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含混,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其作为普通的价值标准却并不因其含混失却其最本质的意义,即“它是基本的,普遍性的,并且是一切具体美德的根源。”②冯友兰先生认为是“为仁的人,所必须有的素质”。他进一步解释说:“孔丘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有真情实感。……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巧言令色,鲜也仁’(《学而》)的人和‘巧言令色’的人,成为鲜明的对比。前者是以自己为主,凭着自己的真性情、真情实感做事的老老实实的人。后者是以别人为主,做事说话,专以讨别人喜欢的虚伪的人。……‘仁’的基础是人的真性情,真情实感。”③
按照这样一个对“仁”的认知前提,反观烛之武的为人,则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愧于“仁”的人。一个人既有志于政治,对国际国内形势了然于心又完全符合现实,其见识和能力远高于一般人,然而,在“世卿世禄”这种保守的人才体制下,却没有用武之地,看看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自己却只能容志林泉,凡有血性者于心不甘,于愤难平,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不平则鸣,自然之理,所以当郑国面临大国加兵,“秦晋围之”的危难关头,佚之狐荐举烛之武,纾解国难的时候,面对郑君的求助,烛之武恃才傲物,满口牢骚,发泄不平之气:“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已也!”这一番怨语,不正是一个人真性情的流露吗?
当然,如果烛之武仅止于敢于流露真性情的话,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率真之人罢了,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并不乏率真之人,有谁仅凭一腔怨气而彪炳史册的呢?看来一味地率真,还算不上“仁”,算不上“仁”,那算什么呢?总得有个说法。算“直”,就是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说到过的“直”,“人之生也直”。从自我出发,凭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看来“直人”和“仁人”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做人固然要“直”,不可虚伪,这是“仁”的基础,但成“仁”的标准更高。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其实这句被广泛引证的箴言,并非始出孔子之口,《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的详情是:“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志”,记载的意思。看来一个人的人格,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以个体为单位呈现的,其实它总是包含了其他许多非个人的东西的,比如:社会组织、社会的制度、社会的秩序、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等。这一切在当时统归之曰“礼”。一个人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感情和情绪,又能克制它,使之服从集体和国家的需要,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仁人”。烛之武不仅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人生际遇,率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在郑君“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的义利晓导下,慨然捐弃前嫌,“许之”,国家大义和自己的长远福祉克服了自己的委屈心理,是所谓“克己复礼”。
所以,历史要给烛之武一个“仁人”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左传·僖公三十年》记载了公元前630年郑国、秦国和晋国三个国家之间的一场引而未发的战争,在记史叙事中突显了烛之武这个英雄的形象。
再说烛之武的“勇”。孔子说:“勇者不惧。”什么是“勇”?“勇是冲破障碍克服困难的能力。”③是一个英雄不可或缺的人格素质,因而,培养勇气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孟子讲“吾养吾浩然之气”。养气,就是养勇,就是通过修养培育刚毅不屈的精神。烛之武的“勇”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挫折中求生存已属不易,在挫折中不放弃为实现理想而追求,勇毅更是不可或缺的。烛之武在出使秦国之前,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砺,文本没有提及,但从面对郑君的一席牢骚“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矣”,不难猜测的是智无处申,力无处用的压抑,而终于老而有用,在不得志的人生中没有放弃对实现理想的追求,“有高深修养的人,才能始终一贯地大义凛然,勇于赴义”。一遇打击就退缩的人,必定一事无成,此其一也。
其二,如果说面对郑君勇于直言,是出于一腔积怨,性情使然的话,那么出使秦营,面对秦君则是非大勇所能济事也,这种大勇表现在对秦郑晋三国形势的正确判断、深刻把握,而且表现在肩负国使之责,受命危难,不卑不亢,坚守立场,捍卫国家利益,不辱使命。
上古中国哲人造就理想人格的标准,仅从孔孟到汉儒这一学源来说,虽有损益,但核心的价值标准除了更见丰富和完善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孔子有三达德:智、仁、勇;孟子有四端:仁、义、礼、智;汉儒又有五常:仁、义、礼、智、信。”①烛之武退秦师事发公元前630年,孔子生活于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两者相距一个世纪,用后者的理想人格标准来评说前者的人格形象是否可行呢?我以为是没有问题的。理由之一是,在上古时代,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先于理论抽象的,人格行为与人格理想的关系也不例外;二是在《烛之武退秦师》中所反应出来人格标准已与孔子的三达德相去不远。文章的结尾,事件的结束,就是以晋公的一番高调的人格表白收场的:“因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借助人家的力量又去伤害他,是不仁德;失去同盟者,是不智慧;用自相冲突去改变一致的步调,是不勇武)。如果说晋公的表白不过是一种标榜的话,那烛之武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一种人格理想。理想人格总是具有超越性的,具有理想人格的人也常常具有属于未来的特点。于是,我想到了用孔子评价人的标准来观照烛之武的问题。如果说这样立论还属于大胆假设的话,那就不妨来小心求证吧。
先从“智”的方面来看吧。孔子说,“智者不惑”,这是很高的境界。“惑”就是糊涂,“不惑”就是不糊涂。人犯糊涂要么是遇到了与自己利害密切的问题,身陷其中而当局者迷;要么是事情复杂到了超出了自身生活经验和智慧。看来犯糊涂的不是价值失衡,就是能力不济。智者不易,也不多。烛之武的“智”恰恰表现在,一能超过个人的利害得失,二有判断非常是非和驾御复杂局面的能力。
烛之武先拒绝出使秦国,游说秦君的理由是“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这自然是对郑文公不能知人善任的批评,对自己一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怨愤之语,不平之言。按照人常事理,拒不从命于情于理也无大碍,然而,在郑文公一番“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的歉言和“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的利害之理之后,烛之武终于超越个人的委屈,答应郑君。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在关键的时候懂得孰轻孰重的人,无疑是一个智者。
烛之武的“智”还表现在对当时诸侯各国形势的准确把握上:大国争霸,身处大国之间的小国,常常成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夹缝中求生存,要么依附大国强国,寻求保护;要么严守中立,互不得罪;要么两面讨好。然而实际的情形很可能是结盟常常招致别的大国或所依附国敌国的攻击,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骑墙往往弄成骑虎难下;两面讨好两面受罪。事实上,郑文公正是因为“贰于楚”才招致了“晋侯,秦伯围郑”。
烛之武的智慧表现在反其道而行之,巧妙地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瓦解其联盟,说退秦国围郑之师,使国家幸免于难。
烛之武离间秦晋联盟的方法就是罗陈秦晋矛盾的历史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分析扩大矛盾,激将秦伯,促使作出“正确”的选择:是继续联晋攻郑,还是班师回国。烛之武成功了。
再说“仁”。在说烛之武人格因素中“仁”的一面之前,我们不妨就“仁”这样的一个人格标准作一番梳理,这当然是为了证明烛之武是否是一个“仁人”。“仁”是《论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概念,共计105次。孔门弟子向老师求教其内涵的也特别多,孔子赋予“仁”的内涵也特别丰富。丰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含混,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其作为普通的价值标准却并不因其含混失却其最本质的意义,即“它是基本的,普遍性的,并且是一切具体美德的根源。”②冯友兰先生认为是“为仁的人,所必须有的素质”。他进一步解释说:“孔丘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有真情实感。……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巧言令色,鲜也仁’(《学而》)的人和‘巧言令色’的人,成为鲜明的对比。前者是以自己为主,凭着自己的真性情、真情实感做事的老老实实的人。后者是以别人为主,做事说话,专以讨别人喜欢的虚伪的人。……‘仁’的基础是人的真性情,真情实感。”③
按照这样一个对“仁”的认知前提,反观烛之武的为人,则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愧于“仁”的人。一个人既有志于政治,对国际国内形势了然于心又完全符合现实,其见识和能力远高于一般人,然而,在“世卿世禄”这种保守的人才体制下,却没有用武之地,看看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自己却只能容志林泉,凡有血性者于心不甘,于愤难平,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不平则鸣,自然之理,所以当郑国面临大国加兵,“秦晋围之”的危难关头,佚之狐荐举烛之武,纾解国难的时候,面对郑君的求助,烛之武恃才傲物,满口牢骚,发泄不平之气:“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已也!”这一番怨语,不正是一个人真性情的流露吗?
当然,如果烛之武仅止于敢于流露真性情的话,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率真之人罢了,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并不乏率真之人,有谁仅凭一腔怨气而彪炳史册的呢?看来一味地率真,还算不上“仁”,算不上“仁”,那算什么呢?总得有个说法。算“直”,就是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说到过的“直”,“人之生也直”。从自我出发,凭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看来“直人”和“仁人”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做人固然要“直”,不可虚伪,这是“仁”的基础,但成“仁”的标准更高。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其实这句被广泛引证的箴言,并非始出孔子之口,《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的详情是:“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志”,记载的意思。看来一个人的人格,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以个体为单位呈现的,其实它总是包含了其他许多非个人的东西的,比如:社会组织、社会的制度、社会的秩序、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等。这一切在当时统归之曰“礼”。一个人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感情和情绪,又能克制它,使之服从集体和国家的需要,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仁人”。烛之武不仅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人生际遇,率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在郑君“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的义利晓导下,慨然捐弃前嫌,“许之”,国家大义和自己的长远福祉克服了自己的委屈心理,是所谓“克己复礼”。
所以,历史要给烛之武一个“仁人”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左传·僖公三十年》记载了公元前630年郑国、秦国和晋国三个国家之间的一场引而未发的战争,在记史叙事中突显了烛之武这个英雄的形象。
再说烛之武的“勇”。孔子说:“勇者不惧。”什么是“勇”?“勇是冲破障碍克服困难的能力。”③是一个英雄不可或缺的人格素质,因而,培养勇气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孟子讲“吾养吾浩然之气”。养气,就是养勇,就是通过修养培育刚毅不屈的精神。烛之武的“勇”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挫折中求生存已属不易,在挫折中不放弃为实现理想而追求,勇毅更是不可或缺的。烛之武在出使秦国之前,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砺,文本没有提及,但从面对郑君的一席牢骚“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矣”,不难猜测的是智无处申,力无处用的压抑,而终于老而有用,在不得志的人生中没有放弃对实现理想的追求,“有高深修养的人,才能始终一贯地大义凛然,勇于赴义”。一遇打击就退缩的人,必定一事无成,此其一也。
其二,如果说面对郑君勇于直言,是出于一腔积怨,性情使然的话,那么出使秦营,面对秦君则是非大勇所能济事也,这种大勇表现在对秦郑晋三国形势的正确判断、深刻把握,而且表现在肩负国使之责,受命危难,不卑不亢,坚守立场,捍卫国家利益,不辱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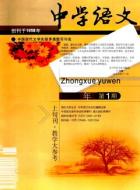
- 回眸与展望 / 陈 枫
- 在叶圣陶经典题词的辉映下 / 王松泉
- 往事如歌 / 江 柳
- 关于《中学语文》的二三事 / 邓先正
-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 韦志成
- 我与《中学语文》 / 洪镇涛
- 钦敬您,我的良师 / 申富南
- 《七律》三则 / 朱祖延 邓先正 周庆元
- 在理论前沿的大开拓与新建构 / 钟启泉
- 文言文怎么教? / 陈隆升
- 语文教育个性化 / 刘笑每
- 语文知识“系统”之辨正 / 许 锃 许晓蕾
- 体验式教学的有效策略 / 汤 蒙
- 谈文章知识对于阅读和写作的价值 / 李正存
- 口语交际教学亟待构建科学的原则体系 / 李子华
- 在何处搭建对话平台 / 彭春炜
- 人文关照下语文课堂教学的误区及对策探讨 / 颜 丹 王家伦
- 《沁园春·长沙》教学随笔三则 / 张 沛
- 揭开话题作文的神秘面纱 / 单云军 殷吉玲
- 关注社会人生,培养思维品质 / 尹小春
- 走进新材料作文 / 冯永忠
- 古典人格观照下的烛之武 / 何永生
- 心灵的一次嬗变 / 章国华
- 一次失约的约会 / 薛保升
- 精彩,不期而至 / 赵清林
- 敬畏语文 / 陈 跃
- 少点架空的分 / 胡继明
- 让诗情画意回归语文课堂 / 冷丽娟
- 略谈对王勃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首联的理解 / 韦树新
- 析《庄子·秋水》注释三误 / 谢序华
- 综述类文章阅读备考指导 / 孟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