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5期
ID: 356124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5期
ID: 356124
语言品味探赜二题
◇ 邓嗣明
语文教学的本质是让学生学习语言,因为课文文本的载体是语言。只有把握语言,才能对文本内涵作出审美评价。同时,积累语言材料,熟练地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是学习语言的重要任务之一。所以,语言品味,乃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
审美是什么?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情感的价值评价。而语言品味,就其性质而言,就是着重诗意的发现、情感的评价,着重读者的性情陶冶、精神感动,以获得高层次的审美享受。
对于文本的解读,尽管中国和西方都强调通过阅读理解获得美感,但西方的分析法只承认美感和视觉、听觉的联系;中国的品味,则不但承认美感和视觉、听觉的联系,而且也承认美感与味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学人谈到阅读中所获得的美感时,总是用味作为评价标准。诸如“品味”、“体味”、“咀味”、“寻味”、“玩味”等,正是古代中国人在阅读中把玩作品的具体方式。一旦发现精品,则被视为“真味”、“清味”、“意味”、“深味”、“美味”等,而档次较低的作品,则成“乏味”、“寡味”、“少味”等。中国人的这种审美胸襟,来自对事物认识的体知,即把外在之物纳入自家生命之中,使其和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用心灵去体验外物。这样,最后的结果不是从多象中获得资料,进行推理,作出客观判断,而是反求诸己,即看自己是否具有纯净的胸襟。那么,对于语言内蕴怎样体知,我以为其法有二:
其一,品味语言,须把语句放到整篇的语境中涵泳,整体把握玩味。
我国古代学者力主对语言的整体感知,反对摘句似的品鉴作品。宋魏庆之说:“看诗不须着意到里面分解,但是平平涵泳自好。”意思是说,读诗不能只是作语词的分解,而应是整体感悟,这才符合涵泳特点。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说:“论曲,当看其全体力量如何,不得以一二句偶合,……遂执以概其高下。”就是说,摘句评诗的高下是不合理的,要看“全体力量”,所谓“涵泳”,就是要有这种整体的眼光,只有整体涵泳亦即整体品味语言,才能理清思路,把握主旨,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比如下面一些句子:
①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
——宗璞《紫藤萝瀑布》
②而我们居然站在这儿,站在这双线道的马路边,这无疑是一种堕落。
——张晓风《行道树》
③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句①中“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把味觉诉诸视觉,一时难以理解。仅仅把它说成是通感,其理解仍然是浅层的。只有把它放到整篇中去品味,才能悟到一种充满生命张力的萌动,一种生命光彩的闪烁,或者是一种对生死谜、手足情的顿悟。而句②中的“堕落”,在整篇的品味中,它已经不是“往坏里变”的词典意义,而是“行道树”成为自我奉献者的高尚形象。句③中的“怀恋”,在整篇中亦无恋旧的“怀念”之思,而却是“永远向着未来”的欣然回想。
总之,语言品味应是以林泉之心去面对文章的整体,反复持久地诵读,深入地感悟艺术世界,诗意地体认其滋味,最终获得审美的感动和精神的升华。
其二,语言品味,应将“言内”之语拓展出“言外”之意,领悟其表情达意的美质。
古代中国文人极为看重“言外之意”或“意在言外”的语言策略。
那么,怎样品出语言的言外之意呢?我以为可从两方面入手:
(1)必须对言内与言外,象内与象外,韵内与韵外的关系作辩证性理解。唐人司空图认为,要品出语言的意在言外、象在象外、韵在韵外,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好“言内”、“象内”、“韵内”的意蕴。为此,他提出了两点看法:一要做到“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韵外之效耳”。“近”就是“言内”、“象内”、“韵内”的意象,对此意象,在品赏时应尽量诉诸想象,几近作者所描绘的意绪与物象,直到能置于眉睫之前,在“近”的物象达到“不浮”而鲜明的情况下,那么“远”的(即“言外”、“象外”、“韵外”)意味,也自然就会味之“不尽”。二是“……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以全美为工”,即能尽味语言表现之美,包括词语所营构的形象、主旨等类,只要实现“全美”,“摘尽枇杷一树金”,则“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就自然显现了。比如,冯骥才《珍珠鸟》中的一段:
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验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嚓嚓”响。
作家将浓郁的温爱情感融注到对珍珠鸟动作的状写,如落花依草,点缀映媚,给人以很高的审美享受。文中把人的性灵赋予珍珠鸟,不露痕迹,明丽天然,竟使珍珠鸟似乎也有了人的神情与心理。特别是动词“挨近”、“蹦”、“俯下”、“喝”、“偏”、“瞧瞧”、“跑到”、“绕”、“蹦来蹦去”的传神如睹,已经远远超越它本身的语词义而显现出“韵外之致”,作家越过写鸟的笔致,而活画出一个天真、稚拙而又聪慧灵动的顽童形象。空灵而富真趣,确有“夕阳连雨足,中翠落庭阴”的审美意味。
(2)先将“言内”之意具体解读,品出“实象”;然后驱遣想象,把语词之意扩展至“言外”的“虚像”,达到深层理解的审美效果。
宋人梅圣俞尝言:“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梅圣俞的话是就创作而言,他强调的是“意新语工”,“意新”除了主旨、立意新颖之外,还应指意蕴多维,亦即内蕴多层性;而“语工”则是内蕴多层面的载体——语词所具有的内蕴与美质。解读时,应抓住这些语词,去品赏它的象外之韵。比如宗璞的《紫藤萝瀑布》中的一段: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
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
这段文字曾为美学家们所激赏!
为什么?就因为它“意新语工”,为前人所未道。它的妙处正在于从“每一穗花”到“每一朵盛开的花”的实景中孕化出的无尽之意,言外包容着作家乍喜还忧的浓浓深情。在这段文字里,作家用帆和船舱作比喻,生动地显现出紫藤花盛开的状态,花光闪烁,生机盎然,这是“实象”。同时,作家又将花人格化,“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这样,不仅花袅娜可爱,而且作家隐藏在花朵中的喜悦之情亦跃然纸上,这是“虚象”。如溪流,如短笛,清幽婉转,滋味近似;又如置身郊野,一股清新之气直扑人的眉宇。
[作者通联:湖北荆州沙市教研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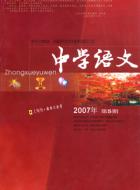
- 语文课程改革的脊梁 / 韦志成
- 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略论 / 陈菊先
- 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高峰论坛综述 / 陈 枫 张萌萌
- “余映潮语文教育研究”研讨会在荆州市隆重举行 / 王世发
- 幸福 欣慰 感谢 / 余映潮
- 想起余映潮老师 / 王 君
- 不言春作苦 常恐负所怀 / 李昌林
-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 张安群
- 诵读、积累、实效——板块式教学设计的三个基点 / 张慧莲
- 论余映潮先生教学艺术的文化品位 / 陈光浩 林富琴
- 新课改背景下语文教学流弊批判 / 石子林
- 语文阅读教学的“边角” / 杨树亮
- 从作品解读中开启学生的善良和悲悯情怀 / 王木清
- 语言品味探赜二题 / 邓嗣明
- 小步轻迈细品读 / 任明新
- 发掘隐含信息:作文审题教学的重要环节 / 陈锦山
- 精彩不仅是他们的 / 唐香萍
- 文本、写作与开放的语文课堂 / 王莉华
- 寻求心灵的自适,被动于山水的皈依 / 樊 华
- 彤管:解读《静女》的钥匙 / 陆精康
- “精彩”之后的反思 / 花海棠
- 让学生在读中享受乐趣 / 刘 丹
- 巧设问 / 段艳敏
- 看似寻常最崎崛 / 陈淼星
- 衬托,还是烘托 / 张淑君
- 新课程改革中新问题的思考 / 丁宏伟 李艳萍
- “高枕”何以“无忧” / 刘 念
- 一“句”一“逗”尽风流 / 郑可菜
- “宴酣之乐”献疑 / 邹 贞
- 贡,求也 / 叶章维
- 李儋元锡是一人还是两人? / 陆 瑢
- “膑脚”“断足”语焉不详 / 孙 云
- 循理以求 / 朱庆和
- 材料设计二则及写作思路详解 / 张志先
- “文学名著阅读”新题备考策略 / 程必荣
- 联合短语在病句中的病情透视 / 周加银
- 海外语文练习的基本特点 / 张悦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