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5期
ID: 35611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5期
ID: 356112
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略论
◇ 陈菊先
大家都知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理论又来源于实践,这就需要人们在生活中有两种眼光,即感性的和理性的眼光。语文教育发展同样需要这种视野。从语文独立设科至今,百多年来,语文发展一直以感性的和理性的眼光,走在法规层面、实践实验层面和理论层面的建设上。理论虽然抽象,但它来自实践的总结,理论的认定和修改也来自对具体实例的分析,泛泛而谈的理论是空洞的。语文教师如果具有这两种眼光,他将是教育工作的创新者。
语文教育是一个类概念,语文教育理论就是研究语文教育原理性的问题,它必须是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的。下面,随机选取三个实验个案,具体看看语文教育理论和语文教育实践是如何相生相长的。
一、廖世承教育科学实验
廖世承(1892年6月——1970年10月),我国近代教育实验的开拓者,著名现代教育家、心理学家。他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在勃朗大学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扎根教育51年中,几乎都是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既是大学校长,又是附中校长;既是大学教授,又是附中教育实验的主持者。在大学,他教授中等教育、教育心理学、测验与统计等课程,在中学他先后以三个附中——东南大学附中、光华大学附中、国立师范学院附中为实验与实践的基地,在理论文本与实验实践互动中,结合国情进行了一系列中等教育的改革实验,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影响深远的辉煌篇章。
20世纪20年代的学制改革中,东大附中的“三三”制实验以其开创性和实效性影响于世。实验在全面发展教育理念下,将宏观的体制改革与微观领域的改革联系起来,使课程教材成为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课程设置以“合于升学,合于谋生,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课程结构新颖,实行分科制,设职业科与普通科。课程形态丰富,改单科制为选科制(读毕了必修科,可以选读选修课)。教材切近生活,以应用为归。课程评价利于学生发展,破除学年制,以能力分组,采用学科升班,实行学分制(学生读毕了学分,达到了主要科目的最低限度,就给毕业)。毕业年限有两年的弹性(或五年毕业,或七年毕业)。课程活动中实行指导制,学生受益与个人指导,选课指导,教育指导,职业指导,培养了选择能力和发现自我的能力。实验在鉴别个性、适应个性、时间经济、增加教育效率、增加中学人数、衔接密切等方面成效卓著。光华大学附中通过实验成了全国的模范中学。国师附中应抗战急需,实验“五年一贯制”,其效果是殊途同归,成为培养优秀师资的摇篮。
20世纪20年代,测验处于草创阶段。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开设《测验课程》,成为我国正式应用心理科学测验的开始。在儿童心理测验和汉字研究的基础上,他俩合著,1921年出版《智力测验法》,1925年出版《测验概要》,推动了测验的科学化和本土化的研究。他创立的“廖氏的团体测验”享誉国内外。
国文改革很超前,认为社会的组织愈复杂,人群的交际愈密切,用“口”发表的机会也愈多。为此,国文教师可使学生在班上演说,练习口头发表,或在台上表演。除了书本以外,还要通过团体的课外活动为学生打下“立身行事”的基础,尽“教”的工夫,尽“育”的责任。开展辩论会,练敏捷,练社交。其正方和反方的辩论方法延续至今,三角式的辩论方法可供今天借鉴。办周刊与国文科结合,使周刊成为学生练习用文字发表思想的阵地,成为形成良好校风的喉舌。自编的刊物多种,皆为课余之练习。举行全校国语比赛。组织文学研究会、戏曲研究会。话剧在学校占有重要地位,认为话剧可以补助语文的练习,增加个人的经费,可以联络各科的教材。对话剧研究社的活动,师生兴趣素来不坏。
二、道尔顿制实验室计划
道尔顿制,1922年传入中国,中国公学附设吴凇中学舒新城于当年10月在国文及社会常识两科率先试验此制。《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先后推出《道尔顿制专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定试验此制,试验学校达百余所。试验的5年间,发展呈波浪起伏状,1926年后,终因财力和师资的滞后,仅有个别学校坚持实验。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具有精密研究的价值。
道尔顿制实验室计划,简称道尔顿制,是教学的一种组织形式和方法,为美国柏克赫斯特所创建。她以美国的道尔顿城一中学命名。该实验大体运用了蒙台梭利和杜威的教育理论。实验的目的是改善学校生活,使各类学生有均等的机会发展个性。它的原则是自由;学校即社会;知而后行。如此以儿童为本位,意在使学生对教育负担责任,感觉兴味。实施中,教室改作实验室。实验室就是知识的工作场,即生活场。实验室有“月约”、“周约”、“日约”三种“公约”:“月约”,给学生以概略的观念;“周约”,给学生博采旁收那些造成这个中心观念的种种材料;学生按前两“约”在实验室作业,作业时间、速率自行酌定。“日约”则是为养成学生责任心、自动力而填写的学习情况表格。师生为师友关系,教师为指导员,指导路程,定走法,让学生自己去走,助其成功进步。成绩考查以“公约”为标准。
在中国该制国文科试验中,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东大附中、北京艺文中学创举空前。代表人物中,除著述甚丰的舒新城外,穆济波、沈仲九、孙俍工,在创造的层面上,与朱自清的“国文科行道尔顿制应该比现行制好”的预见相回应。如穆氏的初二上实验室,作业种类有精读之书、笔记、作文、课堂研究和课外阅读。全学期总计,要精读10万字,笔记至少16则(参考不计),作文8篇,课堂研究40小时,课外阅读3种。孙氏还创造了文艺文作业法:分篇、家别、国别、分组四种作业法。对此制的研究,朱光潜认为课室生活和书本生活在道尔顿制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如果打破这两种生活,将学校生活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把设计教学法的这一目的兼容进来,此制则可锦上添花。正是如此创造性地运用道尔顿制中“自己研究”、“个别学习”的精髓,并以实验的结果随时修改此制,使之合语文特点,合国情的实验方向,使此制的实验价值,更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
上述道尔顿制的精髓与时俱进,它对弥补班级制的不足,丰富班级制的教学形式,促进个别教学在终身教育和素质教育以及全球化语境中的新发展,都有借鉴意义。历史上的程序教学、图书馆教育、函授教育、成人教育;现今的开放学校、远程教育、网络学校;语文教育中的语文自学辅导实验、语文能力三年过关实验、语文自学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实验,以及语文研究性学习实验,特别是高密一中“语文实验室计划”,他们都是明证。高密一中“语文实验室计划”始于1995年秋,是一种全方位的教学改革,它在无可借鉴的基础上起步,为突出其实验性,故称之为“语文实验室计划”。然而,它的精华和运行方法几乎和美国的“道尔顿制实验室计划”不谋而合,它属于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语文素质型实验。在经费和师资具备的条件下,它是可选的语文课程教材改革之路。
三、刘朏朏“作文三级训练体系”实验
刘朏朏(1934年10月——),特级教师。1977年春天,与高原(北京师院分院教授)创立“作文三级训练体系”,实验在北京月坛中学启动,实验经验陆续刊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上。教材《三级训练作文课本》,配套教学参考书于1985年,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专著《作文三级训练体系概论》,1989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新时期起步最早的作文教学实验,它以“理论·教材·实验”相生相长的特色辐射全国。
大家都知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理论又来源于实践,这就需要人们在生活中有两种眼光,即感性的和理性的眼光。语文教育发展同样需要这种视野。从语文独立设科至今,百多年来,语文发展一直以感性的和理性的眼光,走在法规层面、实践实验层面和理论层面的建设上。理论虽然抽象,但它来自实践的总结,理论的认定和修改也来自对具体实例的分析,泛泛而谈的理论是空洞的。语文教师如果具有这两种眼光,他将是教育工作的创新者。
语文教育是一个类概念,语文教育理论就是研究语文教育原理性的问题,它必须是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的。下面,随机选取三个实验个案,具体看看语文教育理论和语文教育实践是如何相生相长的。
一、廖世承教育科学实验
廖世承(1892年6月——1970年10月),我国近代教育实验的开拓者,著名现代教育家、心理学家。他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在勃朗大学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扎根教育51年中,几乎都是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既是大学校长,又是附中校长;既是大学教授,又是附中教育实验的主持者。在大学,他教授中等教育、教育心理学、测验与统计等课程,在中学他先后以三个附中——东南大学附中、光华大学附中、国立师范学院附中为实验与实践的基地,在理论文本与实验实践互动中,结合国情进行了一系列中等教育的改革实验,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影响深远的辉煌篇章。
20世纪20年代的学制改革中,东大附中的“三三”制实验以其开创性和实效性影响于世。实验在全面发展教育理念下,将宏观的体制改革与微观领域的改革联系起来,使课程教材成为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课程设置以“合于升学,合于谋生,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课程结构新颖,实行分科制,设职业科与普通科。课程形态丰富,改单科制为选科制(读毕了必修科,可以选读选修课)。教材切近生活,以应用为归。课程评价利于学生发展,破除学年制,以能力分组,采用学科升班,实行学分制(学生读毕了学分,达到了主要科目的最低限度,就给毕业)。毕业年限有两年的弹性(或五年毕业,或七年毕业)。课程活动中实行指导制,学生受益与个人指导,选课指导,教育指导,职业指导,培养了选择能力和发现自我的能力。实验在鉴别个性、适应个性、时间经济、增加教育效率、增加中学人数、衔接密切等方面成效卓著。光华大学附中通过实验成了全国的模范中学。国师附中应抗战急需,实验“五年一贯制”,其效果是殊途同归,成为培养优秀师资的摇篮。
20世纪20年代,测验处于草创阶段。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开设《测验课程》,成为我国正式应用心理科学测验的开始。在儿童心理测验和汉字研究的基础上,他俩合著,1921年出版《智力测验法》,1925年出版《测验概要》,推动了测验的科学化和本土化的研究。他创立的“廖氏的团体测验”享誉国内外。
国文改革很超前,认为社会的组织愈复杂,人群的交际愈密切,用“口”发表的机会也愈多。为此,国文教师可使学生在班上演说,练习口头发表,或在台上表演。除了书本以外,还要通过团体的课外活动为学生打下“立身行事”的基础,尽“教”的工夫,尽“育”的责任。开展辩论会,练敏捷,练社交。其正方和反方的辩论方法延续至今,三角式的辩论方法可供今天借鉴。办周刊与国文科结合,使周刊成为学生练习用文字发表思想的阵地,成为形成良好校风的喉舌。自编的刊物多种,皆为课余之练习。举行全校国语比赛。组织文学研究会、戏曲研究会。话剧在学校占有重要地位,认为话剧可以补助语文的练习,增加个人的经费,可以联络各科的教材。对话剧研究社的活动,师生兴趣素来不坏。
二、道尔顿制实验室计划
道尔顿制,1922年传入中国,中国公学附设吴凇中学舒新城于当年10月在国文及社会常识两科率先试验此制。《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先后推出《道尔顿制专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定试验此制,试验学校达百余所。试验的5年间,发展呈波浪起伏状,1926年后,终因财力和师资的滞后,仅有个别学校坚持实验。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具有精密研究的价值。
道尔顿制实验室计划,简称道尔顿制,是教学的一种组织形式和方法,为美国柏克赫斯特所创建。她以美国的道尔顿城一中学命名。该实验大体运用了蒙台梭利和杜威的教育理论。实验的目的是改善学校生活,使各类学生有均等的机会发展个性。它的原则是自由;学校即社会;知而后行。如此以儿童为本位,意在使学生对教育负担责任,感觉兴味。实施中,教室改作实验室。实验室就是知识的工作场,即生活场。实验室有“月约”、“周约”、“日约”三种“公约”:“月约”,给学生以概略的观念;“周约”,给学生博采旁收那些造成这个中心观念的种种材料;学生按前两“约”在实验室作业,作业时间、速率自行酌定。“日约”则是为养成学生责任心、自动力而填写的学习情况表格。师生为师友关系,教师为指导员,指导路程,定走法,让学生自己去走,助其成功进步。成绩考查以“公约”为标准。
在中国该制国文科试验中,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东大附中、北京艺文中学创举空前。代表人物中,除著述甚丰的舒新城外,穆济波、沈仲九、孙俍工,在创造的层面上,与朱自清的“国文科行道尔顿制应该比现行制好”的预见相回应。如穆氏的初二上实验室,作业种类有精读之书、笔记、作文、课堂研究和课外阅读。全学期总计,要精读10万字,笔记至少16则(参考不计),作文8篇,课堂研究40小时,课外阅读3种。孙氏还创造了文艺文作业法:分篇、家别、国别、分组四种作业法。对此制的研究,朱光潜认为课室生活和书本生活在道尔顿制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如果打破这两种生活,将学校生活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把设计教学法的这一目的兼容进来,此制则可锦上添花。正是如此创造性地运用道尔顿制中“自己研究”、“个别学习”的精髓,并以实验的结果随时修改此制,使之合语文特点,合国情的实验方向,使此制的实验价值,更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
上述道尔顿制的精髓与时俱进,它对弥补班级制的不足,丰富班级制的教学形式,促进个别教学在终身教育和素质教育以及全球化语境中的新发展,都有借鉴意义。历史上的程序教学、图书馆教育、函授教育、成人教育;现今的开放学校、远程教育、网络学校;语文教育中的语文自学辅导实验、语文能力三年过关实验、语文自学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实验,以及语文研究性学习实验,特别是高密一中“语文实验室计划”,他们都是明证。高密一中“语文实验室计划”始于1995年秋,是一种全方位的教学改革,它在无可借鉴的基础上起步,为突出其实验性,故称之为“语文实验室计划”。然而,它的精华和运行方法几乎和美国的“道尔顿制实验室计划”不谋而合,它属于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语文素质型实验。在经费和师资具备的条件下,它是可选的语文课程教材改革之路。
三、刘朏朏“作文三级训练体系”实验
刘朏朏(1934年10月——),特级教师。1977年春天,与高原(北京师院分院教授)创立“作文三级训练体系”,实验在北京月坛中学启动,实验经验陆续刊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上。教材《三级训练作文课本》,配套教学参考书于1985年,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专著《作文三级训练体系概论》,1989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新时期起步最早的作文教学实验,它以“理论·教材·实验”相生相长的特色辐射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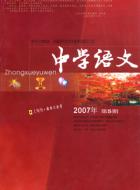
- 语文课程改革的脊梁 / 韦志成
- 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略论 / 陈菊先
- 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高峰论坛综述 / 陈 枫 张萌萌
- “余映潮语文教育研究”研讨会在荆州市隆重举行 / 王世发
- 幸福 欣慰 感谢 / 余映潮
- 想起余映潮老师 / 王 君
- 不言春作苦 常恐负所怀 / 李昌林
-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 张安群
- 诵读、积累、实效——板块式教学设计的三个基点 / 张慧莲
- 论余映潮先生教学艺术的文化品位 / 陈光浩 林富琴
- 新课改背景下语文教学流弊批判 / 石子林
- 语文阅读教学的“边角” / 杨树亮
- 从作品解读中开启学生的善良和悲悯情怀 / 王木清
- 语言品味探赜二题 / 邓嗣明
- 小步轻迈细品读 / 任明新
- 发掘隐含信息:作文审题教学的重要环节 / 陈锦山
- 精彩不仅是他们的 / 唐香萍
- 文本、写作与开放的语文课堂 / 王莉华
- 寻求心灵的自适,被动于山水的皈依 / 樊 华
- 彤管:解读《静女》的钥匙 / 陆精康
- “精彩”之后的反思 / 花海棠
- 让学生在读中享受乐趣 / 刘 丹
- 巧设问 / 段艳敏
- 看似寻常最崎崛 / 陈淼星
- 衬托,还是烘托 / 张淑君
- 新课程改革中新问题的思考 / 丁宏伟 李艳萍
- “高枕”何以“无忧” / 刘 念
- 一“句”一“逗”尽风流 / 郑可菜
- “宴酣之乐”献疑 / 邹 贞
- 贡,求也 / 叶章维
- 李儋元锡是一人还是两人? / 陆 瑢
- “膑脚”“断足”语焉不详 / 孙 云
- 循理以求 / 朱庆和
- 材料设计二则及写作思路详解 / 张志先
- “文学名著阅读”新题备考策略 / 程必荣
- 联合短语在病句中的病情透视 / 周加银
- 海外语文练习的基本特点 / 张悦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