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0期
ID: 143398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0期
ID: 143398
示范课也要有“三不”精神
◇ 孙丽红
谈论公开示范课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许多时候作为中学老师都在评判或公开着;但谈论公开示范课又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有许多纠结与不爽伴随其中。我还觉得,谈论语文公开示范课似乎是一件尤其容易的事情,许多其他学科的老师(特别是领导)喜欢听喜欢谈;但谈论语文公开示范课又似乎是超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除了纠结与不爽,还有太多的疑惑与争议在里面。
不过,难也好,容易也罢,我打算从钱理群先生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谈起。钱理群先生的文章提出“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的问题,笔者需要回答的是“我为什么在谈论中学语文公开示范课这个问题时要提‘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中这个观点”的问题。
首先,钱理群先生在《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 鲁迅也不是“导师”。其中不是“主将”和不是“导师”是鲁迅先生自己强调过的。理由简述如下:无论是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所以不是“主将”;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所以不是“方向”;鲁迅本人更是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明确指出,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所以他也不是“导师”。而正因为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鲁迅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别样的价值。
其次,笔者对本文所谈的“公开示范课”这个概念做一个粗浅的界定,便于行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对“公开”一词的解释是这样的:①形容词,不加隐蔽的;面对大家的(跟“秘密”相对),如“公开活动”;②动词,使秘密的成为公开的,如“这件事暂时不能公开”。“公开课”中的“公开”应取其中“面对大家的”之意。目前中学教学中根据课的功能、任务,有几个常用的概念:公开课、观摩课、研讨课、研修课、实验课、展示课、示范课……顾名思义,笔者认为“公开课”可以作为以上所有“面对大家的”课的总称,换言之,所有“面对大家”上的课都是“公开课”。具体而言,在某个范围内已经成名或公认水平高的老师上的课可以称之为“示范课”,针对解决某个教学问题启发听课者研究讨论的课可以称之为“研讨课”,“示范课”和“研讨课”是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最为常见的两种公开课。再有,既然是公开课,一定有或多或少的听众,因此笔者认为课后的评课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它已经成为公开示范课这种教学交流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课后的交流,公开上了的课也不算真正的公开示范课,跟自说自话的“关门课”没有两样。故此,本文所论“公开示范课”实际上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面对大家上的课;第二,课后的评课交流。二者不可分割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接下来,说说我谈论中学语文公开示范课这个问题时为什么要从这三个“不是”切入话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基于目前公开示范课开展的现状。有一句话能贴切地表达出相当一部分老师对公开课的“纠结”心理:公开课,想说爱你不容易。“想说爱你”意味着对公开课的期待心情,期待意味着价值,价值在于学习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换言之,公开课是被需要的、有价值的。然而“不容易”三个字沉重地反映出“需要”的不被满足。笔者认为目前中学语文公开课(我不知道其它学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故不妄言)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公开课的作用离人们的期望还有一定距离,其本质诱因在于公开课承载了过多类似“主将”、“方向”、“导师”等不堪其重的“责任”,而有些时候却恰恰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甚至走向“反向”。
随手一例:今年6月中旬(实际上就是笔者撰此文的前几天),我在杭州浙江大学的课堂上聆听一位省教研员的讲座。这位资深教研员告诉我们他评课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扬善于公堂,归过于私室”。但有一次,他听完一节课后十分痛苦地发现实在找不出任何优点,于是在点评座谈中“艺术”地把皮球踢给市教研员,结果市教研员也很为难,离开这节课本身大谈这位教师平时的工作成绩,最后表示要听省教研员的高见,把皮球又踢了回去。于是省教研员万分为难之际以高度的“智慧”从如果自己上这节课会怎样处理入手,“巧妙”地“点评”了这节课。听讲者无不佩服这位资深教研员处理难题时高超的“回避艺术”。诚然,当时的情景我没有亲历,也许只有这样才是最佳的选择,但我不知道在这种“巧妙的回避”中,那位授课老师有没有受到更深的伤害,与会听评的老师们内心又是何种滋味;如果诚恳直言,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意见,那位授课老师会否真的会感到“没有面子”?
其实,这还不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位省教研员出发点是善意的,他的底线是不说假话,找不出优点他只好不说,于是采取了顾左右而言其它的“鸵鸟政策”。在参加各种场合的公开课及评议时,发现更加可怕的是出于种种明眼人一望而知的目的,主持者“诱导”听课者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任意拔高,糟糕的说成好的,没有的非要说成有。而一众满怀希望而来的听众抱着满腹的不敢说出口的疑惑无比郁闷地离开会场……这种被人为贴上“主将”、“方向”、“导师”的课与评课,已经不仅仅是让人不爽了,简直是贻害无穷,给青年教师很难纠正的误导。偶或有敢于发难者,则像拆穿皇帝新装的孩子,令人神情为之一爽;但随着主持者一句“请问这位老师是哪个学校的”,令刚准备开口的其他老师不得不识趣地噤若寒蝉了。其实,笔者也不止一次有幸在失败的公开课上遇见水平极佳的评课高手,其谦逊得体的言语、妥帖到位的点评令听众心中无比熨帖,满载而去。
在所有公开课中,“示范课”最可能具有引领“方向”的作用。由于一般是名家、大家或准名家、准大家上的课,成功率相对较高,可资学习的地方也较多。毋庸置疑,名师凭借多年积淀下来的深厚课堂教学功底,以创造性的教学设计,用直观、新颖的教学方法,传递新的教学思想、展示新的教学手段,是促进教师重视课堂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但是,笔者也听到过不少失败的示范课。事实上,即便是名家也无法绝对保证每一堂示范课都成功。记得我仰慕的于漪老师2009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中语会年会上曾提及这样一件事:她出名后,每一节课都有慕名而来的人来听,她说这种感觉完全不是享受,用四个字形容是“生不如死”。当时我听了十分惊讶,鼎鼎有名的于漪老师还如此紧张别人来听课!我想,主要是担心听课者期望太高吧。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名家不能绝对保证每一堂示范课都成功,另一方面,作为听课者也无须苛求示范课都精彩,——但,我们有理由要求每一堂公开课后的评课交流都精彩!可是实际上,令人郁闷的是许多研讨课、实验课更成了不能“触碰”的雷区,一开始就被贴上了“主将”、“方向”、“导师”的标签,承载着指挥者的许多“意图”。由于这类课多由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承担,难以尽如人意的几率相对较高,却无一不是“大获成功”。
“示范课”为人诟病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人认为即使上得很精彩的课也是“作秀”胜于“实用”。于是有观点认为,“示范课”应该是一首歌,人人都可以学唱;而不应该是一场戏,人人只能当捧场的观众。对此,笔者大不以为然: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任何课都是不可复制的。教学是一个尤其复杂的过程,影响我们教学实际过程的因素是不确定的,每节课面对的学习对象、学习内容等等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但不应该学唱别人的歌,甚至不要重复唱自己的歌,惟其如此,我们的课堂教学才可能灵动起来,才可能越来越有灵气。严厉一点说,抱着“学唱歌”的态度参加公开课的研讨,态度是不端正的,动机也是不纯的,这不是“拿来主义”,而是“搬来主义”。
综上,笔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公开课本身可能而且可以不成功,但在“三不”精神的引领下,即便课堂教学失败了,有了精彩的点评,公开课活动一样可以成功!笔者以为,包括“示范课”在内的公开课,要放下架子,切勿从一开始就摆出“主将”、“方向”、“导师”的样子。欢迎评论,尤其欢迎不同意见的评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公开的作用,专业的灼见、求真的氛围、善意的措辞,这些才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方向”。如果我们还愿意把教学研究当做学术看待,则必须摒除讲假话套话的风气,营造鼓励说真话的氛围,以这样的胸怀去发展教育,培养有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教师和学生。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营造公开课的“三不”精神呢?笔者以为,这种真诚探讨的空间需要几方共同构筑:组织者要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专业水准,有不怕被否定的底气和精神,创设讲真话的空间;授课者要有宽广的胸怀和虚心的态度,倾听不同的声音;评课者本着与人为善发表一家之言的平等平和的对话姿态,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值得肯定和需要改进之处。
特别是组织者站在强势的地位,能否容忍甚至鼓励听课者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是对其民主精神、活动本身的学术含量的一个基本的检验。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有许多担任公开课组织者的机会。我的亲身体会是:说真话,说有建设意义的话,是对教育、对执教者最深沉的爱,是对参与公开课的听者最好的尊重,也是对组织者专业水平的考验和体现。当我们一以贯之地本着“不是方向”的精神去营造公开课民主、开放的氛围,长此以往,我们的公开课将会成为教师们心目中真正的“方向”。其结果,我们的示范课就会臻于“不是方向”胜似“方向”的境界,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和向往啊。
评课的良好气氛还需要承担公开课的老师来营造。就公开课本身而言,其价值很明确:通过一位教师的课堂教学让其他听课教师有所启发。承担公开课的教师都希望课上得成功,他背后的智囊团也希望成功,不远N里来听课的老师也希望听到精彩的富有启发的课。事实上,成功的课不仅本身能给众人启发,也使评课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但课堂教学现场情况千变万化,一个环节出问题,课堂教学的效果就可能不尽如人意。何况教学是遗憾的艺术,上得再好的课也有遗憾在其中。维纳斯是美的,断臂的维纳斯也是美的。公开课允许有残缺,但是一定要有“美点”,“美点”就是有别于过去、有别于他人的新尝试、突破和创新,“美点”亦包括评课环节,这都是公开课存在的价值。
一次,我所在的区聘请了北京一位全国知名教师来上示范课,由于对广州学生缺乏了解,虽然看得出教师功底很深,但学生明显跟不上,整堂课颇有启而不发的味道,听课的老师十分佩服这位名师的深厚功底,心中无不着急“学生怎么这么差”。客观地说,由于学生没跟上,课堂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上完课,名师不为自己辩护,反思自己对广州学生缺乏了解,引导不足,对不起学生。此言一出,听课教师心中折服:名师就是名师,有自我批评的底气!接下来的评课其实就变成了请教,希望名师解答自己对语文教学的种种疑惑。由于授课者的大气,整个示范活动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认可。
接下来说到第三方参与者——评课者。评课者的组成是多元的,有组织者专门聘请的专家,有现场听课者……一般而言,评课者的表现是被引导的。也就是说如果组织者善于营造民主和悦的评课氛围,授课者乐于倾听各种意见,评课者的参与往往很容易顺应这种氛围。其实只要是中肯、专业的评价,就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专家的评论也不是结论,切忌“盖棺式”评论,提倡多元评价,对所有评论可以再评论。评课者要怀着善意,以平和的语气提出尽可能中肯的建议,避免过于偏激。事实上,不同的意见往往才是最可贵的和最有价值的,才能在讨论中形成某种张力。针对问题来谈,只要是善意的、有针对性的、到位的意见,不但不会引起授课者的不安,相反会激发授课者的深度思考,使其产生被尊重的愉悦感。
例如笔者年初组织了一次区域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决赛课题是粤教版必修1第3单元第13课《沙田山居》(余光中)。一位选手的课行云流水,真挚动人,十分自然地引领学生走进了文本,赢得了所有评委和听课者的一致好评,是一堂难得的好课。但是,受各种参考资料的影响,跟所有其他选手一样,她把文章的感情基调与“乡愁”联系在一起。过后,作为组织者和评委,我就此问题再次与全区老师探讨,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观点引发了大家对如何深入解读文本的思考。后来,这位获得竞赛第一名的老师在颁奖会上作为代表发言时还真诚地提到这个建议对她教学专业发展的促进。笔者也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我读余光中〈沙田山居〉》),发表在《语文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上。
在这里,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真正有价值的公开课活动,应该是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对教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听课者甚至授课者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灌输,组织者也不试图灌输什么;相反,我们共同期待在这样的活动中成长为有独立教学思想的人。当我们的公开课活动成功地营造了“不是方向”的氛围,则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方向。
最后,我不想就示范课的作用得出一些不痛不痒的教条式结论,我诚恳地建议,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开课的作用,请关心这个问题和所有其它教学问题的老师一定抽出时间,认真读一读钱理群先生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孙丽红,语文教研员,现居广东广州。本文编校;王 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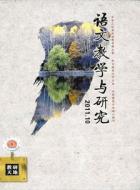
- 作文教学要规范成语运用 / 江建林
- “旧书”:平中见新 意蕴深厚 / 王世发
- 范畴思想下语文性质的三个统一 / 李旭山
- 语文教学要多一些儿童视角 / 丁卫军
- 语文课堂教学最优化的美学特征 / 葛其联
- 语文教学如何利用影视文化资源 / 黄金炳
- 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曲笔艺术 / 张喜梅
- 紧扣关键词组织课堂教学 / 邱守伟
- 语段写作训练教学实录 / 万咏英
- 解读《西游记》与宗教的姻缘 / 陈 洪 朱迪敏
- 人教版八上语文教材的删改与谬误举隅 / 陈晓涛 王秀娟
- 用诵读法执教《阿房宫赋》 / 单 猛
- 语文课堂讨论的误区和策略 / 缪志峰
- 《始得西山宴游记》情感变化轨迹探微 / 吴 琼
- 《马来的雨》教学过程中的朗读策略 / 王静娜
- 感受性原则在朗读教学中的运用 / 朱晓园
- 示范课也要有“三不”精神 / 孙丽红
- 论示范课的作用与反作用 / 吴细云
- 语文阅读教学需要文本的定性解读 / 李 兵
- 湖北省高考作文命制走向及其他 / 李锡林
- 描写性语言在记叙文中的作用 / 顾锦霞
- 2011年江苏高考作文阅卷心得 / 闫振松
- 快乐地给学生示范 / 董新明
- 在立意的深刻性上下功夫 / 李建邡
- 论汉语中唱读唱说吟诵三种声音的呈现形式 / 臧艺兵
- 在教学研的修炼中共同成长 / 尹继东
- 语文示范课的示范作用 / 唐子江
- 素口清音唱新曲 / 谭小红 陆美娟
- 用素读的方式品味语言 / 葛继红
- 语文教材插图要取之有度 / 刘砺萍
- 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困惑与策略 / 任义兵
- 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性读书建议 / 张志平
- 初中鲁迅作品专题教学设想 / 赵 俊
- 艾米莉.迪金森和她的“无名小卒” / 黄燕红
- 屈原的毕业诗 / 金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