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0期
ID: 143395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0期
ID: 143395
《始得西山宴游记》情感变化轨迹探微
◇ 吴 琼
柳宗元被贬永州,长达十年,足迹遍及永州的青山碧水。游之所至,或寄情于青山,或托意于碧水,于是永州的山水便成为他的情感载体。因此,如果要梳理柳宗元情感变化的脉络,就必须走进他笔下的永州山水。通过对山水的欣赏,我们就可以走进其内心世界。
一.被贬永州,惴惴战栗
“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永州。永州地处湘粤交界,乃蛮荒偏僻之地,此地“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简直就是一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即便“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文化苦旅》,文汇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因此被贬永州,就意味着此去会险象环生,凶多吉少。
到达永州之后,政敌们仍不罢休,咒骂之声不绝于耳,人身攻击接连不断。柳宗元本来还心存重返朝廷、报效国家的一线希望,谁知残酷的政治迫害又接踵而至,怎能不让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怎能不让他悲愁万状、愤怒万分!
柳宗元被贬,年近七旬的老母卢氏也跟着遭难,至永州未及半载,老人家便撒手人寰了。老母伴随他半生,历经磨难,而他竟不能让老人家安享清福,颐养天年,怎不满怀愧疚?怎能不羞愧难当?而今老人家竟然驾鹤西去,仙归道山,他又怎能不伤心欲绝?纵有孝亲之心,又何从报答?老母在时,内心若有忧愁苦闷,还可向老母倾诉,如今老母逝去,自己的满腹忧郁,又向谁诉说啊?!
柳宗元初到永州,无处栖身,寄宿寺庙,后方有居所,渐次安定。可谁料,数次火灾,将居所付之一炬,使得贬谪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火灾过后,只剩下一片瓦砾废墟,柳宗元只好重建房屋,而建房又谈何容易!劳神焦思,痛身苦体,竟至“行则膝颤、坐则髀痹”,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身体的痛苦必然会给他带来心灵的痛苦,而心灵的痛苦又无法言说,于是乎,柳宗元的痛苦就变得更加深巨了。
如此深重的苦难,如此愁苦的心境,柳宗元仅用“恒惴栗”三个字一带而过,足见其直面现实的勇气,包容苦难的胸怀。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三个字所蕴含的愁肠百结的复杂心境。
二.游历山水,难遣郁闷
为了排遣心中的悲愤与忧郁,柳宗元便在公务之余,游历永州的佳山秀水,常常是“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施施而行”,他的步履是那样的舒迟缓慢;“漫漫而游”,他的出游是那么地漫无目的。不难发现柳宗元心中是何等怅惘若失!是何等茫然无措!即便如此,他仍“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应当说游历的永州山水是风光迷人的:山峰险峻巍峨,森林幽深宁静,溪流萦回曲折,泉水清幽澄澈,石头绚丽多姿。但柳宗元所至多为人迹罕至之所,清冷凄清之境。彼景彼境,“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所以很难排遣他心中的郁闷愁苦。此时的永州山水成为了他宣泄情绪的一个自然对象。但那山还是那山,那水还是那水,山水并未对其情感宣泄产生回应。试想想柳宗元身处尘世,尘世冷酷无情,身入自然,自然寂寂无声,该是何等孤独、何等寂寞!既然尘世读不懂他的灵魂,自然读不懂他的情感,那么又有谁能读懂他那深入骨髓的痛苦?又有谁能读懂他那痛断肝肠的苦闷呢?即便如此,柳宗元仍执着地寻求着内心情感释放的途径与通道,期待着情感释放后的轻松与宁静。
三.醉而入梦,难以解忧
无奈之下,柳宗元只能“披草而坐,倾壶而醉”,借酒消愁,但酩酊大醉也不能消解心中的抑郁苦闷。酩酊大醉之后便席地而卧,相枕而眠,酣然入梦。心有所思,梦有所想。梦己春风得意、飞黄腾达,鲲鹏展翅、大展宏图。怎奈梦虽甜美,总有梦醒时分,一梦醒来,夕阳西下,暮色苍茫,现实残酷,处境维艰。于是酌酒之酣畅一扫而空,美梦之甜美荡然无存,怎不令柳宗元意兴索然?
柳宗元本想借畅饮来释放心中的抑郁之情,岂料“借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怎能不痛苦万分?本想借美梦排遣心中的忧愁之苦,岂料梦醒时分依然如故,又怎能不黯然伤神?回到现实,现实依然冷酷,柳宗元的心情依旧压抑,只能无奈而起,失意而归。
四.畅游西山,觅得知音
在千寻万觅、千呼万唤之后,西山终于揭去了神秘的面纱,呈现在柳宗元面前。当然游览西山并非一帆风顺的,攀登西山时也遇到了重重阻碍,“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便是明证:“过湘江”可见西山是在水一方,可望不可即;“缘染溪”足见此行之逶迤曲折;丛生的灌木、纵横的杂草,预示着登山无路。但柳宗元并未因此知难而退,相反,他更加锲而不舍地去执着追寻。西山不是可望不可即吗?他就是要识西山真面目。溪流不是逶迤曲折吗?他就是要走这溪流的尽头。登山不是无路可走吗?他就是要在榛莽丛生、茅茷纵横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凭着坚定的信念,硬是开出了一条登山的羊肠小道,最终登临西山之巅。这不正表现了他坚定执着的人生态度,挑战命运的顽强意志吗?其实“榛莽”“茅茷”,何尝不是象征着当时小人横行、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斫”、“焚”又何尝不是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无情批判?
柳宗元登临绝顶之后,极目远眺,“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可见他视野是何等广阔。其实作如此写是有其用意的,用意有二:其一,视野愈广阔,则愈能衬托出西山之高峻;其二,视野愈广阔,就会使其心胸愈开阔,而心胸愈开阔就愈会使心中的郁闷愁苦得到排遣。“其高下之势”三句,暗中将其他的山峰、山谷和西山进行了比较。隆起的山峰“若垤”,低下的溪谷“若穴”。那么其他的山峰、山谷是否真的如此呢?非也。其实其他的山峰也是相当险峻的,其他的的山谷也是特别幽深的,柳宗元说其“若垤若穴”是运用了夸张(缩小夸张),目的就是欲通过两相对比来表现西山的高峻。“尺寸千里”三句,说千里之遥浓缩在尺寸之间,而那纷繁众多之景物,都丛聚收缩于眼界之内,无处遁逃,无法隐藏。千里之景之所以能浓缩于方寸之间,不仅因为西山的高耸入云,险峻巍峨,更因为柳宗元开阔的心胸。“萦青缭白”三句,则由近而远,写青山白水相互萦绕,绵延开去,云天相连,浑然一体。置身其中,他不禁情满于山,意溢于水,思翔于空,宠辱皆忘,万虑皆空!“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一句,则点出西山的特点——特立独行,卓立天地。行文至此,笔下的西山就耐人寻味了。为何如是说呢?因为此时的西山已不仅仅是自然的西山,更是人格化的西山,西山已成为柳宗元精神人格的象征。西山的特立独行,正象征着柳宗元的特立独行;西山的卓尔不群,正象征着柳宗元的卓尔不群。“不与培塿为类”一句中的“培塿”也是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的。“培塿”象征着奸邪谄谀的小人,肮脏龌龊的佞臣。而“不与培塿为类”则表现了柳宗元“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情操,表现了柳宗元不与宵小之辈同流合污的洁身自好。至此,柳宗元在西山风光的饱览中找到了西山与自己追求的精神境界的契合点,自我与山水产生了心灵感应,产生了心灵共鸣。
五.引觞满酌,流连忘返
饱览西山美景之后,柳宗元倍觉神清气爽,颇感意兴盎然,于是把酒临风,开怀畅饮。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后,柳宗元喝得东倒西歪,喝得酣畅淋漓,喝得逸兴壮飞!此时此刻,眼前是壮丽河山,杯中是陈年佳酿,心中是超然洒脱,柳宗元沉醉于这美好的境界之中,竟全然不知时光之流逝!夕阳西下,为霞满天,全然不知;暮色降临,苍苍茫茫,浑然不觉;夜色深沉,漆黑一片,柳宗元流连忘返。内心苦闷彷徨之情感一扫而空,抑郁忧愁之心绪荡然无存,有的只是畅饮美酒,怡然自乐,有的只是忘情山水,悠然自得。
六.身与物化,澄明宁静
高峻峭拔的西山已然成为先生的知音,西山开阔的境界荡涤着先生的心胸。柳宗元神思悠悠,与天地浩然之气相应;情怀浩荡,与自然大千共同遨游。浩然之气无边无际,何其浩淼!自然大千无穷无尽,何其宏大!浩然之气融入柳宗元胸中,他神清气爽;自然大千包容了柳宗元,他心旷神怡。柳宗元的内心一片空明澄澈,似乎连他的形体也消散开去,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此时的他已真正进入了“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最高境界。不再郁闷于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不再感伤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柳宗元变得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变得豁达开朗,超然洒脱,进而在山水自然中完成了贬谪人生中一次崭新的脱胎换骨。
至此,我们通过对西山美景的欣赏,就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柳宗元内心情感变化的轨迹,也就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篇文章的思想感情。
吴琼,语文教师,现居江苏东海。本文编校:左晓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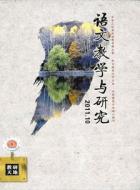
- 作文教学要规范成语运用 / 江建林
- “旧书”:平中见新 意蕴深厚 / 王世发
- 范畴思想下语文性质的三个统一 / 李旭山
- 语文教学要多一些儿童视角 / 丁卫军
- 语文课堂教学最优化的美学特征 / 葛其联
- 语文教学如何利用影视文化资源 / 黄金炳
- 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曲笔艺术 / 张喜梅
- 紧扣关键词组织课堂教学 / 邱守伟
- 语段写作训练教学实录 / 万咏英
- 解读《西游记》与宗教的姻缘 / 陈 洪 朱迪敏
- 人教版八上语文教材的删改与谬误举隅 / 陈晓涛 王秀娟
- 用诵读法执教《阿房宫赋》 / 单 猛
- 语文课堂讨论的误区和策略 / 缪志峰
- 《始得西山宴游记》情感变化轨迹探微 / 吴 琼
- 《马来的雨》教学过程中的朗读策略 / 王静娜
- 感受性原则在朗读教学中的运用 / 朱晓园
- 示范课也要有“三不”精神 / 孙丽红
- 论示范课的作用与反作用 / 吴细云
- 语文阅读教学需要文本的定性解读 / 李 兵
- 湖北省高考作文命制走向及其他 / 李锡林
- 描写性语言在记叙文中的作用 / 顾锦霞
- 2011年江苏高考作文阅卷心得 / 闫振松
- 快乐地给学生示范 / 董新明
- 在立意的深刻性上下功夫 / 李建邡
- 论汉语中唱读唱说吟诵三种声音的呈现形式 / 臧艺兵
- 在教学研的修炼中共同成长 / 尹继东
- 语文示范课的示范作用 / 唐子江
- 素口清音唱新曲 / 谭小红 陆美娟
- 用素读的方式品味语言 / 葛继红
- 语文教材插图要取之有度 / 刘砺萍
- 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困惑与策略 / 任义兵
- 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性读书建议 / 张志平
- 初中鲁迅作品专题教学设想 / 赵 俊
- 艾米莉.迪金森和她的“无名小卒” / 黄燕红
- 屈原的毕业诗 / 金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