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0期
ID: 143416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0期
ID: 143416
屈原的毕业诗
◇ 金道行
读屈原的《橘颂》,我的面前浮现的是满眼茂密的绿叶,挂着碧青的或金黄的非常漂亮的果子。有个少年伸手摘下一个,掰开,外青内白,浓烈的香气扑面而来。这是橘子!《橘颂》就这样展开颂橘,如见其色,如闻其香,如感其人。屈原为什么要颂橘?因为他的故乡在秭归,秭归自古是“柑橘之乡”。弗洛伊德说:“如果我们对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和白日梦者,诗歌创作和白日梦之间的比较是有价值的”,这就是“强烈的现实体验唤起了作家对先前体验的记忆(通常属于童年期),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在作品中获得满足的愿望”(《作家与白日梦》)。屈原正是这样,他对故乡最深的记忆就是看橘树,吃橘子。秭归的巫山云雨,温润潮湿,于是,“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诗里无意识地镂刻着他珍藏的童年记忆,也渗透着他对故乡——巴楚之地的深情。《橘颂》扑面和扑鼻的是屈原的稚气和朝气,足见是屈原的青少年之作,他的第一首诗,从选题就看得出来。
屈原颂橘要满足什么愿望呢?这首诗分两部分。上部咏橘,橘中有我;下部述怀,我中见橘。“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原来全诗是以橘树为象征,而以自我为中心。橘树的形象无处不有我的身影,颂橘是为了展示自我,写我又以橘树为映衬。“独立不迁”,“苏世独立”,表现了屈原从少年时代起就崇尚独立的人格。用精神分析读《橘颂》,诗人的自我形象,自恋人格,活龙活现,锋芒毕露。弗洛伊德说,“自恋者自我欣赏,自我抚摸,自我玩弄,直至获得彻底的满足”(《论自恋》)。屈原之颂橘,正是这样。诗人的自恋性人格在《橘颂》里全都裸露出来。唯其如此,更证明是屈原不谙世事时的青春年少之作。《橘颂》是一首青春颂。
可是,前人却把《橘颂》当成屈原放逐南蛮后的作品,以致王逸把它放在《九章》中。这是历史的误会。姜亮夫先生说,“《九章》的顺序可能是刘向父子校书时,将屈原《离骚》以外的零散作品九篇集中起来而成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九’呢?而且还十分勉强地把《橘颂》也放到里面去了,这是因为汉代人把‘九’当做最高、最大、最理想的数字”(《楚辞今绎讲录》)。离开了作品的精神机理(脉络),就会淆乱得没有道理。
有学者甚至在《橘颂》里读出了“近死之音”(清·蒋骥)。到1980年代,曹大中先生连续写出两篇大作,力辩《橘颂》还为屈原的“绝笔”(见《求索》1986年第2期)。他认为“《橘颂》是屈原一生主要精神矛盾——去留矛盾的最终总结”。他抓住“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等句,读出了屈原最终不离楚国的决心。而且,他认为如果《橘颂》表现青年时代的精神风貌,诗人的脑袋里怎么会想到“迁”、“徙”呢?因而必是遭“迁”、“徙”之后才写出。他还针对许多人以《橘颂》的四言诗形式认为是早期所写的看法,曹先生则以为《怀沙》的“乱曰”也是四言,且也说到“离愍而不迁,愿志之有像”,与《橘颂》末尾的“置以为像兮”多么一致!可见《橘颂》的“受命不迁”和“置以为像”肯定就是对《怀沙》的呼应与发展。其实,不论是《怀沙》还是《橘颂》都不是指的身体之“迁”,而是说的精神和人格。用精神分析读《橘颂》,读出的乃是精神亢奋,一往无前,一派“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味道,自恋人格及其形象如在目前,哪有一点晚年的暮气沉沉,和“近死之音”!
《橘颂》还是屈原的毕业之歌。屈原是楚之同姓,他的家庭却在秭归,这怎么理解?实际上正好说明他的父辈与楚王已不很亲了,才分封到穷乡僻壤的巴楚杂居之地去食俸禄。屈原从小在巫山脚下长大,他后来的确取得了楚国最高学府的学历,我估计可能是在16岁时才因聪明好学被召到兰台宫去读书的。那时楚国的贵族子弟学校设在兰台宫,相当于孔子在鲁国的“杏坛”,齐国的“稷下”,都是盛极一时的名牌学府。据近人考察,楚国的兰台宫建在郢中,即今湖北省钟祥市城内,距楚郢都很近(均属今荆州市),楚文化遗迹尚存甚多,至今还有一所兰台中学。姜亮夫先生说,“稷下是当时的学术中心,是稷下先生们谈天论地最热闹的地方”。而楚国的兰台,也未始不是南方的学术文化教育中心。屈原得到了在贵族子弟学堂接受教育的幸遇,他怎能不勤奋苦读!于是,4年以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20岁行弱冠之礼,就是现代的毕业典礼。那时楚国有盛会赋诗的风气。就在满堂俊彦的毕业典礼上,屈原踌躇满志,诗兴大发。他戴着簇新高耸的“学士帽”(“吾幼好此奇服兮,冠切云之崔嵬”)阔步登高,赋诗一首,就是《橘颂》。当他朗诵到“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全场也为之惊异;一起毕业的同学也都个个欢欣鼓舞。《橘颂》就这样以不凡的气势一鸣惊人。“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果然,毕业后他就留校——留在兰台宫了。从此,他开始在母校讲习,只是开初仍是三闾(分封之地)大夫的身份。《文心雕龙》说:“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可见屈原登台赋诗是常有的事,接触喜好风雅的楚怀王也更多了,以致“王甚任之”。
《橘颂》单纯,单一,甚至还有点单薄,它远不如屈原的其他作品丰富充实,艺术成熟。但是,青春年少,作品稚嫩,还有点可爱。故凡读屈原作品,都从《橘颂》读起,尤其是青少年入门。《橘颂》毫无掩饰地“露才扬己”,裸露了他的人格优点和弱点,成了自恋人格的自画像。而大凡毕业之歌,可贵的不都是一股“参天地兮”的冲天之气!
我在18岁初登讲台,正值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向科学进军,社会一片向上。我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在学生毕业时,我为他们写了一首《毕业歌》:
我们是一群展翅的小鸟,
要飞上蓝色的云霄。
让我们再喊一声“老师好!”
再见吧,亲爱的母校!
在毕业典礼上齐唱的时候,同学们都滚出了热泪,哽咽着,唱不下去。这是怎样难分难舍,而又带着奋飞的豪情!
我更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桃李劫》里的《毕业歌》。那时国难当头,词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从心底发出血性的呐喊: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我们几代人就是唱着这样的毕业歌成长。每次唱起,谁不精神奋发!
毕业,是人生的黄金时候,是最美好的记忆。只要上过学,谁没有毕业的体验?当我从记忆里哼唱: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耳边似乎忽然幻化成屈原当年的声音:
我们今天是绿叶素荣,
明天是行比伯夷的师长……
不管是哪个时代,毕业歌都叫人热血沸腾。
金道行,大学教授,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覃少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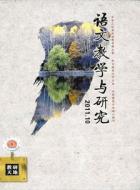
- 作文教学要规范成语运用 / 江建林
- “旧书”:平中见新 意蕴深厚 / 王世发
- 范畴思想下语文性质的三个统一 / 李旭山
- 语文教学要多一些儿童视角 / 丁卫军
- 语文课堂教学最优化的美学特征 / 葛其联
- 语文教学如何利用影视文化资源 / 黄金炳
- 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曲笔艺术 / 张喜梅
- 紧扣关键词组织课堂教学 / 邱守伟
- 语段写作训练教学实录 / 万咏英
- 解读《西游记》与宗教的姻缘 / 陈 洪 朱迪敏
- 人教版八上语文教材的删改与谬误举隅 / 陈晓涛 王秀娟
- 用诵读法执教《阿房宫赋》 / 单 猛
- 语文课堂讨论的误区和策略 / 缪志峰
- 《始得西山宴游记》情感变化轨迹探微 / 吴 琼
- 《马来的雨》教学过程中的朗读策略 / 王静娜
- 感受性原则在朗读教学中的运用 / 朱晓园
- 示范课也要有“三不”精神 / 孙丽红
- 论示范课的作用与反作用 / 吴细云
- 语文阅读教学需要文本的定性解读 / 李 兵
- 湖北省高考作文命制走向及其他 / 李锡林
- 描写性语言在记叙文中的作用 / 顾锦霞
- 2011年江苏高考作文阅卷心得 / 闫振松
- 快乐地给学生示范 / 董新明
- 在立意的深刻性上下功夫 / 李建邡
- 论汉语中唱读唱说吟诵三种声音的呈现形式 / 臧艺兵
- 在教学研的修炼中共同成长 / 尹继东
- 语文示范课的示范作用 / 唐子江
- 素口清音唱新曲 / 谭小红 陆美娟
- 用素读的方式品味语言 / 葛继红
- 语文教材插图要取之有度 / 刘砺萍
- 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困惑与策略 / 任义兵
- 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性读书建议 / 张志平
- 初中鲁迅作品专题教学设想 / 赵 俊
- 艾米莉.迪金森和她的“无名小卒” / 黄燕红
- 屈原的毕业诗 / 金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