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0期
ID: 143406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0期
ID: 143406
论汉语中唱读唱说吟诵三种声音的呈现形式
◇ 臧艺兵
引 言
语言由语言学研究,音乐由音乐学研究,但是既不完全是语言也不完全是音乐的现象由什么学来研究呢?但是这种现象在生活中却大量存在,它是语言学和音乐学共同的边缘地带非常有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领域。
2002年的初冬,我到武当山官山镇的吕家河村田野调查当地的民歌。一天早上,我看见清澈的吕家河布满鹅卵石的河滩上,村小学的女老师和她的小学生们把板凳搬到河边,坐成一组一组,在河边晨读。白的鸭子在河水里嬉戏,雾霭从河水中弥漫出来,学生那似读非唱、似唱非读、如诗如乐、非诗非乐的天籁之声伴着河水的哗哗声在晨曦中飘荡,听着这种声音,看到这等画面,我如同进入了我心中的理想国,那种陶醉感无以言表……
这使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母亲是一个乡村教师,幼小时妈妈得抱着我改作业,带着我在教室上课,自小在这种朗朗的读书声中长大,幼时对那种拿着书本摇头晃脑的大声吟唱式读书充满了热爱。我姥姥说,我还不会说话时,就会拿一本书模仿着小学生摇晃着脑袋,发出“喔恭 喔恭”的声音。我今天成为一名音乐学教授,有我去年刚刚过世的母亲多少心血呢,我说不清楚。只在心中升腾出一种怀念,这种怀念似乎不仅仅是怀念母亲这个人,而是怀念母亲所感染给我们的一种文化,一种我们越来越渐行渐远的美丽传统。
如果你细心品味哲学史为什么有一个语言哲学时代——世界的真相在乎我们如何去表达它;如果你再仔细想想涂尔干(Emile Dukheim(1858—1917))为什么说除了科学真理,还有一种真理叫神话真理——神话也能成为真理?也能变成作用现实生活的强大力量?只要你想想你自己一生中,说话如何影响了你的生活,你的命运,你的爱情,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生意,你的仕途,你就不难理解语言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人创造的语言,但是语言又反过来创造了人,人与语言的确是互为建构的。
无论是人类的说话还是音乐都是有一定声律规律的声音体系。只不过音乐的声音震幅宽得多,而语言,是按照正常说话的音高标记,至少汉语仅仅只用五度的声调值来标记。而人声有的高音音域宽广的可以唱二十几度。因此唱歌显然比说话要夸张很多。就笔者观察,中国许多方言,声调是很夸张的,尽管中国语言声调标记有247个标记符号,但汉语言的音高只有五度声调值的标记法,似乎不能满足其标记音高实际的需要,因为,在生活中,那些实际运用的语言,那些介于说话和唱歌之间的语言运用,声调远远超出5度的音域范围,而且在五度之内,还有比二度更小音程更精确的音高。从音乐记谱的角度来说,语言音调值的标记应该适应其更加准确的表达,如何改进,可能是语言音韵学家和音乐学家未来共同的工作。
标准的说话和标准的唱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分辨出来,这是因为说话的音调是短促的,而唱歌恰恰相反,是将歌词的音调拖得很长。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像唱歌一样的说话,那种介于语言与歌唱之间的语言现象,我们日常生活中,多只从诗词吟诵的角度研究它,其他关注的就比较少。如唱读,就是小孩们读书时,把读书当歌唱的那种。唱说,则是那些在日常对话中,以很夸张的说话音调的方式说法。
关于语言与音乐之间的声音现象,赵元任先生早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讨论过。他说:“所谓吟诗吟文,就是俗话所谓吟诗叹文章,就是拉起嗓子来把字句都唱出来,而不是用说话时或读单字时的语调。”不过赵先生主要是讲诗词吟诵的现象,并没有把说话与唱歌之间的所有现象细分。而事实上,在语言与唱歌之间,的确有一个“灰色地带”,虽然是面对性质相同的语言现象,音韵学不能延伸到音乐里面,旋律学能延伸到语言里面,也就是说这种语言现象,既不能完全用语言学的原理解释,也不能完全用旋律学的原理解释。如何解释,需要探索,我先尝试着将这种现象分为三种,那就是:唱读、唱说、吟诵。
唱 读
唱读,就是对文章的音调夸张的朗读。这种朗读比朗诵更接近唱歌,也包括了小学生背书时的背诵唱读的状态,唱读的最大特点,是在读书的时候,以唱歌的腔调,即兴自由的表达出来。以我的家乡湖北保康县的方言为例,唱读时常常一句话只用一个声调,通常是第一声,但在一句结尾的那个字使用该字的本来音调,也就是有一个拖腔,佛教的诵经也基本是这种读法。我例举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中的几句。
例: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
第一句:除“志”念第三声,其他都念第一声。
第二句:除了“员”念第四声,其他都念第一声。
第三句:全部念第一声,因为“了”字在当地方言念第一声。
第四句:全部念第一声,因为“里”字在当地方言念第一声。
第五句:除“国”念第一声,其余念第一声。
第六句:除“安”字念第三声,其余念第一声。
第七句:除“作”念第四声,其余念第一声。
第八句:除“职”念第四声,其余念第一声。
以上的例句,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总是拖长音的。
唱读时候,有时是根据文章的规定断句,但有时候也根据唱读者的气息长短断句。大致也会遵循句子的意思。总之,唱读者要根据唱读者自己的主观感受,根据方言的音韵拖腔,唱读者在唱读时,觉着舒服、省力,自由自在,自然放大方言音调为原则。唱读多是小学生自习读书时的所谓的“哇哇读书声”,是书童特有的读书方法,因为很多孩子在教室里一起大声读书的状态,最早形成了母语在孩童大脑发育时的神经联系,是最早最深刻打上母语文化印记的东西,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唱读是可以用音乐的乐谱记录下来的,以上的这种唱读方法,在中国的蒙童读书中是比较普遍的,从音乐的角度看,它有些像西方的早期的格里高利圣咏。每一句诗文,前面的字词的音高是差别不大的,尾音有一个拖腔。也是一句歌词的落音,中国民歌中的调式主音常常是这样确定的。但是,因为唱读,除了最后一个音有拖吟之外,前面的字都是几乎在同一个音高上说出了的,所以更多也是语言的范畴。
唱 说
在语言与音乐歌唱之间,还有一种就是唱说。唱说现象也是从日常语言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它也是非唱非说。它不是源于对书本的语言现象,而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使用。笔者小时候在鄂西北的农村生活,经常见到两个村妇在较远的距离交谈。山区地广人稀,环境安静,因为也没有外人,所以两人可以在较远距离谈话,例如一位在菜园里摘菜,不便走出菜园,而另一位则在菜园旁路过,两人需要寒暄几句,或是两人相隔一个小水沟,不必涉水过河交谈等等,常常是因为地理环境,或节省时间等因素,总之双方必须要大声拖腔对方才能听得清楚,每遇这种情况,就需要唱说,你远远地听,俩人像是在对歌,可近距离听她们两个是在说话。
例如:
甲:王—嫂—子,你—到—(哪)儿—尅(去)—滴(的)?
乙:看—我—到—合(作)—社—尅(去)—滴(的)门(嘛)。
甲:你—到—合(作)社—买—点儿啥—子?
乙:看我—灌(了一)—斤油,称(了)—两———盐,还买(了)几—斤—油—果—子门(嘛)
甲:嘿哟——,你—买—这—恁—些—东—西。
以下我来用音乐音韵学的方法来分析上面的对话。其方言音调值标记如下:
第一句:王嫂子,你到儿尅(去)滴(的)?
分析:王(51) 嫂(11)子(214),你(11)到(哪)儿(214)③尅(214)(去)滴(的)?
第二句:看(作虚词)我(11)到(214)合(作:浊化)(51)社(214)尅(去)(214)滴(的11)门(嘛11)。
第三句:你(11)到(214)合(作:浊化)(51)社(214)买(214)点(儿)啥(51)子(虚声)?
第四句:看(作虚词)我(11)灌(214)了一(两个字连读)斤(35)油(51),称(35)(了:虚声)两(11)斤(35)盐(51),还(51)买(11)(了)几(11)斤(35)油(51)果(11)子(11)门(嘛)(214)。
这种语言现象,不是日常的说话,不是唱歌,也不是吟诵,有一些方言,就是被这样表达出来。一是语言本身的音调,二是唱说者的语气,三是唱说者唱说内容的情感因素,因为它是日常生活语言,不是经过一定提炼的民歌歌词,所以它听起来像在唱歌,但实际上是在交谈,但它不是我们所说的通常意义的语言交谈,是介于语言与音乐之间的现象。这种语言现象在城市嘈杂的环境中很难产生,它是特定环境中的语言现象,过去较少有人注意到。
吟 诵
吟诵,是汉文化中的人们对汉语诗文传统的诵读方式,也是中国人学习语言时有效的学习方法,有着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学者的研究和文人的实践也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吟诵有自己的规则。大致分两大类。有格律者(近体诗词曲、律赋、骈文、时文等)为一类,依格律而吟诵;无格律者(古体诗、古文等)为一类,多有上中下几个调,吟诵时每句或做微调,组合使用,以求体现诗情文气。
吟诵的语音与当地方言有密切的关系。但也不是全部用方言口语语音吟诵。吟诵使用的是文读系统的语音。在北方,更接近官话,在南方,更接近当地方言。不同的方言区,有自己固定的流行吟诗调,地方戏曲的念白,能反映地方吟诵腔调的主要特征。吟诵调与本土的民间音乐相近,特别是宗教音乐的诵经、民歌的小调、琴歌、戏曲、说唱等具有密切的关系。吟诵有自娱如文人雅集,也有表演如诗词吟诵表演。吟诵是即兴的,所以同一篇文章诗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吟诵,也是有所不同的。
吟诵有一些基本调。这些调来自师承家传,或学习旁人之调,或自己创度。1、平长仄短。其中平声指1、2声,仄声是3、4声。五言诗歌以四行为一组,若为平起诗(即第一行第二个字为平声),则第1、4行第二个字拖长,第2、3行第四个字拖长。若为仄起诗,则相反。七言诗歌以四行为一组,若为平起诗,则第1、4行2、6字拖长,第2、3行第四个字拖长。若为仄起诗,则相反。都经自己的语感改造过。这些调一般为古体诗的几个调(有上中下之分),近体诗的平起、仄起各数调,读文则与此接近。
关于吟诵,赵元任先生认为“中国吟调用法儿的情形,大略是这样的:吟律诗是一派,吟词又是一派,吟古诗又是一派,吟文又是一派;吟律诗的调儿跟吟词的调儿相近,而吟文的调儿往往与吟古诗的调儿相近:论起地方来,吟律诗吟词调儿从一省到一省,变得比较的不多,而吟古诗吟文的调儿差不多一城有一城的调儿。(所谓调儿,并不是什么正宫调小宫调【key】或八十四调【note】的意思,乃是一只调子【melody,tune】的意思)不过用起来略变花样就是了。倘使有人把全部的《左传》《资治通鉴》《古文词类纂》,以及《新民丛报》等等,都用九连环的词来吟(随平仄长短略变花样),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可能。——也许某省某县吟文的调的确是这么样的,咱们没有调查过全国吟文的调儿,焉能知其没有呢?”吟诵是我国传统的文化,而朗诵是西方的文化,现在朗诵在我国比较普及,而吟诵并不普及,真正严格精通我国吟诵传统的人士是非常稀少的,现在我国有吟诵协会。如常州吟诵艺术协会等。常州吟诵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我国吟诵文化传统做出了贡献。
本文列举的这三种语言现象,在音乐在语言在音韵都属于边缘地带的有趣现象。但是语言学很少研究它,音乐也很少研究。但我却觉得这两方面研究它都很有意义,因为语言和音乐之间事实是没有一个截然的鸿沟的,那么学术研究就不应该留下这么一个空区。
之于语言研究的意义来说,他们的确是一种在生活中存在的语言现象,而且,每一种方言都有一种存在方式,每一种方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语言宝库。可是并不是每一种方言中都会出现一个语言学家。而我一直有一种观点,如果研究方言,你不能像母语一样熟悉它是很难研究的。最好这个方言是你的母语你才可能深入研究。为什么说语言音韵研究应该特别重视这部分呢?是因为它放大了语音的音节,使得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某种语言语音的内在结构性、区域特征和语系特征,以及方言在生活使用时语言语音与使用人的情绪的关系。另外一点,还在于这种语言音韵的标本如果不是特别留心的语言学家,并不是容易采集到,因为语言学家研究方言采集标本大多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多在室内,不是在田野中,不是在实际生活的场景中现场采录,容易被忽略。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能通晓各种方言的语言学家,所以这也是语言研究的误区之一。
之于音乐的意义。音乐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语言主要是同声乐具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声乐的声音形式,旋律节奏等的存在呈现依据主要是根据语言——也就是歌词而产生,就是所谓依字行腔,夸大语言的声腔就是基本旋律。也就是“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无论是作曲家的书面创造,还是民间语言家的口头创作,都是这样。因为各地的语言也就是方言不同,所以才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民歌旋律,决定民歌风格主要因素是方言的音韵发音。所以不研究方言发音的作曲家是很难写成具有地方风格的作品的。现在我们的作曲家都说普通话,用普通话的音韵进行创作,所以写出来的歌曲都是一个腔调,而那些写地方风格的作曲家,也大多是用某些民歌音调加以改变,可以说再配些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歌词,就算是地方特点歌曲了,所以音乐失去个性。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词作家,没有风格化的语言和地域文化底蕴,所以也写不出乡土味道浓厚的歌词,来刺激有才华的作曲家。因此好作品的产生很困难。所以说,我们音乐学院的声乐系和作曲系是应该很好学习音韵学的,不是仅仅知道语言与音乐的一般原理,而是要细致系统学习不同方言语系的发言与相应的民歌和戏曲的旋律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创作和表演的文化艺术精髓,音乐特别是声乐才会获得原创的条件和动力,才会产生真正的经典作品。前面我们谈到语言的社会文化建构力是强大的,普通话的普及的确为信息传播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它并没有取代方言,这说明方言在生活中的存在的文化合理性,因为方言表述了最贴近生命深处的生活,所以它成为各种艺术产生的土壤。但是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使很多艺术家离开了乡土,离开了方言区,所以我们能够欣赏到真正具有本土风格的优秀艺术品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强势的外来语言,还在冲击着那些弱势的土语,并使得它的特征变弱或者消失。
其实,还有基础教育的第三个方面的好处,那就是吟诵、说唱、唱说,对于儿童身心发展的好处。小儿身体发育时期,让其多说话对大脑发育有益处,读书唱读可以消除孩童读书的枯燥,使读书变得有乐趣,从而热爱读书。读书时夸张音调,变成唱说,也是在锻炼他们的唱歌发声能力,唱读时摇头晃脑自由自在高声唱读,要比说话朗读用的气力大,也锻炼孩子们的肺活量,增强了他们的身体机能。反思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我们的教学对知识和能力还有情感教育的分割太厉害,综合教育能力太弱。孩童时期的教育,能够将语言体态运动合为一体的教育,是身心合一的和谐教育。这种探索,理论上的意义是我们将语言和音乐方面的知识总结得更加完善,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实在是在延续着一件美妙无比的事情。
臧艺兵,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民歌与安魂》等。本文编校:晓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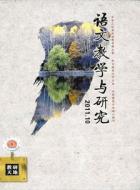
- 作文教学要规范成语运用 / 江建林
- “旧书”:平中见新 意蕴深厚 / 王世发
- 范畴思想下语文性质的三个统一 / 李旭山
- 语文教学要多一些儿童视角 / 丁卫军
- 语文课堂教学最优化的美学特征 / 葛其联
- 语文教学如何利用影视文化资源 / 黄金炳
- 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曲笔艺术 / 张喜梅
- 紧扣关键词组织课堂教学 / 邱守伟
- 语段写作训练教学实录 / 万咏英
- 解读《西游记》与宗教的姻缘 / 陈 洪 朱迪敏
- 人教版八上语文教材的删改与谬误举隅 / 陈晓涛 王秀娟
- 用诵读法执教《阿房宫赋》 / 单 猛
- 语文课堂讨论的误区和策略 / 缪志峰
- 《始得西山宴游记》情感变化轨迹探微 / 吴 琼
- 《马来的雨》教学过程中的朗读策略 / 王静娜
- 感受性原则在朗读教学中的运用 / 朱晓园
- 示范课也要有“三不”精神 / 孙丽红
- 论示范课的作用与反作用 / 吴细云
- 语文阅读教学需要文本的定性解读 / 李 兵
- 湖北省高考作文命制走向及其他 / 李锡林
- 描写性语言在记叙文中的作用 / 顾锦霞
- 2011年江苏高考作文阅卷心得 / 闫振松
- 快乐地给学生示范 / 董新明
- 在立意的深刻性上下功夫 / 李建邡
- 论汉语中唱读唱说吟诵三种声音的呈现形式 / 臧艺兵
- 在教学研的修炼中共同成长 / 尹继东
- 语文示范课的示范作用 / 唐子江
- 素口清音唱新曲 / 谭小红 陆美娟
- 用素读的方式品味语言 / 葛继红
- 语文教材插图要取之有度 / 刘砺萍
- 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困惑与策略 / 任义兵
- 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性读书建议 / 张志平
- 初中鲁迅作品专题教学设想 / 赵 俊
- 艾米莉.迪金森和她的“无名小卒” / 黄燕红
- 屈原的毕业诗 / 金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