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09年第8期
ID: 138376
语文建设 2009年第8期
ID: 138376
从“明规则”谈起
◇ 王灿龙
“规则”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按照一般语文辞书的解释,规则是指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比如交通规则、股票交易规则、球员转会规则、击鼓传花的规则等。规则一旦形成,大家就要达成一种默契——按规则行事。一般情况下,规则既不能违背国家的法律法令,也不能与社会道义和社会公德相抵触。从某种意义上说,规则可以看成对法律的一种业内补充或细化。因此,社会需要规则,规则对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积极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个范畴意义上使用“规则”一词的,也就是说,只要提到此种范畴意义上的规则,我们尽可以大大方方地直接使用“规则”一词。
然而近年来这种情况在发生改变。有些情况下,我们要避免直接使用“规则”一词,要通过前加“明”这么一个标记成分,将“规则”说成“明规则”。例如:“学术期刊的生存,多半靠‘道德自律’,这种情况下,一旦学术道德底线失守,‘潜规则’必然就会上升为‘明规则’。”(《人民日报》2007年7月23日)“潜规则和明规则是‘你进我退’的关系,潜规则的盛行是明规则没有得到坚决维护的结果。”(《北京青年报》2009年3月16日)
从语义真值方面看,以上的“明规则”完全等同于“规则”。用“明规则”取代“规则”,不是因为语义发生了变化,而是出于语用方面的考虑。
从语言内部来看,用“明规则”取代“规则”,只是汉语为适应表达的某种需要而进行的一个“微调”。之所以要作这种调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要反映的社会现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曾几何时,“规则”就是“规则”,它用于指称某一类规章制度,内涵和外延十分明确,使用的语境也非常单纯。所有的“规则”都是为规范人的社会行为而设的。在人们的认识里,“规则”范畴如同法律一样,是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范畴。然而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我们的社会进入一个转型阶段,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某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受到严重挑战和冲击,不良思潮及行为方式开始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中。有些事情像以前那样走正常途径,按传统规则来办,反而行不通,它们常常由一套另类规则管着。而这些另类规则一般都上不了台面,进不了文件,有的甚至令人难以启齿。但是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却都能大行其道,行内(或圈内)尽人皆知。一般人除了愤愤不平之外,无计可施。比如社会上流行的孩子升学“交钱搞牢”、病人住院要“派送红包”、演员上戏须“投怀送抱”等,都是另类规则的写照。由于这些规则普遍不能公之于众,只能潜滋暗长,暗箱操作,因此,人们便名之日“潜规则”。“潜”者,“隐而不露”也。为什么要“隐而不露”呢?见不得阳光之故也。
“潜规则”产生的历史并不长。笔者利用“人民数据库”(网址:http://people.com.cn)
对1946年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作了穷尽性的搜索,结果显示:2002年及以前的《人民日报》未见“潜规则”的用例,该词首现于《人民日报》是在2003年(当然,“潜规则”确切的首现时间还有待更广泛的语料调查)。
“潜规则”这一语言表达形式产生之后,便与“规则”形成了对立。以标记理论来审视,此时“规则”是无标记形式,“潜规则”是有标记形式。当“潜规则”偶尔一用时,它对“规则”还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可是随着“潜规则”愈加泛滥,“规则”在某些社会语境中的地位就愈显尴尬,难以与“潜规则”“相对而行”。因为在语义上,“规则”与“潜规则”相对,但在形式上,“规则”与“潜规则”却构不成明显的对称关系。再从逻辑语义方面看,“潜规则”也是一种规则,二者形式上的包含关系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规则”与“潜规则”似乎还有脱不掉的干系。这么一来,不仅“规则”这个范畴的“积极意义”被明显削弱,而且它与“潜规则”语义上的对立因为失去形式上的对称而渐趋模糊。
在这种情况下,挽救“规则”于颓势之中的唯一途径就是使它标记化,即在它前面加上“明”这个限定性标记词,说成“明规则”,使它与“潜规则”在形式上形成鲜明的对称关系。“明”的加入只是为了进一步突显其原有的语义,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其本来意义。也就是说,“明规则”还是原来的“规则”,原来的“规则”就是明规则。以前没有“潜规则”的时候,“明”是一个默认信息,在形式上可以缺省,我们可以直称“规则”;现在有了“潜规则”的干扰,就需要将这个“明”字由幕后提到前台,明确地宣称这是“明”规则,以示与“潜”规则相对。
可见,由“规则”到“明规则”,是无标记词语标记化的直接结果。这种对无标记词语进行标记化操作的手段,在现代汉语中时常用到。有不少词因其所记录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而不得不在语表形式上作适当的调整,比如由“保姆”到“女保姆”,由“富翁”到“男富翁”等。下面再简单分析一下“女保姆”这个词。
“保姆”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历史不算短。《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保姆”的解释是“受雇为人照管儿童或为人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该释文明确指出“保姆”是女性。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提及“保姆”这个词,都是指女性保姆。但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变化,从事保姆这个行业的不再只限于女性,许多男子也开始涉足这个行业。为方便称谓从事保姆工作的男人,人们便创造了“男保姆”这一词语。
“男保姆”这个类名产生伊始,就与“保姆”一词形成对立。“保姆”是无标记词语,“男保姆”是有标记词语。最初,“男保姆”偶尔一用,人们还不觉得它对“保姆”这个词的女性定位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随着“男保姆”的大量使用,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结果:“保姆”所包含的“女性”语义特征被削弱,以致后来人们感到,如再直接单用“保姆”一词,恐不足以激活或突显它原本的“女性”语义特征,因此,有必要说成“女保姆”。下面举两个例子:“他想找个女保姆,帮着做饭、打扫卫生什么的。”(《北京日报》2001年3月3日)“这艘宇宙飞船一共有三个休息舱,父亲戴维斯和母亲马克索住一个舱,黑人女保姆凯瑟住一个舱,小沃特自己一个舱。”(《北京晚报》2001年2月11日)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明规则”和“女保姆”的产生。最直接的目的是跟“潜规则…‘男保姆”相区别,但它们背后的真正动因乃是社会性的。“男保姆”的出现。是传统的社会分工和职业的性别定位在现代社会被突破的一个表现;“潜规则”是“规则”在现代商品社会被异化的一个怪胎。因此,“明规则”和“女保姆”虽都是无标记词语标记化的产物,但二者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女保姆”的使用有绝对的自由,它并不限于与“男保姆”相对而言的语境。“女保姆”产生以后,就与“男保姆”共同作为“保姆”的下位概念。进入语言的一般词汇,正如“女人”和“男人”作为“人”的下位概念一样。
但“明规则”似乎没有这么自由,它的使用对语境有一定的要求,即一般都是用在与“潜规则”相对的语境中。因此,在不提及“潜规则”,也不打算让人联想到“潜规则”,甚或要避免使人产生“潜规则”的联想的时候,一般还是直接用“规则”来表示所谓的“明规则”。总之,在当前。“明规则”的使用主要限于某种特定的语用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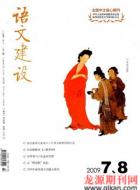
- 中学语文宋词鉴赏方法例谈 / 刘丙利 温宏娟
- 中学文学教学阅读体验的促生 / 陈 斐
- 新形势下的中学语文作业设计 / 吕秀红
- 点亮语文教学的“魔灯” / 石 岩
- 谈审美与人的全面发展 / 童庆炳
- 在极限处抒情 / 穆 青
- 高考作文题:理性的失语与诗意的欠缺 / 王鹏伟
- 用生成语言学理论认识联语的语法教学功能 / 黄明明
- 也谈“狐死首丘” / 王丹丹
- 曲径通 / 尤立增
- “齐天大圣”得名考 / 姚伟嘉
- “项羽”的名和字 / 段亚广
- 彰显“大教材”,杜绝“泛语文” / 段双全
- 从“明规则”谈起 / 王灿龙
- “标题党”之面面观 / 吴 鹏
- 关键在命题的切入点 / 陈成龙
- “五毛”新解 / 曲丽玮
- “云时代”到来了 / 宗守云
- 探究“探究” / 孙晋诺
- 说“性价比” / 曾 柱
- 开放度、简明性与考试公平 / 潘新和
- 2009年部分高考语文试卷语言文字运用题浅析 / 郭龙生
- 积极推广“经典诵读”,大力推进文化建设 / 王登峰
- 我看2009年全国高考文言文试题 / 史杰鹏
- 2009年高考文言文阅读试题综述 / 赵 华
- 听唱新翻杨柳枝 / 任富强
- 昏暗时世的沉痛悼亡 / 王培元
- 2009年高考语言表达试题特点刍议 / 俞发亮
- 《红楼梦》经典艺术正在被消解 / 薛 颖
- 重在意识,重在过程,重在常规 / 李 节
- 篇章回指与话语衔接 / 马国彦
- 将语言文字工作落实到名校创建之中 / 黄少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