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09年第7期
ID: 138355
语文建设 2009年第7期
ID: 138355
浅析苏轼的“以文为诗”
◇ 曾 姝
“以文为诗”是中唐至宋,特别是北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们针对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文”指的是不同于骈文的散行单句,不拘骈偶、对仗、音律等的形式自由的文体。“诗”则是特指六朝至唐以来形成的句法、字数、平仄、音韵等有严格规定的近体诗。“以文为诗”即是突破近体诗的种种束缚和羁绊,借用形式较为自由的散文之字、句、章法来进行诗歌写作。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出:“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这段评论清楚地指出了苏轼的“以文为诗”不仅是对唐人的继承,而且有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发展。那么,苏轼究竟是如何“大放厥词”,使“以文为诗”“成一代之大观”的呢?
纵观苏轼的文学创作,其诗歌的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质量之高,是其词作所不能及的。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指出:“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从24岁在《南行集》中创作的第一批诗歌至66岁终老,40多年间苏轼共创作了2700多首诗,可见他对诗歌创作的热爱和坚持。
一般来说,苏轼的诗歌并不违背韵律要求,而且能够充分表达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随意挥写,自由奔放,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能做到这一点,便要仰仗于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巧妙运用。
在字法上,首先,苏轼把一些本多见于散文、极少出现在诗中的字词用于诗中。如“是”“之”“矣”等。如《游金山寺》中“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韩干马十四匹》中“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泗州僧伽塔》中“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其次,苏轼善于将一些口语、俗语引入诗中。例如在《雨后行菜圃》一诗中,苏轼写道“天公真富有,膏乳泻黄壤。霜根一蕃滋,风叶渐俯仰……小摘饭山僧,清安寄真赏”,“天公”“富有”“小摘”等本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通俗口语,苏轼却拿它们来作诗,看似粗俗不登大雅之堂,实却生动朴实自然。
可以说,苏轼的诗词之所以能流传不朽,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其通俗化、口语化、朴实自然的语言。这在其诗歌的句法方面亦有突出表现。苏轼作诗常常打破诗歌格律化的限制,而使用散文的句式来传情达意。例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长长的散文句式信手拈来,自由潇洒。又如《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三字散句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独特的意境。语法结构上与时俱进的革新更是苏轼诗歌的一大特色。北宋所在的中古时期的语法特点主要有判断句式、“把”字结构、“者”字结构、“所”字结构等,如《病中游祖塔院》中的“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次韵答元素》中的“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将地狱等天宫”……这些句式赋予了诗歌明快平实、朗朗上口的散文特色,充分顺应了诗歌回归“自然艺术”境界的美学潮流。
苏轼同样成功地将散文的章法植入诗歌创作中,创造出变幻无穷的诗歌结构,将通俗自然的诗句架构成雄奇瑰丽、独具匠心的艺术作品。倘若能真正深入地挖掘苏诗的章法艺术,我想,那些批判宋诗“思想平庸,内容浅薄,艺术低下,语言陈腐”的人也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评论了。苏轼的诗歌中有许多以章法取胜的名篇,如《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雪浪石》《荔枝叹》等。
总之,苏轼的确将“以文为诗”的手法运用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在坚持诗歌自身艺术特色的前提下,大胆尝试、创新,突破当时诗歌创作的陈规,将散文的自由性融入严谨的诗歌创作中,使诗歌更加接近生活原型,更好地表达出诗人的情感,并与读者产生共鸣,让诗歌成为亲切、自然的艺术载体,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开创了北宋诗歌别开生面的时代风格,对我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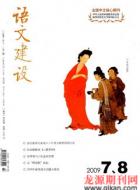
- 温故知新 / 饶杰腾
- “语文”课程名称亟须规正 / 潘 涌
- 敬畏母语 / 史绍典
- 素质教育视野中的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 李 节
- 让我们走出两极思维的怪圈 / 黄厚江
- 看母语教学地位的升沉 / 于漪
- 论点摘编 /
- 两个答 / 王尚文
- 谈《鲁滨孙漂流记》的后殖民语境 / 龙剑明
- 回望六十年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轨迹 / 顾振彪
- 语文定名六十年,名实相副何其难 / 王松泉
- 语文教学的去知识化和技能化倾向 / 倪文锦
- 主题组元潜藏的危机 / 施 平
- 生活本位与伪科学化 / 潘新和
- 浅析小作文训练的类型、特点与价值 / 钟家莲 邓小珠
- 对比阅读: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 钱理群
- 抒情景观中的悲剧氛围 / 孙绍振
- 学生主体与语文知识内容的缺失 / 徐林祥
- “刘姥姥进大观园”喜剧效应的心理分析 / 翟应增
- 好嘴“好”在哪里? / 章国华
- 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 叶利清
- 一利化干戈 / 叶茂樟
- 论语文教学中学生反思能力的培养 / 李福灼
- 浅析苏轼的“以文为诗” / 曾 姝
- 斥天与誓天 / 杨小曼
- 评出“真”味,品出“悲”情 / 孙建高
- 此“民”非彼“民” / 杨仕威
- 《雨霖铃》 / 梅培军
- 《采薇》教学设计 / 徐德琳
- 追求课堂训练设计的有效性 / 王 君
- 根据现实阅读需要创生合宜的教学内容 / 叶黎明
- 优化语文教学的提问策略 / 刘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