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2期
ID: 136760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2期
ID: 136760
对毛词《贺新郎》的五大辨正
◇ 肖科
1923年,毛泽东创作了《贺新郎》一词。该词极不一般,它地位显赫,待遇优厚:
其一,在众多版本的《毛泽东诗词》中,它被列于开篇(只有刘继兴编著《魅力毛泽东》等少数书例外,将1921年写给夫人杨开慧的《虞美人·枕上》列在第一),足见其在毛诗词中的重要地位。
其二,天纵诗才的毛泽东一生写过大量的诗词,《人民日报》却独独将《贺新郎》两度发表:一次是毛泽东逝世两周年即1978年9月9日,另一次是毛泽东诞生101周年纪念日即1994年12月26日。
其三,毛泽东一生写给女性的诗词不过六首,分别是:1921年的《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1923年的《贺新郎》,1936年12月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57年5月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1961年2月写给已参加民兵的女机要员小李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以及1961年9月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一般学者、读者均有一个共识,《贺新郎》与《虞美人》、《蝶恋花·答李淑一》都是直接或间接关乎原配夫人杨开慧,而这“两首半”词几乎占据了6首诗词的半壁江山。
当然,纯粹地从艺术价值来看,《贺新郎》一词也确是词中上品,情真意切、凄清婉丽,在数量可观的毛诗词中别具一格。
也许正基于上述原因,人民教育出版社选择了这首《贺新郎》作为高中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第二单元“挚情的呼唤”的“精读”篇目。但是随着对文本的细读、精读,笔者却发现了不少疑问:《贺新郎》存在“版本”的差异,词题存在分歧(一作《贺新郎·别友》,一作《贺新郎》),词句“人有病”的确解,“误会”的有无等等。下面,笔者试图就五个方面的疑问做些考订与辨正,求教于方家。
一辨:《贺新郎》的“版本”之别——1923版和1978版存在四大差别
翻检《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季世昌,南京出版社,2001年4月)、《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罗炽主编,周谷城、赵朴初、臧克家、姚雪垠等18人顾问,华夏出版社,1993年12月)等书发现,《贺新郎》存在两个“版本”:1923版和1978版。为简明起见,笔者姑且称1923版为“初创版”,而称1978年《人民日报》等发表的文本为“修订版”,高中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版本属于后者,全词如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3年版(初创版)词的本来面貌是: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诗词集》的注释等资料显示:1973年冬天,毛泽东将修改后的这首词,加上“别友”的标题,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即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版本。
“初创版”与“修订版”四大区别如下表:
二辨:《贺新郎》的抒发对象——“妻”还是“友”?
对《贺新郎》的词题究竟是“别友”还是无题这个问题,多数读者和学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也许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那么重要。毕竟,存在从词题到词句4处差别(见上表)的两个版本在表达革命者毛泽东“不愿或不能留恋儿女私情,而要以四海为家的革命豪情与远大志向”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词题有分歧,可是另一方面包括“文献版”在内的绝大多数意见又认为,“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这里就存在一个蹊跷事:为什么不题为“别妻”?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妻”与“友”混淆不辨?从惯例上说,毛的诗词在正式发表前,都曾经过反复的推敲、修改,包括与他的诗友郭沫若、臧克家、胡乔木、陈毅等讨论切磋,往往是修改后显得更具光彩,更显精绝,如“水拍”与“浪拍”,“我失杨花……”与“我失骄杨……”等。这确系一疑。
长沙人、当代学人彭明道则干脆提出,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他还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断定杨开慧不是这个“倩影”后,他更指出毛泽东眼前的“倩影”是陶毅(字斯咏,湖南湘潭人,与向警予、蔡畅号称“周南三杰”,又有“江南第一才女”之称)。
无独有偶,黄建新导演、2011年热播的影片《建党伟业》曾以汤唯饰演陶毅,毛泽东与陶斯咏的婚外恋情越传越神……当然,作为制片商炒作毛的情感故事,更多的是打造票房“卖点”的考虑,正式播出的影片已不见汤唯的戏份,足见该问题的复杂与敏感,处理它需要审慎从事。
对此,笔者认为鹤龄先生的一篇与彭明道商榷文章中的解说令人耳目一新且令人信服——究其实,“妻”这个名词只是婚姻关系中与“夫”相对的一个概念,与感情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妻”是“夫为妻纲”的夫权下的一种附属物。对于广大妇女而言,就是屈辱的代名词。“友”则不同,它建立在志趣相投的友情友爱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力量的干预和约制。没有友情友爱,也就没有友的存在。毛主席在晚年整理此词稿时,对标题是进行了再三斟酌的。所以才有了两个手稿前稿无标题而后稿用“别友”作标题。用“友”不用“妻”,正是从“妻与友”的内涵着想,所表示的正是他与杨开慧不同寻常的挚爱。何况,毛主席的婚姻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先后有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三任妻子。而“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样的知心女友却只有杨开慧一个。所以,词题不用“妻”而用“友”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了毛主席思考问题的精明之处。如用“别妻”为题,不但显得俗气,也不能反映出他与杨开慧相交以心的挚爱,同时还产生了专指之嫌。
而杨开慧《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的话语也可以呼应此说:“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了他。婚前有差不多二年的恋爱生活,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去共这一个命运。”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的弱女子,竟然可以在爱人干革命的日子里克服种种苦难一人扛起全家的重任,抚养三个孩子,最后为了自己爱人的事业,牺牲了年仅29岁的生命。从中不难看出,二人情感的真挚与刻骨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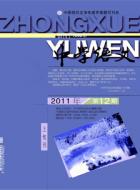
- 建设真正开放的语文学科 / 李国栋
- 漫谈语文教师的角色意识 / 李新生
- 语文教师的语文教育史知识探析 / 袁彬
- 学情探测:从评价方式到教学模式 / 胡根林
- 深度赏析 广角生发 / 席欣圣
- 功夫在诗外 / 梅晴
- 论“朱子读书法”对阅读教学的启示 / 佃礼杰
- 刍议说明文教学内容的确定 / 陈俊江
- 对话课堂:让生命在快乐中拔节 / 李利中
- 作文命题指导思想及基本要求管见 / 萧兴国
- 线性不足:作文常见的危险区域 / 崔国明
- “经验之塔”理论对作文情境教学策略的启示 / 晓棣
- 欣赏中领略写作奥义 / 黄希鹏
- 读出课文内容的“集合” / 余映潮
- 语文人本教育的开拓者 / 张晨
- 解读翠翠内心世界的N重悲凉 / 何莉
- “排” / 张旋
- 自我救赎的漫漫长途 / 惠军明
- “教”与“学”思维的差异与转化 / 章国华
- 借用多媒体 促进学生的探究能力 / 董旭午
- 人文性:语文教学的灵魂 / 张朝昌
- 高效的阅读,快乐的分享 / 刘娟
- 《学会描写景物》教学实录 / 胡礼仁
- 微博中的符号体态语 / 赵军
- 人究竟是不是东西 / 郝文华
- 析“考碗族” / 丁瑞华
- 对毛词《贺新郎》的五大辨正 / 肖科
- 写《旧书》欲得高分:关键在于“有思想” / 覃明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