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2期
ID: 356021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2期
ID: 356021
语文阅读教学的理论困境
◇ 李国栋
阅读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在语文教学中,阅读最为基本”(于漪语)。在以读写为核心的语文教学中,“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叶圣陶语)。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语文教学在后现代课程观的影响下呈现了一些新气象,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课堂讨论热烈了,但琅琅的读书声少了;所谓独立的、个性化的解读多了,但合理化的推演少了;创造性阅读、探究性阅读、多元解读多了,但误读也泛滥成灾了。阅读活动成为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对话”,课堂成了众声喧哗的“自由论坛”。
不少人开始反思,阅读的本质该是什么?阅读活动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语文阅读教学成为了“无中心”、“无组织”、“无结果”的“非指示性教学”?笔者认为,造成当前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阅读学元理论的纠缠不清。近一百年来。阅读学理论受西方哲学、文艺学影响。经历了一个头绪繁多的发展过程。龙协涛在《文学阅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说,文学解释学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阅读教学作为特殊的阅读活动,因为有了特定的读者——教师和学生的参与,其实也走过了一个与之相似的过程: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教师中心最后是学生中心。
笔者在拙文《对话:从独语走向喧哗》中曾指出,阅读理论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接受主义阅读理论取代文本中心主义;对话理论改造接受主义;建构主义应运而生。通过三次重大的变革,我们很容易看出:阅读学走的一条路径是:解释——结构——解构——建构。而当前的语文阅读教学正徘徊在解构——建构的路上。
问题由此产生了,当前语文阅读教学的元理论到底应该是文本主义的、接受主义的、对话理论的,还是建构主义的?我们到底该服膺于哪种理论,把它们奉为圭臬?
事实是,在我们的新课程理念中,传统的解释学理论与后现代思潮共存交织,纠缠不清。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说:“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作品意义的过程。作品的文学价值,是由读者在阅读鉴赏过程中得以实现的。”“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从这些表述,我们看得出清晰的建构主义印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话理论的影子,“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还说:“应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努力做到知人论世,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知人论世”不正是中国最古老的作者中心论吗?不同的阅读理论混杂在一起,其产生的必然结果是阅读教学莫衷一是,不知所措。于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困境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困境之一:文本中心与读者中心
阅读学的文本中心论是20世纪艾略特和瑞恰兹开启的新批评派提出的。兰色姆则在《新批评》中提出了文学作品本体论,他认为。如果承认文学作品是一种带有本质意义的存在,那么文本自然就会处于一种不容挑战的中心位置。
文本是文学的载体。一切文学活动都是围绕文本展开的:作家创作文本,读者阅读文本,批评家研究文本。傅修延在《文本学》中写道:“文本学既可以说是文学中的基础理论。也可以说是阅读学的基础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教学作为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的特殊阅读活动也应该围绕文本这个核心来进行。在文本中心论看来,作品一旦写成,创造它的“上帝”——作者死了。所有的阅读和批评都与作者无关。文本成为一个自足的独立的个体,它才是阅读活动的权威,文本本身的意义才是阅读的终极目标。所谓阅读,就是寻找那个隐藏在作品中的正确意义。
但是,文本中心论的阅读观后来却遭遇到了最严峻的挑战。接受主义美学否定了文本中心论。他们把读者拉进了文本的生产行列。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自身独立向每一个读者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越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的反响,使文体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当读者逐渐占领文学舞台的中心,阅读学的后现代时代到来了。20世纪后半期,后结构主义对文本的固定意义产生了怀疑,这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解构主义彻底颠覆了文本的意义。至此,文本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在读者中心主义主导下,语文阅读教学对文本的无限制多元解读泛滥成灾。许多解读过于追求新奇,却远离了文本,丧失了审美趣味。比如,一位著名的青年语文特级教师在教学朱自清《背影》时,最后的“创造性阅读结论”竟然是“父亲违反了交通规则,私自攀越铁道”。这种所谓的多元解读和创造性阅读,实质上是一种悖逆文本、文本边缘化、空洞化的“误读”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当前这种误读的倾向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困境之二:解构与建构
“解构”的出现是一次颠覆性的事件。解构主义的倡导者德里达自创了一个词——延异来说明文本意义无限延宕的过程:意义取决于差异,意义必将向外扩散。意义最终无法获得,处于无穷延宕的状态。
在阅读理论上,解构主义认为,任何文本都没有定解,因而永远向读者的阐释活动敞开,没有读者参与的文本是不完整的。他们否定经典,主张在阅读中悬置前人的阐释,直接面对作为阅读目标的文本。他们认为,任何所谓的意义都只是阐释。而不是对文本内在性质的客观揭示。
虽然持解构主义观点的人口口声声说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多元视角、多维思考,并不是想把阅读教学变成一种没有本源性、根基性和意义约束的游戏,堕入一种“丧失中心”、“无权威”、无确定性状态的虚无世界。但解构主义以无中心论反对中心论带来的必然结果是阅读的虚无主义。因此,艾布拉姆斯在《解构的天使》中批评说:“德里达的文本之室是一个封闭的回音室,其中诸多意义被降格为某种无休止的言语模仿,变成某种由符号到符号的横七竖八的反弹回响。它们如不在场的幽灵,不是由某种声音发出。不具有任何意向。不指向任何事物,只是真空中的一团混响。”
建构主义基本上是与解构主义共生出现的。这种理论认为:学习过程是学生的认识思维活动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是学习者通过自身已有的知识、技能、经验与外界(读本、生活等)进行交互活动以获取、建构新知识的过程。建构主义抛弃了解构主义否定和批判一切的做法,主张要建构。我们可以看出,从解构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解构主义倡导的是颠覆,建构主义则强调重建。
建构主义理论坚持认为,阅读是读者领会文本、发现问题、创造意义的一种思维活动,从发现的角度而言,文本的意义是读者通过阅读活动发掘出来的。它要求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储备、学习经验来主宰自己的思维活动,建构新的知识和意义,达到个性鲜明的深刻
阅读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在语文教学中,阅读最为基本”(于漪语)。在以读写为核心的语文教学中,“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叶圣陶语)。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语文教学在后现代课程观的影响下呈现了一些新气象,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课堂讨论热烈了,但琅琅的读书声少了;所谓独立的、个性化的解读多了,但合理化的推演少了;创造性阅读、探究性阅读、多元解读多了,但误读也泛滥成灾了。阅读活动成为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对话”,课堂成了众声喧哗的“自由论坛”。
不少人开始反思,阅读的本质该是什么?阅读活动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语文阅读教学成为了“无中心”、“无组织”、“无结果”的“非指示性教学”?笔者认为,造成当前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阅读学元理论的纠缠不清。近一百年来。阅读学理论受西方哲学、文艺学影响。经历了一个头绪繁多的发展过程。龙协涛在《文学阅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说,文学解释学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阅读教学作为特殊的阅读活动,因为有了特定的读者——教师和学生的参与,其实也走过了一个与之相似的过程: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教师中心最后是学生中心。
笔者在拙文《对话:从独语走向喧哗》中曾指出,阅读理论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接受主义阅读理论取代文本中心主义;对话理论改造接受主义;建构主义应运而生。通过三次重大的变革,我们很容易看出:阅读学走的一条路径是:解释——结构——解构——建构。而当前的语文阅读教学正徘徊在解构——建构的路上。
问题由此产生了,当前语文阅读教学的元理论到底应该是文本主义的、接受主义的、对话理论的,还是建构主义的?我们到底该服膺于哪种理论,把它们奉为圭臬?
事实是,在我们的新课程理念中,传统的解释学理论与后现代思潮共存交织,纠缠不清。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说:“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作品意义的过程。作品的文学价值,是由读者在阅读鉴赏过程中得以实现的。”“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从这些表述,我们看得出清晰的建构主义印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话理论的影子,“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还说:“应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努力做到知人论世,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知人论世”不正是中国最古老的作者中心论吗?不同的阅读理论混杂在一起,其产生的必然结果是阅读教学莫衷一是,不知所措。于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困境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困境之一:文本中心与读者中心
阅读学的文本中心论是20世纪艾略特和瑞恰兹开启的新批评派提出的。兰色姆则在《新批评》中提出了文学作品本体论,他认为。如果承认文学作品是一种带有本质意义的存在,那么文本自然就会处于一种不容挑战的中心位置。
文本是文学的载体。一切文学活动都是围绕文本展开的:作家创作文本,读者阅读文本,批评家研究文本。傅修延在《文本学》中写道:“文本学既可以说是文学中的基础理论。也可以说是阅读学的基础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教学作为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的特殊阅读活动也应该围绕文本这个核心来进行。在文本中心论看来,作品一旦写成,创造它的“上帝”——作者死了。所有的阅读和批评都与作者无关。文本成为一个自足的独立的个体,它才是阅读活动的权威,文本本身的意义才是阅读的终极目标。所谓阅读,就是寻找那个隐藏在作品中的正确意义。
但是,文本中心论的阅读观后来却遭遇到了最严峻的挑战。接受主义美学否定了文本中心论。他们把读者拉进了文本的生产行列。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自身独立向每一个读者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越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的反响,使文体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当读者逐渐占领文学舞台的中心,阅读学的后现代时代到来了。20世纪后半期,后结构主义对文本的固定意义产生了怀疑,这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解构主义彻底颠覆了文本的意义。至此,文本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在读者中心主义主导下,语文阅读教学对文本的无限制多元解读泛滥成灾。许多解读过于追求新奇,却远离了文本,丧失了审美趣味。比如,一位著名的青年语文特级教师在教学朱自清《背影》时,最后的“创造性阅读结论”竟然是“父亲违反了交通规则,私自攀越铁道”。这种所谓的多元解读和创造性阅读,实质上是一种悖逆文本、文本边缘化、空洞化的“误读”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当前这种误读的倾向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困境之二:解构与建构
“解构”的出现是一次颠覆性的事件。解构主义的倡导者德里达自创了一个词——延异来说明文本意义无限延宕的过程:意义取决于差异,意义必将向外扩散。意义最终无法获得,处于无穷延宕的状态。
在阅读理论上,解构主义认为,任何文本都没有定解,因而永远向读者的阐释活动敞开,没有读者参与的文本是不完整的。他们否定经典,主张在阅读中悬置前人的阐释,直接面对作为阅读目标的文本。他们认为,任何所谓的意义都只是阐释。而不是对文本内在性质的客观揭示。
虽然持解构主义观点的人口口声声说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多元视角、多维思考,并不是想把阅读教学变成一种没有本源性、根基性和意义约束的游戏,堕入一种“丧失中心”、“无权威”、无确定性状态的虚无世界。但解构主义以无中心论反对中心论带来的必然结果是阅读的虚无主义。因此,艾布拉姆斯在《解构的天使》中批评说:“德里达的文本之室是一个封闭的回音室,其中诸多意义被降格为某种无休止的言语模仿,变成某种由符号到符号的横七竖八的反弹回响。它们如不在场的幽灵,不是由某种声音发出。不具有任何意向。不指向任何事物,只是真空中的一团混响。”
建构主义基本上是与解构主义共生出现的。这种理论认为:学习过程是学生的认识思维活动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是学习者通过自身已有的知识、技能、经验与外界(读本、生活等)进行交互活动以获取、建构新知识的过程。建构主义抛弃了解构主义否定和批判一切的做法,主张要建构。我们可以看出,从解构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解构主义倡导的是颠覆,建构主义则强调重建。
建构主义理论坚持认为,阅读是读者领会文本、发现问题、创造意义的一种思维活动,从发现的角度而言,文本的意义是读者通过阅读活动发掘出来的。它要求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储备、学习经验来主宰自己的思维活动,建构新的知识和意义,达到个性鲜明的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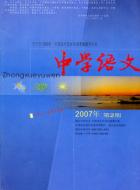
- 论语文知识系统重构的原则 / 屠锦红
- 文学教学的基本目标及策略 / 汤奇云
- 语文的激情与激情语文 / 刘 祥
- 语文教学中的体验学习 / 程良焱
- 说说“探究梳理”教学 / 朱宗明
- 熟悉基础上的陌生 / 孙 月
- 语文阅读教学的理论困境 / 李国栋
- 善用教学契 / 厉行威
- 例谈消息类文本的阅读教学 / 李仁甫
- 请跟我来 / 方兰香
- 我想象的翅膀在这里起飞 / 章国华
- 握住你的手 / 刘德海
- 再谈高考作文命题的科学性 / 谭未为 谭德华
- 作文育 / 计占海
- 史怀泽告诉了我们什么? / 文 勇
- 品读《小石潭记》中的禅意 / 徐艳霞
- 孤光肝胆 / 司亚飞
- 高中课程目标需要修改 / 陈祥书
- 解读意象、意 / 赵运兵
- 引导学生主动感悟文学作品中的美 / 兰燕妮
- 课文因创新阅读而精彩 / 江美华
- 如何寻找阅读的感觉 / 刘 方
- 《孔雀东南飞》偶记二则 / 朱 江
- “发生”与“发展” / 刘 恒
- 新课标初中语文九年级(上)第四单元教案设计 / 徐世玉
- “国语”探源 / 李薛妃
- 说“快闪族” / 高昆白
- 谈讳饰修辞在古文中的应用 / 范保林
- 成语结构和汉民族社会文化背景 / 李德伦
- 从写作语境的多层制约因素中看高考作文的失语 / 高西栋
- 高考压缩语段题解题技巧指要 / 王 珏 王 穹
- 高考作文要有“五气” / 王学华
- “君子好逑”的“好”应该怎么读? / 张传权
- 《出师表》难句析疑 / 李晓华
- 《桃花源记》注释商补三则 / 谢政伟
- “何处”可以表示“什么时候”吗? / 陈淼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