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2期
ID: 356030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2期
ID: 356030
品读《小石潭记》中的禅意
◇ 徐艳霞
《小石潭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所作的一篇山水游记。文章清丽中蕴藏幽怨,宁静里包蕴禅机。“清”与“寒”的境界,抒发出作者孤标傲世的思想格调。
禅定:山水洗尽尘俗的纯粹
佛语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因为禅定于心,所以眼中所见的才是纯粹的景物,空灵的境界。“闻水声,如鸣佩环”,声音是纯粹的,隔篁竹,亦能听闻,除却山林的寂静,若没有一颗纯净的禅心,又怎么能够听得见?“水尤清冽”,潭水是纯粹的,无任何杂质,因为小潭“全石以为底”,与尘俗彻底隔绝,一如诗人的心灵。“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树木藤蔓是纯粹的,随缘任运,纵横交错,恣意生长。“怡然不动;傲尔远逝,往来翕忽”,游鱼是纯粹的,任性自由,洒脱无羁,不必理会红尘中的纷纷扰扰。客观物象是无情的,但是到了作者笔下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因为它浸润了诗人的情怀,展现了这位“穷则独善其身”的失意者高雅的精神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柳宗元的山水诗文,虽有许多写无我之境。但更多是写有我之境。他笔下的山石溪流,花草树木,都是有灵有性而又无人赏识的。读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正是借这些具有人的品格的山水景物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气。
在山清水秀的幽静之乡,既没有尘世的车马喧闹,又远离人事的格斗纷争,这种清静的自然环境。如同佛教追求的“禅定”境界,如同高僧们潜心研读经典必需的清静心境,达到了天然的默契与和谐。使作者忘怀世事,把思想和意念导引到“清静无为”的境地,从而潜心于体悟禅理经义。在这幽静的所在,人与自然山水有着一种巨大的亲和力,在清幽冷寂中渗透生死轮回,于大自然的永恒宁静中妙悟禅机。
出世:摆脱世俗的羁绊,于山水中见性灵
柳宗元是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的。柳宗元出生在“安史之乱”后,幼年又曾经历过“建中之乱”,所以他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他一心想要改革弊政,为民请命,所以参与了王叔文的革新集团。并导致了最终的失败被贬。仕途坎坷,宦海沉浮。这时的他身为闲职,政治抱负已无法实现。所以他只有寄情于山水,在山水之间寻求心灵的解脱,
在《小石潭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远离尘俗与喧嚣的清静之地,画面清冷幽寒。小潭须“伐竹取道”方可寻觅,可见其悠远荒僻,潭的周围环境是“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给人一种透骨的寒意。意境宁静淡远。贬谪中的柳宗元,虽然在主观上依旧处于压抑与寂寞的氛围中,但在客观上,他毕竟远离了官场倾轧与政治纷争的污浊,这一时期的柳宗元得以有空闲与释门高僧交往,进一步拉开了他与现实的距离。他同他们参禅论道,谈玄说佛,并写了许多有关佛教的诗序碑铭。佛教的出世间法,慰藉着诗人孤独寂寞的灵魂,不时地淡化着他的自我情志。使他步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之途。在这样一个无名的小潭边,作者竟能静下心来观游鱼,赏藤木,听水声,可见其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在山水中,作者抛却了一切尘俗,甚至忽略了与他来同游的人,若不是后记中附带提及,我们几乎以为是他一个人来到了这样幽僻的山野丛林。
但是柳宗元的思想又是矛盾的。身受儒家与释家两种思想的熏陶,他内心的出世与人世的思想时时纠缠,所以他的自我解脱与排遣总是暂时的,凄怆与忧伤才是他情感的主流。小石潭的冷静与清幽反而触发了他的感伤情绪,所以他“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柳宗元在佛教与山水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与沉迷,却很快被现实的剧痛唤醒。于是他的山水诗文形成苏轼所说的:“柳仪曹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南涧中题》详注)的模式。用柳宗元自己的诗句来概括,就是:“升高欲自轷,弥使远念来”(《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
柳宗元禅学思想探源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注:袁家耀《柳宗元“好佛”略谈》,《江淮论坛》1995年第3期。)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详见《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只不过这时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忙于实现政治抱负。不以文为意,所以作品少,佛教思想也表现得不明显。被贬永州后,他由一朝重臣而流落远荒,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内心的极度痛苦,使他不得不到佛教中寻求寄托甚或解脱。初到永到永州,居无定所,只好寄居在重巽的龙兴寺,这样每天接触的是经书禅堂,促使他进一步研究佛教教义,从而对佛教有了深切的体会。他改贬柳州后,来到提倡“顿悟”的南宗禅的老巢,进一步受到禅宗的浸染。苏轼曾说:“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绝妙古今”。(注:《柳宗元全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详注》,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64页。)佛教的出世间法已影响到他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趣味,并渗透于他的诗歌散文创作中。
柳宗元一生好佛,佛禅为柳宗元的山水诗文提供了宁静、淡远的意境,在小石潭记中,我们便可具体领略到他文章中的禅意。
[作者通联:江苏张家港外国语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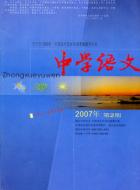
- 论语文知识系统重构的原则 / 屠锦红
- 文学教学的基本目标及策略 / 汤奇云
- 语文的激情与激情语文 / 刘 祥
- 语文教学中的体验学习 / 程良焱
- 说说“探究梳理”教学 / 朱宗明
- 熟悉基础上的陌生 / 孙 月
- 语文阅读教学的理论困境 / 李国栋
- 善用教学契 / 厉行威
- 例谈消息类文本的阅读教学 / 李仁甫
- 请跟我来 / 方兰香
- 我想象的翅膀在这里起飞 / 章国华
- 握住你的手 / 刘德海
- 再谈高考作文命题的科学性 / 谭未为 谭德华
- 作文育 / 计占海
- 史怀泽告诉了我们什么? / 文 勇
- 品读《小石潭记》中的禅意 / 徐艳霞
- 孤光肝胆 / 司亚飞
- 高中课程目标需要修改 / 陈祥书
- 解读意象、意 / 赵运兵
- 引导学生主动感悟文学作品中的美 / 兰燕妮
- 课文因创新阅读而精彩 / 江美华
- 如何寻找阅读的感觉 / 刘 方
- 《孔雀东南飞》偶记二则 / 朱 江
- “发生”与“发展” / 刘 恒
- 新课标初中语文九年级(上)第四单元教案设计 / 徐世玉
- “国语”探源 / 李薛妃
- 说“快闪族” / 高昆白
- 谈讳饰修辞在古文中的应用 / 范保林
- 成语结构和汉民族社会文化背景 / 李德伦
- 从写作语境的多层制约因素中看高考作文的失语 / 高西栋
- 高考压缩语段题解题技巧指要 / 王 珏 王 穹
- 高考作文要有“五气” / 王学华
- “君子好逑”的“好”应该怎么读? / 张传权
- 《出师表》难句析疑 / 李晓华
- 《桃花源记》注释商补三则 / 谢政伟
- “何处”可以表示“什么时候”吗? / 陈淼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