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2期
ID: 356016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2期
ID: 356016
文学教学的基本目标及策略
◇ 汤奇云
一、问题的提出:语文课堂文学教育的缺失
我做了一个实验,让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和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同时读一篇他们都还没有学过的文章——人教社八年级上册课本中的一篇课文,当代作家李森祥的《台阶》。之所以选这篇文章,是由于这篇现代文新字生词极少,甚至可以说写得十分浅白,可以“照顾”到那位小学生的阅读水平。全文除了“尴尬”一词外,几乎没有十分出彩的字句。不到20分钟,他们都读完了。我问:读懂了没有?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读懂了。我逐一地问他们:这篇文章说些什么?小学四年级学生回答:讲一个父亲把一座三级台阶的房子改为了九级台阶的房子。初中生显然嫌小学生的回答太简陋,补充道:主要是他家乡有一种观念,房子的台阶越多,房主人的地位就显得越高。初中生为他比小学生读出的东西要多一些而显得尤为得意。
教材的选编者显然不是为了给初中生介绍这种奇异的风俗或观念,主要目的还是要展示作家对一位地位平凡,一生穷苦劳作,老实而憨厚,却矢志不移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到老的父亲形象的文学描写技法,同时培养学生对“父亲”的“奋斗史”产生一种崇高的感恩之情。这一意图已为课文前的小提示说得很清楚:“与《背影》一样,这篇课文写的也是一位父亲,儿子眼中的父亲。这位父亲是怎样生活和劳动的?他有什么追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者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去叙述父亲的故事的?”,
这两个学生的“自主阅读”,显然都没有触及到“父亲”形象的问题,更谈不到情感体验的问题。这些关于文学教学中的基本问题(主要是指审美教育问题和情感教育问题),只有通过教师的有效指导和引导。才能使学生得以接近。尽管这一实验只是个别案例,并不能普遍地说明问题,但由这一实验,我还是感到中学语文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文学教育目标缺失的问题。由于语文课中文学教育目标的缺失,导致了语文课堂变成了枯燥的汉语语言工具的解剖室。其实,在当下以新课标教材为上课依据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字词句的积累以及语法修辞技法的发现与破解,除了在文言文的教学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展示空间外,在现代文特别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教学中则实际已经降居次要的地位,在腾挪出来的这一片教学空间里,要求相应地让位于文学教育,以切实落实汉语教学中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双重统一。也就是说,不要让中学的语文教育止步于认词识字、复述故事概要、分析文章的篇章结构,而要进一步实施文学审美教育和情感熏陶教育,让新课标下的中学语文教学目标清晰起来,课堂教学内容充实完整起来。
二、识解双重艺术形象,是文学教学的基本目标
那么,中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到底该教些什么呢?
文学教育问题,当然是一个很宽泛也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从宏观来说,文学教育包括文学创作、文学基本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一系列内容;但对于中学语文课堂来说,文学教育的目的就要具体得多,主要是要对教材和配套读本中所筛选的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学鉴赏,培养中学生对文学的感性认识。这也是新课标要求中学语文实施“人文教育”的目标所规定的。
由于中学语文的“人文教育”主要要落实两个目标:一个是审美教育,能够辨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一个是情感教育,要有健康的思想情感和文化情怀,因此中学语文中的文学教学目标,就可以进一步具体到艺术形象与作家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所寄寓的思想情感这两个基本元素上。只有通过对不同艺术形象的识解,才能让学生了解各种千差万别的审美形态:如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等;并通过对文本中的情感的体验,让学生体会作家在作品中所熔铸的心灵美,建立基本的人文思想与道德底线,树立健康的情感立场。
因此,艺术形象的解读是中学语文中的文学教学的核心元素。
那么什么是文学中的艺术形象呢?它在具体的文本中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尽管关于文学的定义多种多样,也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立得下来的结论,但有一点却是确定不移的,那便是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的一门艺术。汉语文学就是用我们的汉语来塑造艺术形象。汉语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一切人与物、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等都是艺术形象,这就包括叙事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抒情文学中的物象或意象。以当前所流行的四大文学体裁而论,小说、戏剧一般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抒情短制的诗歌和散文则往往以物象或意象为主。当然报告文学、通讯特写,乃至长篇叙事诗也是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主。
认识到艺术形象的塑造是文学艺术的核心,那么另一个重点便是,辨别每一个具体文本所构筑的艺术世界里的关键人物形象和关键意象,因为关键人物和关键意象往往是作家“微言大义”之所在,也就是常言所谓的“文眼”或“诗眼”,它们几乎潜藏着作者的全部言说秘密,也是这篇作品成为独特艺术创造的决定性成分。
小说与戏剧等叙事文学中通过情节或事件来塑造人物形象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中短篇小说或独幕剧,往往情节简单,人物较少乃至单一,人们较易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如鲁迅《阿Q正传》里的阿Q,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里的陈奂生,他们在题目上就已经点明里作者所要刻画的重点人物形象。而对于长篇叙事作品,则往往由于叙述的事件纷杂,人物也众多,则需要人们在鉴赏过程中费一番甄辨功夫,找出其中最为出彩的人物;在戏剧文学中则应该找出其中最有戏份的人物。不过,在中学课本中。即使编选了经典长篇叙事作品,也是经过了节选以适应课本篇幅和教学时数,而节选则是由编者把他认为最出“小说”或最出“戏”的篇章段落挑选出来,为教材的使用者(教师)事先完成了甄别功夫。如曹禺的《雷雨》,几乎所有的编选者都会将鲁侍萍再入周公馆导致周家人伦真相的大揭底,周萍要出走,蘩漪“雷雨”性格总爆发的这一段纳入教材,因此蘩漪才是《雷雨》中的关键人物。
抒情文学一般呈现于比较短制的散文和诗歌之中。尽管是对作家主观缥缈情绪的抒发,或是对社会人生的抽象思考,但对于作家的表达来说,除了他要依赖的“感慨系之”的具体物象之外也别无他法。走进作家生命的一切人、事、物,都成为了他们折射思想与情绪的反光板。朱自清笔下的月夜、荷塘、荷塘上空漂浮的清风(《荷塘月色》);吴伯箫笔下的菜园(《菜园小记》);纺车(《记一辆纺车》);戴望舒笔下的小巷、细雨(《雨巷》);王之涣笔下的鹳鹊楼(《登鹳鹊楼》);苏轼笔下的赤壁(《赤壁赋》)……,都在传递着他们各自在不同生存时空中的生命感悟或人生的情怀。因此,古今中外各种抒情短制中的物象纷呈,就不仅仅是“写景状物”、“写景抒情”的语言描摹,更是千姿百态的人生姿态在语言中的呈现。常言之谓“文如其人”,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说“文学是人学”,所指涉的正是这种状况。
我们对文学艺术的欣赏,也不仅仅是对文本中人物形象、各种物象或意象及其描摹状写高超技法的欣
一、问题的提出:语文课堂文学教育的缺失
我做了一个实验,让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和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同时读一篇他们都还没有学过的文章——人教社八年级上册课本中的一篇课文,当代作家李森祥的《台阶》。之所以选这篇文章,是由于这篇现代文新字生词极少,甚至可以说写得十分浅白,可以“照顾”到那位小学生的阅读水平。全文除了“尴尬”一词外,几乎没有十分出彩的字句。不到20分钟,他们都读完了。我问:读懂了没有?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读懂了。我逐一地问他们:这篇文章说些什么?小学四年级学生回答:讲一个父亲把一座三级台阶的房子改为了九级台阶的房子。初中生显然嫌小学生的回答太简陋,补充道:主要是他家乡有一种观念,房子的台阶越多,房主人的地位就显得越高。初中生为他比小学生读出的东西要多一些而显得尤为得意。
教材的选编者显然不是为了给初中生介绍这种奇异的风俗或观念,主要目的还是要展示作家对一位地位平凡,一生穷苦劳作,老实而憨厚,却矢志不移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到老的父亲形象的文学描写技法,同时培养学生对“父亲”的“奋斗史”产生一种崇高的感恩之情。这一意图已为课文前的小提示说得很清楚:“与《背影》一样,这篇课文写的也是一位父亲,儿子眼中的父亲。这位父亲是怎样生活和劳动的?他有什么追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者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去叙述父亲的故事的?”,
这两个学生的“自主阅读”,显然都没有触及到“父亲”形象的问题,更谈不到情感体验的问题。这些关于文学教学中的基本问题(主要是指审美教育问题和情感教育问题),只有通过教师的有效指导和引导。才能使学生得以接近。尽管这一实验只是个别案例,并不能普遍地说明问题,但由这一实验,我还是感到中学语文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文学教育目标缺失的问题。由于语文课中文学教育目标的缺失,导致了语文课堂变成了枯燥的汉语语言工具的解剖室。其实,在当下以新课标教材为上课依据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字词句的积累以及语法修辞技法的发现与破解,除了在文言文的教学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展示空间外,在现代文特别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教学中则实际已经降居次要的地位,在腾挪出来的这一片教学空间里,要求相应地让位于文学教育,以切实落实汉语教学中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双重统一。也就是说,不要让中学的语文教育止步于认词识字、复述故事概要、分析文章的篇章结构,而要进一步实施文学审美教育和情感熏陶教育,让新课标下的中学语文教学目标清晰起来,课堂教学内容充实完整起来。
二、识解双重艺术形象,是文学教学的基本目标
那么,中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到底该教些什么呢?
文学教育问题,当然是一个很宽泛也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从宏观来说,文学教育包括文学创作、文学基本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一系列内容;但对于中学语文课堂来说,文学教育的目的就要具体得多,主要是要对教材和配套读本中所筛选的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学鉴赏,培养中学生对文学的感性认识。这也是新课标要求中学语文实施“人文教育”的目标所规定的。
由于中学语文的“人文教育”主要要落实两个目标:一个是审美教育,能够辨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一个是情感教育,要有健康的思想情感和文化情怀,因此中学语文中的文学教学目标,就可以进一步具体到艺术形象与作家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所寄寓的思想情感这两个基本元素上。只有通过对不同艺术形象的识解,才能让学生了解各种千差万别的审美形态:如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等;并通过对文本中的情感的体验,让学生体会作家在作品中所熔铸的心灵美,建立基本的人文思想与道德底线,树立健康的情感立场。
因此,艺术形象的解读是中学语文中的文学教学的核心元素。
那么什么是文学中的艺术形象呢?它在具体的文本中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尽管关于文学的定义多种多样,也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立得下来的结论,但有一点却是确定不移的,那便是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的一门艺术。汉语文学就是用我们的汉语来塑造艺术形象。汉语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一切人与物、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等都是艺术形象,这就包括叙事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抒情文学中的物象或意象。以当前所流行的四大文学体裁而论,小说、戏剧一般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抒情短制的诗歌和散文则往往以物象或意象为主。当然报告文学、通讯特写,乃至长篇叙事诗也是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主。
认识到艺术形象的塑造是文学艺术的核心,那么另一个重点便是,辨别每一个具体文本所构筑的艺术世界里的关键人物形象和关键意象,因为关键人物和关键意象往往是作家“微言大义”之所在,也就是常言所谓的“文眼”或“诗眼”,它们几乎潜藏着作者的全部言说秘密,也是这篇作品成为独特艺术创造的决定性成分。
小说与戏剧等叙事文学中通过情节或事件来塑造人物形象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中短篇小说或独幕剧,往往情节简单,人物较少乃至单一,人们较易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如鲁迅《阿Q正传》里的阿Q,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里的陈奂生,他们在题目上就已经点明里作者所要刻画的重点人物形象。而对于长篇叙事作品,则往往由于叙述的事件纷杂,人物也众多,则需要人们在鉴赏过程中费一番甄辨功夫,找出其中最为出彩的人物;在戏剧文学中则应该找出其中最有戏份的人物。不过,在中学课本中。即使编选了经典长篇叙事作品,也是经过了节选以适应课本篇幅和教学时数,而节选则是由编者把他认为最出“小说”或最出“戏”的篇章段落挑选出来,为教材的使用者(教师)事先完成了甄别功夫。如曹禺的《雷雨》,几乎所有的编选者都会将鲁侍萍再入周公馆导致周家人伦真相的大揭底,周萍要出走,蘩漪“雷雨”性格总爆发的这一段纳入教材,因此蘩漪才是《雷雨》中的关键人物。
抒情文学一般呈现于比较短制的散文和诗歌之中。尽管是对作家主观缥缈情绪的抒发,或是对社会人生的抽象思考,但对于作家的表达来说,除了他要依赖的“感慨系之”的具体物象之外也别无他法。走进作家生命的一切人、事、物,都成为了他们折射思想与情绪的反光板。朱自清笔下的月夜、荷塘、荷塘上空漂浮的清风(《荷塘月色》);吴伯箫笔下的菜园(《菜园小记》);纺车(《记一辆纺车》);戴望舒笔下的小巷、细雨(《雨巷》);王之涣笔下的鹳鹊楼(《登鹳鹊楼》);苏轼笔下的赤壁(《赤壁赋》)……,都在传递着他们各自在不同生存时空中的生命感悟或人生的情怀。因此,古今中外各种抒情短制中的物象纷呈,就不仅仅是“写景状物”、“写景抒情”的语言描摹,更是千姿百态的人生姿态在语言中的呈现。常言之谓“文如其人”,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说“文学是人学”,所指涉的正是这种状况。
我们对文学艺术的欣赏,也不仅仅是对文本中人物形象、各种物象或意象及其描摹状写高超技法的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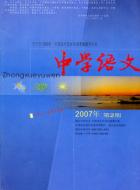
- 论语文知识系统重构的原则 / 屠锦红
- 文学教学的基本目标及策略 / 汤奇云
- 语文的激情与激情语文 / 刘 祥
- 语文教学中的体验学习 / 程良焱
- 说说“探究梳理”教学 / 朱宗明
- 熟悉基础上的陌生 / 孙 月
- 语文阅读教学的理论困境 / 李国栋
- 善用教学契 / 厉行威
- 例谈消息类文本的阅读教学 / 李仁甫
- 请跟我来 / 方兰香
- 我想象的翅膀在这里起飞 / 章国华
- 握住你的手 / 刘德海
- 再谈高考作文命题的科学性 / 谭未为 谭德华
- 作文育 / 计占海
- 史怀泽告诉了我们什么? / 文 勇
- 品读《小石潭记》中的禅意 / 徐艳霞
- 孤光肝胆 / 司亚飞
- 高中课程目标需要修改 / 陈祥书
- 解读意象、意 / 赵运兵
- 引导学生主动感悟文学作品中的美 / 兰燕妮
- 课文因创新阅读而精彩 / 江美华
- 如何寻找阅读的感觉 / 刘 方
- 《孔雀东南飞》偶记二则 / 朱 江
- “发生”与“发展” / 刘 恒
- 新课标初中语文九年级(上)第四单元教案设计 / 徐世玉
- “国语”探源 / 李薛妃
- 说“快闪族” / 高昆白
- 谈讳饰修辞在古文中的应用 / 范保林
- 成语结构和汉民族社会文化背景 / 李德伦
- 从写作语境的多层制约因素中看高考作文的失语 / 高西栋
- 高考压缩语段题解题技巧指要 / 王 珏 王 穹
- 高考作文要有“五气” / 王学华
- “君子好逑”的“好”应该怎么读? / 张传权
- 《出师表》难句析疑 / 李晓华
- 《桃花源记》注释商补三则 / 谢政伟
- “何处”可以表示“什么时候”吗? / 陈淼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