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2期
ID: 356031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2期
ID: 356031
孤光肝胆
◇ 司亚飞
张孝祥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南宋朝廷国运衰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国家划江分冶,江北是饱受金人蹂躏的中原遗民。张孝祥《六州歌头》一词写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二月间。此前一年冬季十一月初八,金主完颜亮与宋会战于采石,金大败,完颜亮东下扬州被部下所杀,南宋小朝廷才转危为安,得以喘息。闻听采石大捷的消息,张孝祥喜悦欲狂,赋词一首《水调歌头,庞佑甫闻采石战胜》,表达壮怀激烈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将皇权传给太子赵昚,自己做起了太上皇,太子赵昚即位后第二年改元为隆兴元年(1163年),世为孝宗。孝宗皇帝是南宋皇帝中尚有恢复中原志向的,隆兴元年正月,他想整饬军队,起用人才,朝廷上弥漫着北伐的空气,起用了抗金老将张浚为右丞相,将江南军事指挥权交给张浚,并密谋联合西夏协同抗金。在做了北伐的简略准备后,4月发兵六万大军北伐,战事初期比较顺利,5月中旬收复宿州,主将李显忠与邵宏渊二人因小事失和,大敌当前。邵宏渊置国家大局而不顾。在敌人反扑李显忠被围的紧急情势下,居然按兵不动,李显忠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助只得放弃宿州,于5月24日溃退到符离集一带。抗战失利。主和派势力占据上风,孝宗起用了秦桧余党汤思退为丞相,一时间,主和派及投降势力左右着南宋朝廷,此时张孝祥在建康(今南京)为张浚幕僚。所见所闻,不免令人失望,故在张浚的筵席上写了这首著名的《六州歌头》,表达了诗人满腔悲愤,更激发了人们爱国热情。
词的开篇便把我们带入眼前的凄凉场景: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在千里连绵的长(江)淮(河)上,极目远眺,过去森严壁垒的关塞险要已经荡然无存。“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征尘暗淡,霜风凄厉,更增加战后的凄凉。此情此景,勾引诗人无限情怀,“暗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站在建康城外,风猎猎,霜凄紧,人影孤,心悲切,迫使诗人回转到对往事的追忆,慨叹中原陷落,大好河山南北分置,彼岸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驻足江边,我只有拳拳报国之心,就连当年孔子讲学的圣地洙(水)泗(水)上,早已不见弹弦歌舞的盛景,四处飘溢胡酋茹毛饮血般的腥风血雨。“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强敌仅仅一水之隔,烈火照江,笳鼓惊心,形势岌岌可危。金酋却耀武扬威,借着夜色寻隙围猎。俨然一代霸主气势。
下阕抒发自己的情怀,“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词人慨叹自己空有雄心壮志却难施展男儿抱负,明知时不我待,人生易逝,却只能嗟叹利剑封尘,一事无成。怯懦的南宋统治者按兵不动。议和的使者络绎不绝。“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像这样的委曲求全、丧权辱国、苟且偷安,其情何堪?词的最后举出沦陷区人民向往祖国统一,殷切希望山河统一的事实,更“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渴望南归,每每“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真有“有泪如倾”的悲愤之感。
上阕写景叙事,下阕议论抒情。该词表达出作者的侠肝义胆,光照青史,其激荡的爱国情怀,感天动地。对现实淋漓尽致的揭露,壮士徒怀报国之志的描写,令读者更深切感受到作者的义愤与无奈。真可谓孤光肝胆照,忠愤气填膺,壮志竟未酬。豪杰血践行。
此词成稿后,不仅主战派遭到了打击和迫害。隆兴二年(1164年4月撤消了江准都督府,罢免了张浚,与金人签定了“隆兴和议”,张孝祥也被免职。同期与张孝祥有类似命运和共同情感的还有陆游、文天祥、岳飞等南宋爱国诗人,他们以自己的壮举践行杀敌报国的决心。岳飞在《满江红》发出的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慨叹,更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憾,何时灭”的诘问,强烈道出叫士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抗敌豪情,并发出重整山河的雄图大志。更有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誓死铭言。就是那才情洋溢的陆游也把他生前不能看到祖国山河统一“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愿化做无限的感慨“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后人对张孝祥的《六州歌头》评价很高,我们看张孝祥的词,追踪苏轼,气概凌云,以雄丽著称。善于用典,词章清丽,描摹自然,长于抒情。正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六盛赞其词曰:“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
[作者通联:大连大学人文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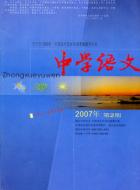
- 论语文知识系统重构的原则 / 屠锦红
- 文学教学的基本目标及策略 / 汤奇云
- 语文的激情与激情语文 / 刘 祥
- 语文教学中的体验学习 / 程良焱
- 说说“探究梳理”教学 / 朱宗明
- 熟悉基础上的陌生 / 孙 月
- 语文阅读教学的理论困境 / 李国栋
- 善用教学契 / 厉行威
- 例谈消息类文本的阅读教学 / 李仁甫
- 请跟我来 / 方兰香
- 我想象的翅膀在这里起飞 / 章国华
- 握住你的手 / 刘德海
- 再谈高考作文命题的科学性 / 谭未为 谭德华
- 作文育 / 计占海
- 史怀泽告诉了我们什么? / 文 勇
- 品读《小石潭记》中的禅意 / 徐艳霞
- 孤光肝胆 / 司亚飞
- 高中课程目标需要修改 / 陈祥书
- 解读意象、意 / 赵运兵
- 引导学生主动感悟文学作品中的美 / 兰燕妮
- 课文因创新阅读而精彩 / 江美华
- 如何寻找阅读的感觉 / 刘 方
- 《孔雀东南飞》偶记二则 / 朱 江
- “发生”与“发展” / 刘 恒
- 新课标初中语文九年级(上)第四单元教案设计 / 徐世玉
- “国语”探源 / 李薛妃
- 说“快闪族” / 高昆白
- 谈讳饰修辞在古文中的应用 / 范保林
- 成语结构和汉民族社会文化背景 / 李德伦
- 从写作语境的多层制约因素中看高考作文的失语 / 高西栋
- 高考压缩语段题解题技巧指要 / 王 珏 王 穹
- 高考作文要有“五气” / 王学华
- “君子好逑”的“好”应该怎么读? / 张传权
- 《出师表》难句析疑 / 李晓华
- 《桃花源记》注释商补三则 / 谢政伟
- “何处”可以表示“什么时候”吗? / 陈淼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