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期
ID: 355983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期
ID: 355983
应该把阅读当作一门独立的课程来设计
◇ 李祖贵
要把阅读当作一门独立的课程来设计,首先必须把课内课外放到同等地位来规划。孙绍振教授近期谈到阅读教学的问题时,认为要“求实”必先“去蔽”。过去的阅读教学,不仅封闭内敛,死抠课本,造成了学生在阅读总量上的严重不足,而且僵化保守,死搬教条,造成了学生在阅读质量上的严重滑坡。现在要来检讨学生的读书生活,一是要检讨我们的阅读教学方式,二是要检讨我们的阅读指导方法。一个侧重于课内,一个偏重于课外,改革应该同步启动。
过去的阅读教学存在着许多自我“蒙蔽”现象。譬如关于知识教学的问题,新课程一提重发展、重过程、重感悟,就有人认为是不要知识教学了。许多语文公开课上,根本就没有了知识教学的环节,大家似乎都以知识教学为耻了。其实,针对广大中小学生而言,他们的知识储备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只不过是我们过去所津津乐道的许多语法知识,文体知识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丰富学生的阅读体验而已。很显然,这里要讨论、要改革的是知识本身的问题,而不应该是要不要知识教学的问题。我们的阅读教学,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譬如:课文是例子还是引子(靶子、影子)的问题,多元解读有无边界的问题,训练与感悟的关系问题,讲解与诵读的比例问题等,都应该是当前阅读教学亟待解决的难题。但课内的问题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随着新课改的推进,有些问题已经并正在得到顺利的解决。所以,我们目前讨论阅读的话题。重镇还是课外这一块。
我以为,要把课外阅读当作课程来规划和经营,至少应该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一是阅读兴趣问题。朱永新博士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但对于刚刚开智的青少年来说,阅读的兴趣是需要激发和引导的。尤其是当今社会,不良诱惑太多。学业负担太重。如果老师和家长不能有意识地激发和引导学生进行文本阅读,很多人可能从此就会远离书本,厌恶读书。古时人们常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利益诱惑来激发孩子读书,并且也产生了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等发奋读书的感人故事,但利益驱动下的阅读难免局促和浮躁。“目前师生读书之弊,在低年级的问题是功利性太强(体现于只为课堂教学服务)、引导不足但牵制过多……一句话,童年读书没了童年味,少年读书没了少年味,最终是在书与儿童少年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而错过了浪漫阶段的泛阅读、趣味阅读,也就错失了无意识地积累和存储,将严重影响到后面精确阶段的顺利发展。”总之,过去我们强加给阅读的负荷太多,期待太多,目标太多。其实,真正愉悦而有兴趣的阅读,应该是宽松、自由、宁静状态下的阅读。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应该努力为学生争取这样的读书空间,营造这样的读书环境。尤其是在启蒙阶段,更应该导而不牵,让学生在兴趣的支配下养成读书的习惯。
二是阅读品位问题。兴趣一旦激发,习惯一旦养成,如果不给予正确的引导和提升,则很有可能陷入一种阅读黑洞——虽然总在不知疲倦的读,但总是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读。知识视野得不到拓展,人生境界得不到升华,思维能力得不到锻炼。这样的阅读不仅徒费光阴,而且戕害心灵。目前世面上最为流行的漫画、言情、武侠、侦探、魔幻等快餐和消遣读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学生的阅读胃口。他们更愿意享受阅读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愉悦,而不愿意接受阅读所引发的思维碰撞和问题探究。这种情形的阅读,实质上只是一种游成和娱乐,而根本不能上升到课程的层面来考量。这就似乎产生了一对矛盾。如果过早的给阅读以限定和诱导的话,就会消减学生的阅读兴味。如果一直不给阅读以规范和标高的话,又会放纵学生的阅读惰性。所以,真正要把阅读当作课程来规划,首先必须对儿童的阅读心理,阅读习惯,阅读倾向,阅读级差进行仔细研究和科学定位。
关于阅读品位的问题,我曾经有过两点,一点是说读物要有品位,一点是说读者要会品味,二者不可偏废。
一说阅读如进食,应注意营养搭配。现在的中小学生,一味喜欢《时文选粹》和《智慧背囊》一类的书籍,固然能丰富语言,澡雪精神,但要真正成为一个学有成就的人,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有丰厚的科学、艺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储备,才能够登高望远,触类旁通,拥有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思维。现在的孩子,叫他们稍微看一点富有理论深度和思辩色彩的书籍,常常便会以“看不懂”和“不感兴趣”相回绝,岂不知,这正如吃菜,虽然不一定样样可口,但为了营养平衡,还是应该硬咽一些。从这一角度出发,我是非常赞成如下说法的:“一本书,如果有10—30%是有阅读障碍的,那么对读者而言这就是极有益的阅读;如果有50%以上是有阅读障碍的,那么这种阅读就会显得很艰难,难以为继;但如果几乎没有任何阅读障碍,可以一目十行地从头看到尾,那么这本书对阅读者而言就几乎没有价值可言了。”
一说阅读如品茗,应讲究细嚼慢咽。我国古代文人,很讲究喝茶,三五同仁,清风明月,一盏在手,诗情画意,讲究的是一个“品”字。读书也是一样,惟有“品”,才有回味;惟有“品”,才生情致;惟有“品”,才养精神。可是,当代人读书,要么如走马观花,不求甚解,要么如金秋割麦,放倒一片,更多的时候甚至是为写而读,为抄而读,为读而读,这是解渴的读法,而不是养“气”的读法,我国古代教育家朱熹曾经说过:“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当然,这是指达到一定境界之后的“精确阅读”,与前面所提到的“浪漫阅读”并无矛盾之处。
三是阅读资源问题。据有关报道,中国人的年平均阅读量仅为0.5本左右。这既有阅读习惯的问题,更有阅读资源的问题。我曾到过许多乡镇中学,实验室,微机室,语音室,劳技室,无不设备簇新,投资巨大,但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室和阅览室,即使有一些装点门面的图书,也是要么破旧不堪,要么概不外借。学生在学校里无书可读,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许多校长和老师把读书看作是学生个人的事情,实际上这是天大的失误。学生在学校里来,绝不仅仅是为了读那几本教科书,学校更多的应该是为学生创造阅读条件,提供阅读环境,指引阅读方向。朱永新博士在苏州掀起的书香校园活动,本是一个对症下药的金点子,但如果从课程的高度来审视的话,仅有一个“书香校园”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更多的书香家庭、书香社区、书香村落应运而生的时候,我们的阅读教学才会有落脚的根基。真诚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精神和肉体双重饥饿的悲剧不要重演。
一说到阅读资源的问题,可能有人又要叫穷。可只要看一看学校周边地区的教育书社,看一看里面堆积如山的教辅资料,我们便会明白,学生并不是没有花这一份买书的钱,也并不是没有时间来读相应的书。而是教育自身出了偏差,学校自己拒绝了书香。
[作者通联:湖北宜都市教研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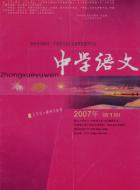
- 用语文点燃学生的生命之灯 / 曹明海 史 洁
- 新课程下语文教学目标研究简论 / 程春梅
- 让生成因预设而丰富 / 胡明道
- 作文教学研究与创造性思维的培育 / 王敬波
- 新课标下语文文本阅读之探讨 / 张治海
- 应该把阅读当作一门独立的课程来设计 / 李祖贵
- 摭谈语文扩展教学的价值 / 曹爱琴
- 阅读教学中的对话误区 / 郁 萍
- 以写促学 / 邓 敏
- 作文拟题教学设计 / 赵成昌
- 新课标下高中新诗写作教学的理性思考 / 孙陆江 曹尉军
- 梁实秋的作文观 / 吴永福
- 文学解读的四重天 / 宋 亮
- 解读景物就是解读生命 / 刘小华
- 爱的不等式 / 章国华
- 《羚羊木雕》教学实录 / 刘 丹 王林皖
- 《赤壁赋》教案 / 杨 宏
- 贤臣善谏良君 / 张瑞旸
- 语文探究学习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萧兴国
- 语文教科书应建立科学的背诵知识体系 / 杨广收
- 教学中“自主学习”之我见 / 彭 英
- “曲笔”写尽思乡情 / 苏传明
- 让“对话”更深入 / 冯颖艳
- 对一种评课现象的批评 / 程少堂
- “多元解读”与“追求真理” / 易国祥
- 新课标初中语文九年级(上)第三单元教案设计 / 刘 芳
- 两种特殊的文言复词例释 / 牛严济
- 叠词妙 / 孟 华
- 《兰亭集序》思想探微 / 于爱国
- 不是“罗汉”,是“壶卢”! / 杭起义
- 令人费解的“积伶积俐” / 孙心世
- “秦伯说”能译为“秦伯高兴”吗? / 杨广英
- 2007年高考现代文阅读命题走向蠡测 / 刘国良
- 高考语言表达题的问题与对策 / 沈坤林
- 关注赋分要 / 张学德
- 海外语文教材述略 / 张悦群
- 大陆、港台及国外语文课程标准中教学目标研究 / 冯旭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