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期
ID: 35600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期
ID: 356007
不是“罗汉”,是“壶卢”!
◇ 杭起义
鲁迅的散文诗《雪》,我至今尚能记诵。
在备课时,我参阅了人教版的教学用书,写好了一篇简案,便去上课。其中课后《研讨与练习》有一题要求学生理解“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的意思。我照例是让学生先思考再讨论后回答,可是被提问的几个学生,站在那里,摇摇晃晃,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这情景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老师在课堂上也要求一个学生回答这个问题,那位同学也是摇摇晃晃,口中支支吾吾,像犯了错误一般。于是,老师就一再降低要求,让他背诵,直至把课文读一遍,仍然是没有动静。我想这位同学总不至于不会读课文的,只是在那种情形下,谁愿意开口呢。可我们的老师终于恼怒了,他引用了《雪》中的原句,大声地说道:“这哪里是什么‘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这分明就不是糊涂(壶卢)而是不干(罗汉)!”
今天,我的学生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也想说他不是“壶卢”而是“罗汉”。可是当我照着参考书的答案讲解时,我自己也“壶卢”了。为了维护人教社教参的权威,原谅我在这里不想把参考答案抄下了。我倒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句话的含义加以阐发。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孤独”是写朔方的雪的自身状态。它不“滋润”,“永远如粉如沙,绝不粘连”;它也不“美艳”,既不会“如处子的皮肤”,也没有烂漫的冬花开在雪野之中。
“死掉”是写朔方的雪的生存环境。雪是由雨在严寒的天气中形成的。因此称之为“死掉的雨”。“死”字透出此生存环境的冷酷。
“雨的精魂”是由上句“死掉的雨”而来,又是诗眼。在寒冷的天气里,雨“死掉”后便化作了雪。又因为是在朔方,风力的作用和日光的照耀,此“孤独”的雪,竟会“旋转而且升腾闪烁”。所谓“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目光中灿灿地生光”是也。这是多么坚强的灵魂!这是多么壮美的境界!同样是晴天,南方的雪即便堆成了雪人,能给人以短暂的欢欣,却也留给人深深的遗憾与惋惜,因为它经不起日光的照耀,它会消释,会褪色,没有朔方的雪的这种傲骨精神。
总之,鲁迅对比着来写南方的雪的优美与朔方的雪的壮美,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这不是简单的写南方的雪的滋润美艳,或者带给人热闹与欢愉,也不是对雨或者是对雪的献身的挽歌,而是对朔方的雪的另一种生机与生命力的歌颂——它不屈于冷酷的环境,具有着“韧”抗争精神,它是对雨的“升华”,“是雨的精魂”。
时至今日,教参对这首散文诗《雪》还没有解释清楚,让我终于明白了,我的那位受过批评的中学同学真的是有点冤枉——
这分明不是“罗汉”(不干),而是“壶卢”(糊涂)!
[作者通联:浙江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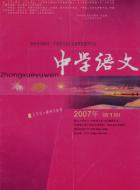
- 用语文点燃学生的生命之灯 / 曹明海 史 洁
- 新课程下语文教学目标研究简论 / 程春梅
- 让生成因预设而丰富 / 胡明道
- 作文教学研究与创造性思维的培育 / 王敬波
- 新课标下语文文本阅读之探讨 / 张治海
- 应该把阅读当作一门独立的课程来设计 / 李祖贵
- 摭谈语文扩展教学的价值 / 曹爱琴
- 阅读教学中的对话误区 / 郁 萍
- 以写促学 / 邓 敏
- 作文拟题教学设计 / 赵成昌
- 新课标下高中新诗写作教学的理性思考 / 孙陆江 曹尉军
- 梁实秋的作文观 / 吴永福
- 文学解读的四重天 / 宋 亮
- 解读景物就是解读生命 / 刘小华
- 爱的不等式 / 章国华
- 《羚羊木雕》教学实录 / 刘 丹 王林皖
- 《赤壁赋》教案 / 杨 宏
- 贤臣善谏良君 / 张瑞旸
- 语文探究学习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萧兴国
- 语文教科书应建立科学的背诵知识体系 / 杨广收
- 教学中“自主学习”之我见 / 彭 英
- “曲笔”写尽思乡情 / 苏传明
- 让“对话”更深入 / 冯颖艳
- 对一种评课现象的批评 / 程少堂
- “多元解读”与“追求真理” / 易国祥
- 新课标初中语文九年级(上)第三单元教案设计 / 刘 芳
- 两种特殊的文言复词例释 / 牛严济
- 叠词妙 / 孟 华
- 《兰亭集序》思想探微 / 于爱国
- 不是“罗汉”,是“壶卢”! / 杭起义
- 令人费解的“积伶积俐” / 孙心世
- “秦伯说”能译为“秦伯高兴”吗? / 杨广英
- 2007年高考现代文阅读命题走向蠡测 / 刘国良
- 高考语言表达题的问题与对策 / 沈坤林
- 关注赋分要 / 张学德
- 海外语文教材述略 / 张悦群
- 大陆、港台及国外语文课程标准中教学目标研究 / 冯旭洋
